|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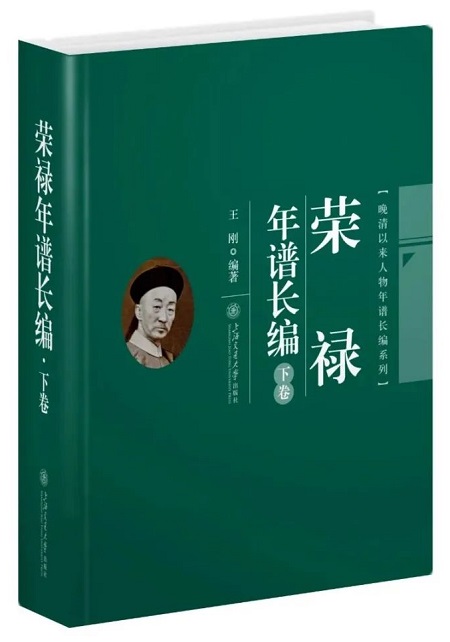
《荣禄年谱长编》(订购)
王刚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荣禄(1836—1903),字仲华,号略园,别号田舍主人。早年曾任步军统领、户部左侍郎、内务府大臣、西安将军等职,甲午战争时期派督办军务处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与闻机要。戊戌政变后入值军机处并节制北洋各军。庚子事变后,在西安行在中枢中,任领班军机大臣,是《辛丑条约》谈判及”清末新政”开端时期之政府首脑。荣禄属慈禧太后亲信重臣,其女指婚于醇亲王载沣,其外孙溥仪被立为皇帝。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荣禄年谱长编》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荣禄折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荣禄传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荣禄存札》及《荣禄存各处禀稿》、清华大学图书馆藏《荣禄函稿底本》为主干资料,同时搜罗散见于时人日记、函札、笔记、年谱及报刊上的零碎素材,编撰而成的首部荣禄年谱长编之作,累计约百余万字。资料之取舍、编排,除反映荣禄之生平行述外,亦考虑作为史料集供学界利用。
序
尚小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王刚耗费多年心血,终于完成了《荣禄年谱长编》上下两卷的编著。早在十多年前,当王刚还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时,就对荣禄产生浓厚兴趣,并就荣禄与戊戌政变的关系进行过探究。以后他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从茅海建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又以“荣禄与晚清政局”为题,对其人进行了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其间,我曾为他这一届研究生讲授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并参与过他的博士培养方案实施的若干环节。可能因为这种因缘吧,他希望我在年谱出版之际写几句话。我仔细拜读后,觉得这部年谱有三个突出的优点。
一、征引详赡。一部好的年谱,首先应该详实、客观地呈现谱主一生交游及行事,这就要求编撰者尽可能详尽地搜集、占有相关史料。就这一点而言,这部年谱几乎无可挑剔,举凡与谱主相关的各类型史料,如上谕、奏折(片)、咨呈、禀帖、函札、电报、日记、诗文、年谱、传记、地方志、报刊等,无一不加搜罗。其中既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多个全宗的大量未刊档案,又有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荣禄存札》及清华大学图书馆藏《荣禄函稿底本》这样的久为学界所知,但并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已刊未刊史料,以及不少近年新出史料,乃至拍卖文物图片史料等。具体征引史料时又有一个突出特点,即不仅仅以出自荣禄本人之手的文字为重点,而是如凡例所言:凡能反映谱主生平活动又可资征信者均予收录。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有一大类以往并没有受到研究者高度重视的史料,在年谱中被反复征引,这就是各级官员、门生故吏和戚友私下请托荣禄提携或办事的书信。此类书信现存百封以上,零星看似无太大价值,综合看其实是反映晚清社会与官场百态极为重要的素材,也是深刻了解谱主必不可少的材料。除此外,年谱征引重点当然还是与荣禄处理各类公务相关的史料,戊戌以后征引尤富,许多时段其实是“日谱”。由于荣禄长期受宠于慈禧太后,担任过内务府总管大臣、户部侍郎、西安将军、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等诸多要职,朝廷大小事务几乎都有其参与或主持,而年谱在编排史料和史事时又非常注意前后呼应,这就使阅读本谱宛如阅读一部经过精心别择的晚清历史资料集,特别是关于甲午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新政开端史的资料集。这一特点如此突出,相信读者会有强烈感受,阅后所得收获也就不仅限于了解荣禄个人生平行事而已。
二、考订扎实。年谱的主要特点是按时序记录谱主生平交游及行事,这就要求编著者尽可能考订清楚每条史料的形成时间及每件史事的发生的时间,并要时刻注意考辨史料记载的真实性。《荣禄年谱长编》在这些方面做得也是很好的。谱中对记载不够清楚的史料的形成时间随时进行考订,并对档案、官书、史料集中错误的时间标注随时加以订正,然后以按语或注释一一呈现。对一些关键史料记载错误,或撰者与学界既有解读不同之处,也特别指出。比如,据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所记,同治帝驾崩之际,由于沈桂芬入宫迟后,荣禄“擅动枢笔”,代病中的文祥草拟了“哀诏”,结果沈桂芬到后颇不高兴,由此与谱主结怨,并思借机陷害,而文祥袒护谱主,李鸿藻又支持文祥,于是“南北之争”起于中枢。年谱首先根据《翁同龢日记》对陈夔龙的说法提出质疑,指出同治帝弥留之际,沈桂芬入宫其实早于文祥和谱主;然后指出,即使文祥因病不能拟旨,在场尚有军机大臣恭亲王、宝鋆、李鸿藻等以及弘德殿大臣翁同龢、徐桐等,资历均高于时任内务府总管大臣的谱主,不可能都推谱主执笔,况且谱主不由科举出身,生平不以文字见长,怎么可能由他来起草如此至重至大之诏书。再如,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上谕陈宝箴补授湖南巡抚,《清史稿》谓其“以荣禄荐,擢湖南巡抚”。年谱依据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皮锡瑞日记》中“夔帅(王文韶)入枢廷,右帅(陈宝箴)之起乃其保荐,必能为护法也”一则,认为《清史稿》之说“当不确”,并指出皮锡瑞当时就在长沙,“为陈宝箴亲近人物,所述近于实情”。由于戊戌变法之初,荣禄曾递折保荐陈宝箴等文武官员三十余人,《清史稿》显然是将该次保荐与陈宝箴三年前补授湖南巡抚混为一谈了。年谱虽然未能指出这一点,但依据更可靠的史料对《清史稿》提出质疑,是令人信服的。又如,有论者依据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军机大臣廖寿恒日记中“贻蔼人封事召见时发下,乃因此慈圣忽命将康、刘、林、杨、谭、杨六人处斩”的记述,认为戊戌六君子当天被处斩“系由荣禄的僚属、国子监司业贻谷上疏所引发”,并认为贻谷上疏系荣禄“授意”。年谱对此亦提出质疑,认为贻谷(霭人)庚子时期才入荣禄幕府,“此时尚无材料证明二人关系已属亲密,更无材料证明贻谷上疏系谱主授意”,而且从政变发生后谱主的一系列举动看,“其保全新党之意甚明”,无材料证明其“抵京后向慈禧献策诛杀六君子”;贻谷上疏也主要是把矛头指向张荫桓,其次才是六君子,且疏中谓“分别轻重,早正其罪”,并无一律正法字样。因此,“贻谷奏折虽是引发慈禧太后正法六君子的直接起因,但此折并非出自谱主意志,也不能反映谱主有诛杀六君子之献策”。由以上几例足可看出撰者谂熟史料,心思缜密,考订功夫甚是扎实。
三、评判允洽。年谱虽然以客观记述谱主生平交游及行事为主,但对所涉史事完全不加评判,似乎很难。尤其对荣禄这样在晚清不少重大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而言,适当的评判也是必要的,要在于客观记述和主观评判之间拿捏分寸恰到好处。《荣禄年谱长编》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可谓深思熟虑。年谱通篇不为空论,评判之处不多,但往往能在紧要处揭出,起到点睛之效,给人启发。比如荣禄早期任职神机营和内务府时,曾多次承担陵工肥差,年谱在征引相关史料后,提示这类“差事之优,令人艳羡,但亦有危机藏于其中:其一陵工挑选监督、监修不经吏部铨选,向由承修大臣自定,故请托、钻营者极多,易滋夤缘滥调情形;其二陵工进项极丰,不能自律者易沾奢靡习气,进而招惹物议”。又在叙及谱主所建“略园”时写道:“彼时京官俸禄可称微薄,营建如此奢华之私家园林,合法收入必不足,当有一大部分来自陵工及内务府任上的灰色收入。而谱主任内务府及陵差之期,与‘丁戊奇荒’相重叠,在大灾之年行中饱之事,吃穿日用又招摇若此,言官何能不觉?”显然,这种以事实为据的评判极具说服力,对读者理解谱主前期的宦途浮沉很有帮助。甲午之后,谱主渐成朝廷重臣,中外益加注目。尤其戊戌期间,其所为扑朔迷离,言人人殊。年谱认为既往对谱主的认识并不客观,于是特别针对康有为笔下的谱主形象,有一段精彩的解析:“百日维新前,荣、康关系既已不睦,六七月间天津废立传闻四起,康据此敌视荣更甚。七月底、八月初,杨崇伊、曾广汉等赴天津见荣,康更相信荣有政变阴谋,其拉拢袁世凯图谋政变,也是为对抗荣禄之需要。故康心目中,荣为反对新法之旧臣,图谋废立之元凶,后党集团之中坚。新法所以不行,引袁所以失败,政变所以发生,荣都是西后之外罪魁祸首。是以政变之后,康即据此印象丑诋荣禄。”迨至庚辛议和,清廷谋划新政,荣禄作为首席军机大臣起到何种作用,不能回避。年谱在记述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筹商新政情形后,指出其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已深知依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倡议新政无望,因此,“东南的思路主要是围绕枢臣做文章,新政之启,实由东南与枢臣合力为之”,并在记述新政诏书颁发情形后,更加明确地指出,“新政之始,实由谱主等枢臣与东南督抚‘枢疆合谋’……这是谱主于庚辛政局的一大贡献”。类似评判皆以大量史料为依据,很难让人不表认同,至少可成一家之说。
上述几个特点充分显示了王刚对晚清史料占有之丰富、运用之熟练与理解之深入。不过,这部年谱所要处理的史料如此繁杂,撰者对所涉史事不可能一一细加研究,这就难免有理解不够精密之处。兹举两例,或可为本谱之补正。其一是对康有为应召至总署对谈变法的理解。事发于百日维新开始前大约半年,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张荫桓等总署大臣均参与会见,康事后述他与荣禄发生了争执,荣声言“祖宗之法不能变”。茅海建先生认为康说可疑,因“此时康尚未大用,正谋求前程,即便与荣禄意见不一,也未必当面露出锋芒”,而“荣处世为人甚精密,似不会去主动攻康,提出‘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命题”。年谱认同这一分析,认为“‘祖宗之法不能变’云云,属康一面之词”。然而,细读年谱所引翁同龢当天日记,以“高谈时局”四字描述康的表现,以“狂甚”二字描述康给其留下的印象,甚至当晚回家后,翁仍不能平静,以“愤甚,疲甚”描述其感受。而康有为则在政变后向港报记者透露当天对谈内容说:“我建议的第一件事情是中国应当有一个组织适宜的司法制度,必须聘请一个外国人和我自己以及其他的人,共同改订法律和政府各部门的组织。”显然,康足够“锋芒毕露”,以至于让力主改革的翁都难以忍受,那么,比翁保守的荣禄以“祖宗之法不能变”来回应康之狂妄,也就可以理解了。而据康向港报透露,他并没有因荣禄反对就有所收敛,反而回怼一句:“我们的祖宗并没有一个总理衙门,难道这不已经是一个改革吗?”荣禄显然被激怒了,于是不愿再听,先行离去。其二是对庚子事变时东南督抚“不奉诏”的理解。年谱延续了一百多年来广为流行的说法,提及庚子五月二十九日“东南督抚接到二十五日宣战谕旨,决定不奉诏,继续谋划‘互保’”。然而,仔细排比、考辨相关史料,我们就会发现,庚子五月二十五日清廷除了颁布“宣战”谕旨外,还颁布了一道重要谕旨,即“集义民御外侮”谕旨。前者虽是“明发”谕旨,但因矛头指向列强,内阁实际并未向督抚传达,于督抚而言自然也就谈不到“奉诏”或“不奉诏”的问题。后者则是“廷寄”沿江沿海督抚要求执行,东南督抚不论赞同与否,都不能不表明态度。其时由于京津电报线路断绝,东南督抚直至五月二十九日尚不知朝廷颁发“宣战”谕旨,而“集义民御外侮”谕旨则通过山东巡抚袁世凯转发,在此之前已为东南督抚知悉,并在盛宣怀的穿针引线下酝酿应对之策。因此,所谓“不奉诏”并不是指不奉“宣战”谕旨,而是指不奉“集义民御外侮”谕旨,两道谕旨的指向并不相同。
就编撰技术而言,这部年谱也有完善的空间。比如,征引史料如何更加精炼,以剔除枝蔓;编排史料如何更加合理,以减少重复;叙述文字与史料如何更好地衔接,以避免脱节;按语和注释如何更好地区分,以凸显异同。还有,个别史料断句的准确性,也可以进一步打磨,精益求精。
虽然,荣禄年谱长编撰著到如此程度,已然非常成功。年谱面世无疑将会对荣禄和晚清史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对王刚多年来默默努力最好的回报。像王刚这样不为名利所惑,肯坐冷板凳,能下死功夫的学者,在当今中国学界最值得尊敬。深望他坚守这种精神,继续以优秀作品贡献学界。
名人推荐
马忠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历史人物年谱长编从形式上看,介于著作和资料之间,但是,非编者多年默默的奉献和辛劳不能竟其功,究其学术价值,往往超越一般的传记,因而普遍受到学者的欢迎和重视。《荣禄年谱长编》编者从研究荣禄,到编辑其年谱长编,跨越10多年时间,独自投入了大量精力。这部大部头的年谱,不仅是资料丰富的编年著作,同样是有分量的荣禄研究的重要成果。全书虽然以荣禄本人的经历为线索,但是,在遵循年谱体例的前提下,关注到时局变化,注意荣禄与慈禧、醇亲王、庆亲、端王、袁世凯、刘坤一、李鸿章等各个政治派系人员的交往,精心设计,详略兼顾,勾勒出晚清政局的基本面貌,从另一个侧面为展现荣禄的作用和地位提供了历史场景,这是该年谱的鲜明特色。
李文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荣禄年谱长编》综合利用晚清日记史料、官方档案、陆续刊布的名人信札、近代中外报刊等基本史料,从中搜罗并提取相关内容,囊括了现在能寻获的晚清重臣荣禄的重要资料,按照编年的形式,勾勒出荣禄一生所历经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荣禄在这些事件中的表现,史料翔实充分,对于推进晚清人物研究与政治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基础性贡献。
周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这是关于晚清重臣荣禄的第一部资料长编,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考虑到荣禄并无文集,该史料集的意义便显得十分重要。而且该年谱是在编者对于荣禄的研究中形成的,以十余年的研究为基础,不同于普通的资料搜集与整理。
霍红伟(河北师范大学法政系教授):
荣禄是影响晚清政局的重要人物,但是相对于其地位来说,以往学界对于荣禄的研究很不充分,形成了研究成果少而人物分量极重的强烈反差。作者不遗余力搜集各种存世资料,并据此排比其人生历程,形成年谱长编,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全书文字朴实,叙述冷静、客观,资料逐一注明出处,这些都体现出作者良好的学风。
编辑推荐
荣禄(1836—1903)是晚清极为重要的政治人物,其生平正处于历史学家唐德刚关注的“晚清七十年”(1840—1912)。三朝(咸丰、同治、光绪)老臣荣禄经历光绪登基、戊戌变法、庚子国变、操练新军等重要历史,他既是清朝贵胄,又是枢垣重臣,一度成为清廷最具实权的大臣。故一方面深得清朝统治者的天然信任,后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外公;另一方面又与光绪、慈禧太后等统治者,文祥、醇亲王、恭亲王、李鸿藻、李鸿章、王文韶、翁同龢、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刚毅、袁世凯等晚清政要枢臣,以及外国使臣有深入密切的公私交往。荣禄不仅是晚清史的重要见证人,更是重要参与者,其生前身后也屡遭评议,褒贬不一。张之洞赞他“既聪明又通达事理”,康有为斥他为“满洲第一大奸雄”, 章太炎戏称他为《石头记》里的“王凤姐”。荣禄也是《走向共和》电视剧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
这样一个重要、复杂而又有趣的人物却一直没有一部相应分量的年谱,好在西南大学历史学者王刚十数年潜心研究荣禄,终于在今年推出荣禄首部年谱长编。140万字、上下两卷的大部头长编可能会令一些读者“望而生畏”,但阅读过程中,我感觉这部长编颇有可读性:一是荣禄经历丰富,交游广阔,一部荣禄长编中能看到我们熟悉的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二是尚小明教授在序中称赞的“征引详赡”“考订扎实”“评判允洽”,这三个特点造就了阅读本书最酣畅淋漓的时刻:一件事情有各种说法,彼此攻击很厉害,作者从容列出各大史料,最后来一段缜密精彩的分析。这样的阅读体验并不鲜见,足以刺激读者的肾上腺素。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编辑 宋丽军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