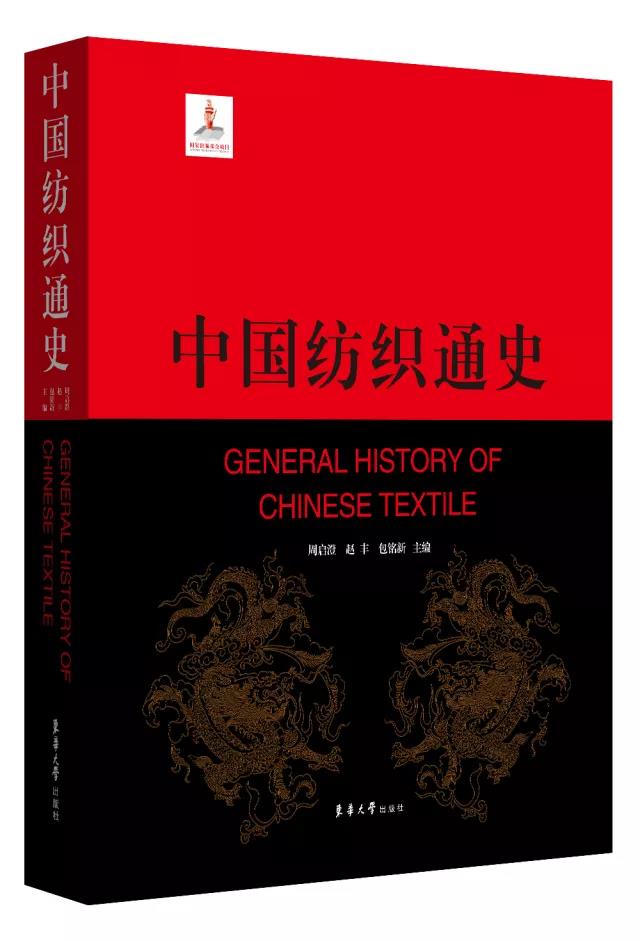
由东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历时前后8年编纂完成的《中国纺织通史》在沪首发。作为我国首部全面论述原始手工生产到当代动力机器生产的纺织业发展通史,完整、全面地研究、梳理了其在我国七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填补空白、惠及当代、传世久远,将对我国甚至世界纺织学术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具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我国著名纺织史学家及教育家96岁高龄的周启澄先生就是该书的第一主编。下文《半个世纪前 在莫斯科的留学生活》是周老发表在《档案春秋》的文章,为大家讲述他在苏联的求学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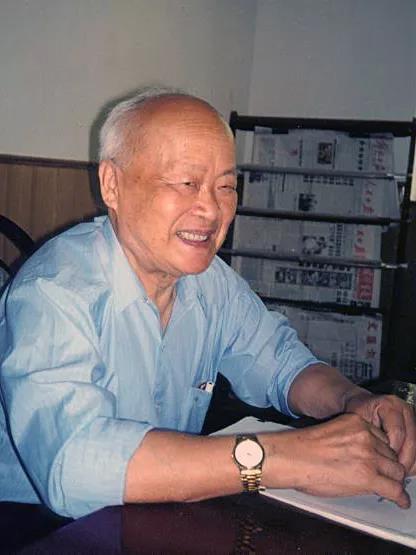
周启澄,1923年3月生,浙江宁波人,194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纺织系,1959年获莫斯科纺织学院副博士(相当于西方Ph.D)学位;历任该校毛纺教研室副主任,纺织系副主任,纺织研究所所长;1994年底离休。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上台不久,我被公派留学苏联,在莫斯科住了近4年。对当时的苏联高校以及作为学生所能接触到的当时苏联社会,印象很深。我在莫斯科拍了许多照片,每当看到这些黑白的影像,当时的留学生活情景就仿佛历历在目。
学校生活写真

1955年9月,我来到莫斯科纺织学院攻读副博士学位。坐北京到莫斯科加班专列火车,一路穿行在一望无际的白桦林中,走了11天。“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那首广泛流行的歌,不断在脑海中回荡。
去纺织学院的本科生加研究生有十多个人。到校正是星期天,学校不办公,老同学把我们临时安排住到他们房间里的空铺上。学生宿舍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十分整齐清洁,桌子、茶几上铺了洁白的方巾,上面放着插了鲜花的花瓶和瓷器或绒毛小动物等小摆设;床上笔挺的毛毯四周用雪白的床单包覆起来,叠得方方正正;枕头套了雪白的枕套,蓬松挺拔得像一块碑一般竖立在毛毯上,真像是美术馆里的艺术展台。
当天中午,大家一起到宿舍附近一家对外营业的工厂食堂用餐。先要到窗口点菜、买票。我们按照国内的习惯,由一位同学替大家集体买。由于不知道菜的俄语名称,只好按照价格点。菜上来时才发现:有的点了两个汤,有的点了两个甜食。吃完,付钱的同学向各人算账,折腾了好半天。从此,体会到国内的习惯行不通了,“集体主义”不行,以后只能个别行动。
第二天早上,本科生按照课程表去上课了。研究生则要去见导师。当时莫斯科纺织学院只有一位毛纺教授,他每天穿着工作服在一角办公。我俄语口语没过关,就请一位老同学去当翻译。我在国内学的是棉纺,临出国时,纺织工业部领导要求我改学毛纺。作为共产党员,服从组织是天经地义的,我同意了。可是,好多毛纺课程我没有学过。许多毛纺机器,我连名称也不知道。我对导师如实地说了。导师说:“研究生一般3年,你要补很多课,起码得5年。”于是,我就埋头学习,每天起码14-15小时,每星期7天。那时,每周6个工作日,5天上课,苏联同学每周六是军事训练,纺织学院男同学参加后勤部队训练,女同学则参加战地救护训练,到大学毕业时,可以获得少尉军衔。我到本科生班级去听导师讲课,因为听力速度跟不上,而且毛纺没有教科书,我就坐在第一排优秀的同学旁边,课后还把同学的笔记借回去消化,其余的时间就扑在教师阅览室。那时,研究生享受教师待遇,借书容易,座位宽敞,人也不太挤。

作者在莫斯科河边
苏联教授讲课条理清楚,简明扼要。在国内我认为纺纱中的精梳是很复杂的,不对着机器细看,简直弄不懂。我的导师把精梳过程用4个符号表达4个主要作用,分析各种工艺的不同组合,真是一目了然。
当时苏联的学制是本科5年,副博士研究生3-3.5年。博士则必须是已有相当成就的副博士才有资格攻读。苏联的高等教育基本上参照德国,比较重视实践,专业分得很细。本科毕业授予工程师学位。工科研究生通过答辩,授予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答辩前,必须有2篇论文在专业刊物上发表。当时,我国派去的本科生已读完国内大学一年级,所以,第一年课程内容都已经学过,主要是练俄语听力。研究生则大都已经工作了三、四年。
当时苏联中年教授,已经开始和学电脑的青年合作,运用电子计算机(那时,还没有个人电脑,用的是半个房间大的中型计算机)来分析纺织。于是,我在做研究时,也努力向这方面下功夫。
研究生宿舍2人一间,往往是不同国家的研究生住在一起。我就先后和波兰、匈牙利、乌兹别克、哈萨克的同学合住。由于彼此俄语水平差不多,我练口语的机会比本科学生就少得多,所以,口语长期过不了关。有时就和宿舍门厅管钥匙的退休老奶奶交谈。
当时宿舍里没有浴室,洗澡要到附近小澡堂。那里附有理发室和洗衣房。理发很快,10分钟解决问题。而当时在国内,理发、修面、挖耳朵、按摩头部、敲背等,起码30-40分钟。洗衣房备有尼龙网线袋,把需要洗的衣物一古脑儿塞进,放人大滚筒式洗衣机里清洗,离心机甩干,拿回去自己烫平。苏联人不用热水瓶。喝水临时烧,或者干脆喝自来水。苏联人洗脸不用脸盆,只凑在水槽用两手掌捧水往脸上搓洗,然后用干毛巾擦干。他们的毛巾是厚实的平织方格纹粗布巾,不起毛圈。我们都用国内带去的用品。
苏联人的生活习惯和我们不大一样,早上临八点才起床,啃几片面包就去上学、上班。晚班是夜大学,晚上八点到十一点。实验室则全天开放。午饭一般在两点以后;晚饭在八点以后。苏联教室和实验设备利用率极高,这是紧缺经济时期形成的。为了省钱,我们常常在商店里买饺子、面条、面包、鸡蛋、半成品鱼肉,自己在公用的厨房里做饭。那时,除了饺子外,还没有小包装速冻食品。中午,为了节省时间,就在食堂里吃。那时,俄语词典只有陈昌浩编的一本《俄华词典》,词汇很少。许多单词查不到。我带了一本日文的《露和(俄日)词典》,还有很多字查不到,食堂的菜单根本没法看懂。所以,只好一种一种挨个儿轮流吃。苏联正餐一般三道:第一道汤,主要是蔬菜汤。特别在漫长的冬季,只有酸白菜汤,当时价格1卢布,合人民币5角。要荤就加一大块肉,加2卢布,总价合人民币15元。当时国内大学食堂,一个月的饭钱才12元,一盆汤就得花国内4天的饭钱!所以,我们一般把汤给免了,直接点第二道正菜。我最常吃的主菜是“比附需兑克斯”,后来知道这是英语牛肉串的音译。当时,我国对研究生,按每人每月1000卢布同苏联方面结算。由学校扣除300卢布住宿费,每月发给我们每人每月700卢布。按当时汇价,合人民币350元,相当于我出国前5个月的工资。
有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活
大学学生宿舍里毛毯、床单、被单、台布、床头柜布、枕头套等都是学校提供的。而且除毛毯外,都是每星期免费换洗,简直和我国的宾馆一样。那时,我们国内上大学时,行李铺盖、热水瓶、草席、被褥、蚊帐等等都要自己带。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莫斯科城乡结合部盖起了大批高层住宅;商店里开始出售进口化妆品;星期六提前2小时下班。
我是1923年出生的。差不多和我同龄的苏联男子,都在卫国战争中上过战场。当时,我们男同学发了两套中山服,款式和苏联军服差不多。

作者在莫斯科市内教堂前留影
莫斯科冬天很长,大约有半年温度在10度以下,最冷到零下30多度。每年10月宿舍管理员就给每个房间发纸条和浆糊,让大家把窗缝糊好,避免冷风吹进来。窗有内外两层,有的同学只把内层的窗糊起来,这样,两层窗之间就成了天然的“冰箱”,把吃不了的食物放到里边冷藏或冷冻。冬季室内温度一直保持在20度左右,晚上盖一条毛毯已经够了,因为有城市集体供暖系统供应蒸汽或高温水。据说,都是有关工厂余热集中利用。因为冬季室内外温差很大,大楼出入口都有两重门,之间是一间缓冲区,门上都挂了厚重的棉门帘。教学楼、办公楼、食堂、剧场等公共场所,入口处都有衣帽间,冬季有人值班。一般都聘用退休老人,负责保管进门人员的大衣和帽子,发给存衣牌。
溜冰是冬季最流行的运动。晚上,买1卢布门票进学校附近高尔基公园的公共溜冰场,小学生们会主动上来,拉着我们的手飞快地溜。
走出校门参加社会实践
苏联的教育,很注重实践。除了校内有实验室和实习工厂,还安排学生去校外,甚至外地参观和实习。另外,还组织参观纪念地、博物馆,邀请名人来校作报告,组织参加群众活动,从而使学生接触实际,了解社会。
第二学期末,导师叫我利用暑假到外高加索近黑海边苏联最大的洗毛厂实习。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独自在国外旅行。当时我口语还不流利,学校管留学生的约飞教授委托一位家住索契(苏联黑海滨避暑胜地,距洗毛厂只一站路)的同学沿途照应我直到下车的车站。
下火车到了厂区附近,已见到了工厂的外墙,可就是找不到工厂的大门。我问路人:“工厂的大门在哪儿?”不料回答都是“工厂没有巨大的门!”我感到奇怪,后来只好改口问:“怎样才能进这个工厂?”总算得到了答案。后来我发现,是我的口语不行,还处在先汉语思维,再翻译成俄语的阶段,把“入口”直译为“大大的门”。
到了工厂,厂长派了一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技术员陪同我,料理生活。星期天带我到附近走走,替我照了许多相片。那时只有黑自的,但都会自己冲印。这位技术员1944年随部队进入柏林,战争结束后回国,复员进了洗毛厂。我听了他的经历介绍,不禁对他肃然起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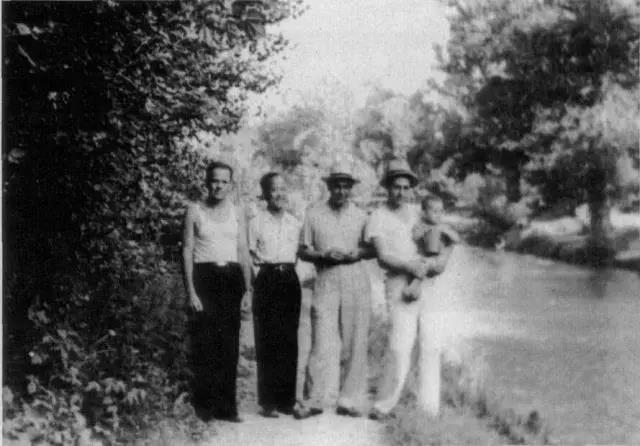
作者(左二)与工厂职工合影
工厂安排我住到一所空的职工住宅内,和两位来自环境保护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一起住。他们正在厂里搞污水治理研究。
在车间里,工程师给我介绍了情况,又指定了一位老师傅教我。师傅详详细细地给我讲解,又手把手教我操作。过两个小时,师傅就让我休息,并说:“你尽管去找姑娘们聊聊天。”我们那时思想是“一本正经”的,简直表现得有点拘谨。但苏联姑娘会主动来聊天一起去食堂吃饭。
实习结束,同住的环保研究所人员劝我去索契玩,我还是按照计划,径直返校。当时想:我必须抓紧每一分钟的时间,因为人民花了这么多外汇供我来苏联,绝不能浪费人民的钱。现在看来,那时确实有一股“傻”劲。
第二个暑假,学校安排中国学生去乌克兰首府基辅旅游。接着又应我们的要求,组织我们去莫斯科郊区一所集体农庄参加劳动。
乌克兰的语言与俄语有部分词汇互不相同。我国山东话与普通话也有差异,如把肥皂叫“胰子”,山芋叫“地瓜”,但书写时,还是都用普通话。在乌克兰,这些差异就在单词拼写上表现出来,与俄语不同了。我们看当地的报纸,得连读带猜。
在基辅,由当地共青团接待。除了参观一些景区,还让我们参加少先队夏令营在郊区森林中的集会,以及工厂职工的联欢会。我们还到一个民用小机场去坐游览飞机,每人10卢布,可在基辅上空绕2圈。那时,我们都还没有近距离接触过飞机。游览飞机由退役军用双翼、螺旋桨式小型运输机改装。机舱里有长凳可坐10人。飞行员是退伍空军老兵,卫国战争期间参加过对德国人的空战。

作者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牌坊前
列宁像下文字“向着共产主义胜利前进”
集体农庄离莫斯科大约一小时的车程,14年前,卫国战争危急关头,曾被德军占领。中年庄员们常常向我们用德语表演当年德军的粗暴言行。我们大都住在放了假的小学教室里。部分同学则分散住到庄员的家里。庄员的住宅外面用原木垒起当墙,木板盖顶,像童话小说描写的一般。室内十分整齐清洁,床罩、台布、沙发一应俱全。大型收音机(电子管式,半导体还没有推广)一直在播音。那时,电视还是珍稀商品,而且只有黑白的,高档场所才能看到。农庄里有奶牛牧场,牛奶每升才1个卢布。
学校除了安排远距离外出,还组织莫斯科市郊一日游,如参观博物馆、克里姆林宫和名人故居。我们到过列宁博物馆、农业展览馆、柴可夫斯基故居等处。导游介绍:柴可夫斯基讨厌交际,住宅门口始终挂着一块木板,上面写着:“主人不在家,请勿打铃!”实际上,他正在屋里埋头创作。学校还邀请知名人士给留学生做报告。如当时流行小说《卓娅和舒拉》中2位主角的母亲、卫国战争时期的空军战斗英雄、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姐姐等。
通过校外一系列活动,我们逐渐增加了对当时苏联社会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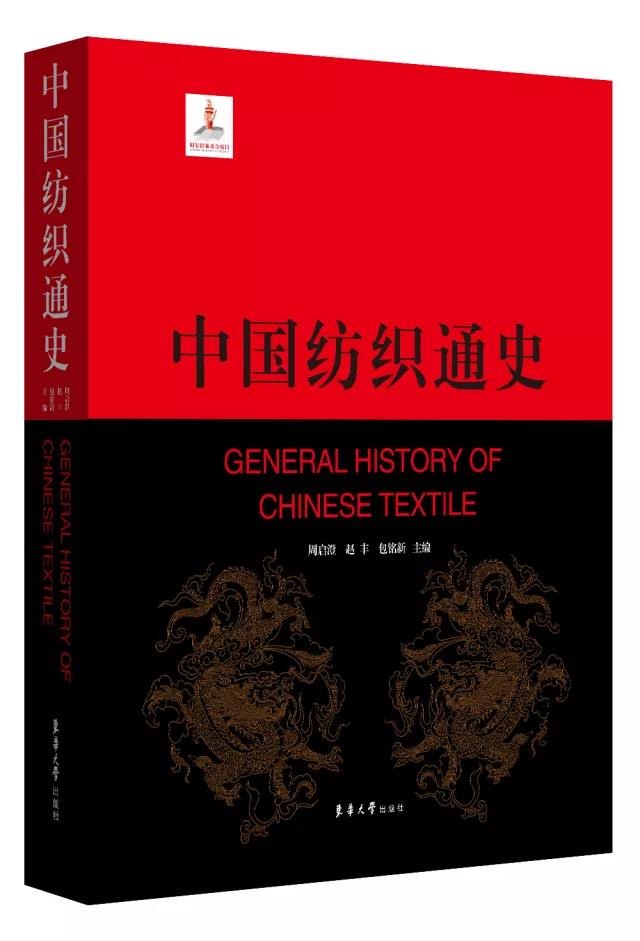
来源:东华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