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段时间,说话不离书。
本也不稀奇,做书者,以书为生,甚或生而为书,须臾不离书才对!然事实也并非总是如此! 一则做书得先做人,什么样的人决定了做什么样的书,学会跳出做书的视域观照书的种种,会有不一样的感悟;二则当下书人甘坐冷板凳的少,赶熙熙攘攘的场子的多,对书的本质为何失了定见,多有迷离。由此,书业之内,说话不谈书,也并非不是常态!
好在每每到了年终,书们又回来了。
先是一波一波的好书评选、推荐,有官方的、媒体的,也有出版机构自家的,此时气氛最浓。再是编辑、出版人也到了自我总结的阶段。要总结,自我表功也好,自我批判也罢,离开书,你能谈个什么呢? 此外,纷纷扰扰的一年即过,静下来读点书、充个电,说到底也是一种功课,读书虽说不上有多神圣多光彩,但总比压根儿不读书让人踏实一些。
浙大出版社自然概莫能外。
前阵子小伙伴们搞了年度好书评选,500进50,50进20,请专家评,请读者评,结果得到好评不少,好评多集中在对坚守学术精品出版的鼓励和赞赏上,这似乎一下子捡回了不少做书人丢失了的尊严。翻看翻看那最后的20本甚至之前的50本书,也有种“这一年总算没白过”的满足感,有同行同道看到了书单来要书,似也比以前有更多的欣欣然。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度好书(学术文化、大众读物类)
|
学术文化 |
|
中华礼藏 |
王云路 总主编 |
|
敦煌画研究 |
[日]松本荣一 著
林保尧 赵声良 李梅 译 |
|
良渚文明丛书 |
刘斌 方向明 王宁远 等著 |
|
剑桥日本史(第3卷):中世日本 |
[美]山村康庄 主编
严忠志 译 |
|
蒋礼鸿全集 |
蒋礼鸿 著 |
|
民主社会中的科学 |
[英]菲利普·基切尔(Philip Kitcher)著
白惠仁 袁海军 译 |
|
解释学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 |
克里斯蒂娜•娜丰(Cristina Lafont) 著
何松旭 朱海斌 译 |
|
心智、大脑与法律:法律神经科学的概念基础 |
[美] 迈克尔·帕尔多(Michael S. Pardo)
[美] 丹尼斯·帕特森(Dennis Patterson)著
杨彤丹 译 |
|
帝制中国初期的儒术 |
朱维铮 著 |
|
现代性的想象:从晚清到当下 |
李欧梵 著 季进 编 |
|
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 |
敦煌研究院 编 吴健 主编 |
|
思想与艺术 |
周天黎 等著 |
|
加缪手记(精装版) |
[法]阿尔贝·加缪 著
黄馨慧 译 |
|
大众读物 |
|
新金融,新格局:中国经济改革新思路 |
巴曙松 著 |
|
聚变:商业和科技的前沿思考 |
吴晨 著 |
|
对话最强大脑:精英眼中的未来世界 |
李大巍 著 |
|
歌集:支离破碎的俗语诗 |
〔意〕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 著
王军 译 |
|
身边的世界简史:腰带、咖啡和绵羊 |
[日]宫崎正胜 著
吴小米 译 |
|
植物的生命之书:写给花的情诗 |
[法]西多妮·加布里埃尔·柯莱特 著
姜富霞 编译 |
|
天堂之旅:六道风味品中国 |
[德] 马可斯•赫尼格(Marcus Hernig) 著
王丽萍 译 |
三年一度的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也公示了。继上届(2016年)首度入选1种图书正式奖之后,浙大版这次也入选1正式、1提名,算得是历史上最好成绩。恰巧这本获得正式奖的图书英文版也由国际知名的麦克米伦出版社从浙大引进出版。这样,一套多年前策划出版的丛书,因有了这些耀眼的亮点,就有了比较完美的收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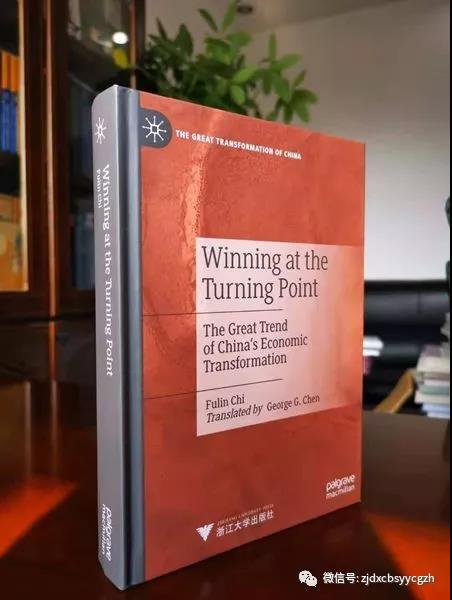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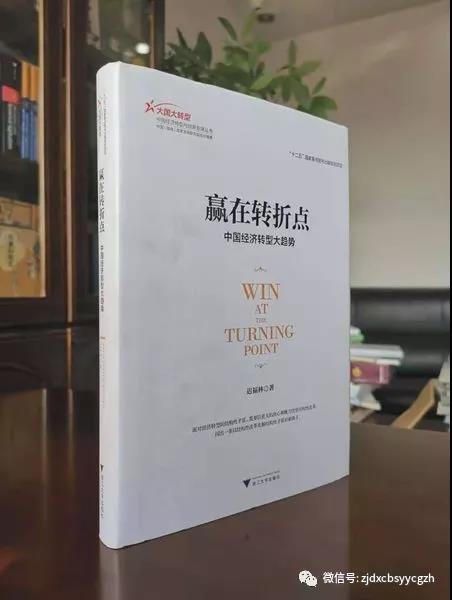
还有可以一说的是,今年是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历代绘画大系”出版成果较丰的一年,《明画全集》《清画全集》《先秦汉唐画全集》均有新品出来。近期《宋画全集》第八卷增补本又出了2册,真是令人欣喜之事!
大型古典文献集成《中华礼藏》最近也出来了十来册,虽比计划少了一些,但因调整了出版策略,无论书的品相还是内容,都有了明显的提升,认可度应该会更高。当然还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敦煌画研究》、从剑桥大学引进的《剑桥日本史》第三、五卷也于近期陆续出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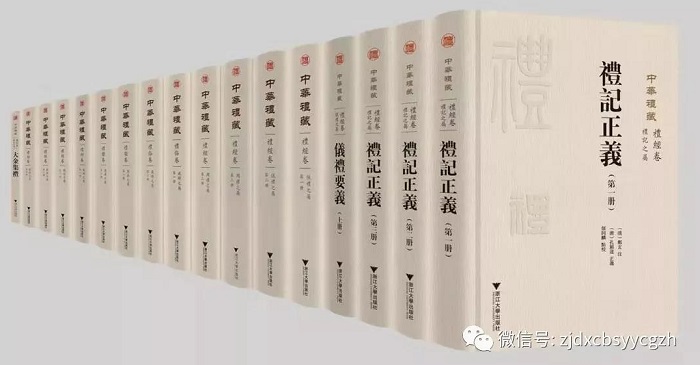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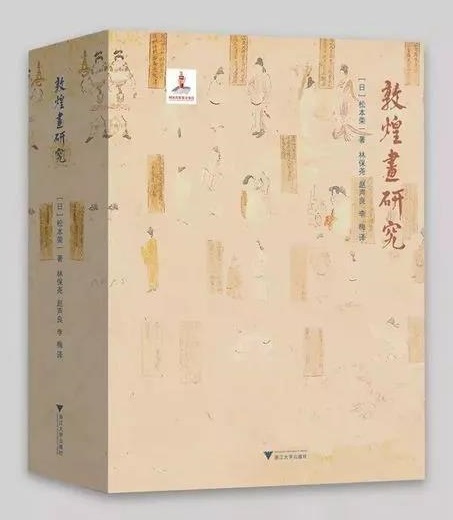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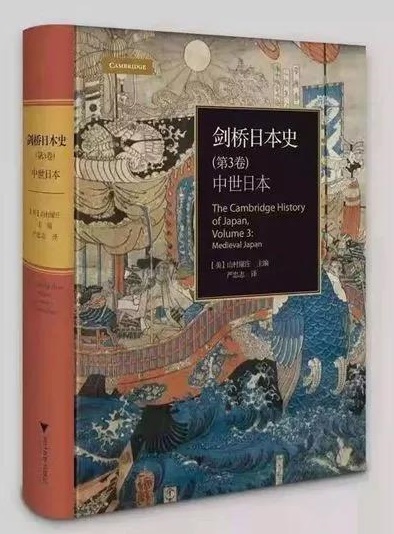
身处日渐萎靡的书业,业务关系不顺、管理效能不彰,烦忧的事委实不少,惟有书是兴奋剂、也是清醒剂,看到一本本好书入库、摆上书架,再不好的信息也不再让你沮丧,再扯不清的事情也不那么能扰乱你心智!所以,真得向做出一本本好书的伙伴们致个敬,也许还可以向终究没有沉沦、没有偏离过方向的自己致个敬!
今天坐高铁上京城,参加全国编辑学会的年会暨理事换届选举。火车上也带着两本可以轻松读的书。
一本是著名经济学家王则柯老师赠阅的,写他自己年少时求学的经历,不用经济学和数学知识就可轻松阅读。发了个朋友圈,说是看了书中“不敢碰手”一篇,忍不住捧腹。王老师回复了一条:“病中偷懒没读清样,句子不通半百。歉甚!” 老师是苛责自己了,虽作者文责自负,然句子通与不通,编辑还是要负起该负的加工之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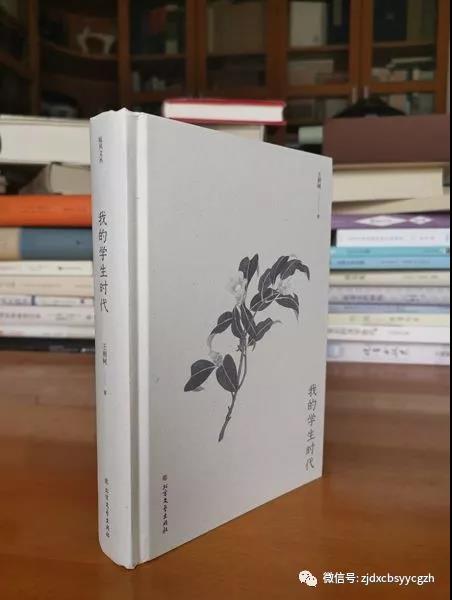
另一本是浙大版郑培凯先生著的《高尚的快乐》。前次郑先生来杭州,陪他吃饭,我为了找话头,跟他笑说阅读他的书也很快乐,有人来问我要他的书,我书也送得挺快乐。但有点不诚实的是,当时并没看完这本书,翻读了三分之一不到的样子。这次趁出差就带着再读读其余的内容。读了几篇,兴味依然浓厚。所谓“高尚的快乐”者何?书中说,康德把艺术分成两种:为了感官享受的“快适的艺术”与提供反省快乐的“美的艺术”,前者“单纯以享受做它的目的”,后者则是“一种意境......虽然没有目的,它仍然具有促进心灵诸力的陶冶以达到社会性的传达作用。” 按此定义,读书,当也算是“高尚的快乐”了吧?
郑先生的书还对“每下愈况”与“每况愈下”的意涵作了辨析,说鲁迅曾批评章士钊误用典故,批错了用“每下愈况”之人,事实是,两种用法表达不同的意义,只要用对地方,都可以用的,章士钊是吹毛求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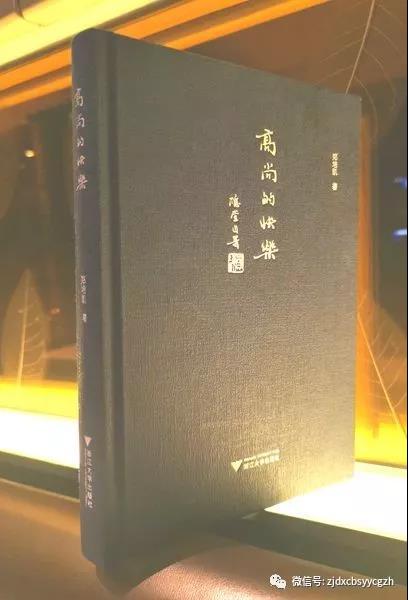
关于读书,郑先生讲到,陈寅恪先生曾作诗云:“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意思是,自己天生是能独立思考的读书人,读书是为了自己,为了寻找人生的意义而已,并不是为了别人,为了功与名。当然,陈寅恪先生是大师,禀赋异质,一般的的读书人还是有一些功名追求的,所谓“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无可非议,但不同的是,心性情致更高远者,越过了用知识换来温饱的阶段之后,依然能坚持读无用之书,以独立的思想来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而“禄蠹”则永远不能!
说来有趣,昨天有幸承蒙崔巍院长茶约谈书。崔导是著名舞蹈艺术家,大家都知道,但她酷爱读书,大家未必知道。当我谈及,有不少家长要我给他们的孩子推荐阅读书单,我一概回答:先读中外经典名著,没有比这个更划算有效果的了!文学即是人学,读莫泊桑的《项链》,就让人懂得有时虚荣是要付出一辈子的代价的,但付代价的过程也就是人格完善的过程! 这一说,就把崔导的经典瘾阅读给”催“了回来,原来她少女时代几乎把所有的经典名著都读遍了,在我脱口而出讲到莫泊桑的《项链》之前,她已经把这个经典无比的短篇作为案例,对她的“学生”们开讲过多次了! 多巧啊,我想,《项链》等等经典的阅读,一定是成就今天的崔巍的重要“催化剂”之一吧! 可见,无用之好书的阅读,似阳光空气,不能果腹,却能让人活得更有风骨!
读书如此,做书当亦如是!
来源:浙江大学出版社 袁亚春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