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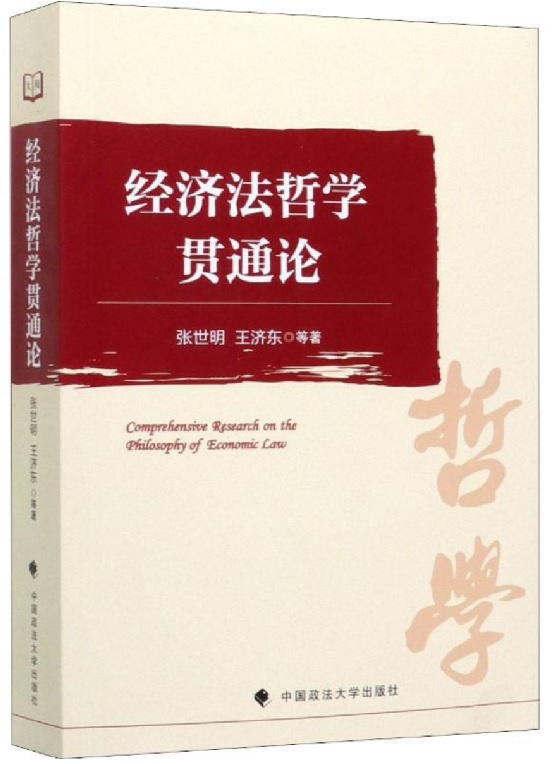
《经济法哲学贯通论》 张世明 著
黑格尔把哲学看成是人类文化的基石,他在柏林大学讲授《小逻辑》时,建议柏林大学应当把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摆在所有学科的首位。在黑格尔看来:“一个国家没有哲学,就像一座雄伟壮观的庙中没有神像一样,空空荡荡,徒有其表,因为它没有可信仰的东西,可尊敬的东西。”唯有当人在内心中蕴涵神圣的东西,蕴涵必须小心恭护的东西,蕴涵天意神道的东西,人生才有依持,灵魂才不至于空虚。学术的研究必须保持一种终极关怀,所以笔者在拙著《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一书中强调从大本大源进行四两拨千斤式的基点式研究。
哈耶克在描述政治哲学家的定位时这样指出:“政治哲学家的任务只能是影响公众舆论,而不是组织人民采取行动。只有当政治哲学家不去关注那些在当下政治上可行的事务,而只关注如何一以贯之地捍卫‘恒久不变的一般性原则’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有效地完成他们的使命。”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改造世界的解释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即切入点和切入方式。这种解释绝非是简单的策论。强调法学实践性的霍姆斯法官在一篇著名论文中就表示了问题的另一面相,即仅仅成为大公司的律师并拥有5万美元的薪水,并不能成为幸福、伟大到足以赢得赞誉的有识之士,除了成功以外尚需其他食粮。法律较为边际的方面和较为一般的方面,恰是人们应当普遍关注的。正是通过这些方面,一个法律人不仅会成为职业中的大师,而且还能把他的论题同大千世界联系起来,得到空间和时间上的共鸣、洞见到它那深不可测的变化过程、领悟到普世性的规律。如果一个人只是个法律工匠,只知道审判程序之规程和实在法之专门规则,那么他便绝对不可能成为第一流的法律工作者,甚至如同路易斯·布兰代斯法官所言,这样的人极易成为“一个社会公敌”(a public enemy)。
德国哲学家摩里兹·石里克言简意赅地揭示了哲学对于科学的重要性:“哲学不是在各门单个学科之外或之上的一门独立的科学。毋宁说,哲学的要素存在于一切科学之中;哲学是它们的真正灵魂,而且只有借助于哲学它们才成为科学。任何特殊领域中的知识必须预设一套非常普遍的原则,并与这些原则相适应,否则它就不成为知识。” “任何科学问题都会把我们引向哲学,只要我们把问题追索得足够深远。”吴经熊认为,研究任何法则都必须把握它的哲学基础。如不能把握哲学基础,即不能了解其根本精神。
从1802年到1842年,萨维尼先后在马堡大学、兰茨胡特大学、柏林大学等地传道授业,舌耕笔耘,开设了三十多次法学方法论课程,以其清晰、流畅、优雅并且富有洞察力的讲授吸引了大批莘莘学子。除马克思这样的世界伟人之外,萨氏课堂的听讲者有不少后来也成了名噪于世的法学家,如温德夏特、霍默耶、布卢默、布尔沙迪等。格林兄弟也是萨维尼的“粉丝”,其为我们留下了一份萨维尼关于法学方法论的讲义笔记。萨维尼的这本不起眼的小册子可以说是德国后来法学发展的设计蓝图。正是这样,我们在谈论德国现代法学方法论时就必须回溯到萨维尼。在萨维尼看来,完整的绝对法学方法论应当包括:①法学的解释如何成为可能(语文性的研究)。②历史(历史性的研究)。③体系(体系性-哲学性的研究)。在该讲义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萨维尼关于法学方法论的三条基本原则,即①法学是一门“历史性的科学”(historische Wissenschaft);②法学也是一门“哲学性的科学”(philosophische Wissenschaft);③上述两条原则应当结合起来,即法学是历史性科学与哲学性科学的统一。借用中国传统的术语,萨维尼强调从“小学”入手,极精微而至广大,臻于一种以宏廓思想为意境的“大学”。萨维尼的方法论要求对法律素材进行“历史-语文学的”和“哲学-体系的”处理,其结果应当是一种“绝对的方法学”,即把“实用法学”(Jurisprudenz)提升至一种“哲学的法学”(philosophische Rechtswissenschaft),“其终极目标”应当是哲学(尽管萨维尼本人对此没有详细的考虑)。萨维尼所谓“哲学的”处理,是指把这些素材组成一个“内在体系”,这个体系不应再是法律规范的单纯“堆砌”,而应建构法律素材的普遍精神关联。这样的形式与素材的方法论关系,正好契合当时追求从康德的精神出发革新各精神科学的理想。例如,席勒于1794年在耶拿的就职演讲中曾提到,用康德精神将“饭碗学者”(Brodgelehrter)与“哲学头脑”(philosophischer Kopf)加以分殊,而谢林在1802年就期待着从科学的科学(即哲学)观察科学的有机整体。
日本人的研究也是很扎实的,他们对中国法学也影响深远。尽管日本师法德国而有许多详赡丰富的法律注释书籍,但与德国相比,日本学者的研究给人一种细碎化的感觉,缺乏一种高韵逸气,大师级人物比较罕见。德国的法学之所以发达,除了对于实用法学较为关注之外,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是一种“哲学化的”(die philosophirende)法学。这就是萨维尼在方法论讲义中强调的哲学层面的思考。正如萨维尼所言,注释性因素与体系性因素的结合,使法学方法走向完美。萨维尼在这里实际上已经为德国法学发展确立了纲领,他的讲义可以说是德国法学发达的最好解释,揭开了一个国家的法学“大脑”是如何发育起来的秘密。
学术仿佛在平路上走,理论仿佛在山路上走;学术走了十步,理论才可能走一步;学术不易倒退,而理论却极易倒退。德国诗人海涅在《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Deutschland-Ein Winterm rchen)曾说过:“法国和俄国拥有大陆,英国拥有海洋,无可争辩,德国占有思维的空间。”(Franzosen und Russen geh rt das Land Das Meer geh rt den Briten Wir aber besitzen im Luftreich des Traums die Herrschaft unbestritten)德国人是如此喜爱并善于运用理论思维,并且创造了许多丰富而又深刻的思想,所以德国也被称为“心灵的王国”。康德亦云:“德国人是根,意大利人是顶,法国人是花,英国人是果。”这根深深地根植于大地的土壤之中,汲取着大地的乳汁,滋润着德意志民族的灵魂。德国法学之所以能够戛戛独造,就在于其具有深厚的理论支撑。反观我国,未来贡献给世界的,不仅应包括硬实力,还必须拥有思想的创造。“新松恨不高千尺,只为根基尚脆弱。”在当下的经济法学研究中,由于思想的退隐,思想已经成为稀缺资源,看似繁花似锦的背后,蕴藏着花果飘零的隐忧。理论贫困的根本在于哲学的贫困。经济法研究缺乏理论深度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学者看问题不能提升至哲学的高度。互联网经济一时兴盛,学位论文尽往这方面钻,以至于将天际浮云误认为是地平线上的丛树。第三方支付、网络消费知情权、互联网金融,连篇累牍,令人产生视觉疲劳,而基础性研究则鲜人问津。热火朝天之后往往是风卷残云。这些时髦玩意最多各领风骚数年,最佳也就是很快沦为有“学术史上的意义”而不再有“学术意义”的作品,等而下之者则朝花夕死,不胜浩叹。
伯特兰·罗素曾说过:“当有人提出一个普遍性问题时,哲学就产生了,科学也是如此。”“提出普遍性问题就是哲学和科学的开始。”对于本书的主题问题,元理论坐标的确立是首要的,也是实质性的任务。理论越是具有一般性和概括性,其威望就越大。任何一个学科,研究到最后都是哲学问题。由于近代所有学科的博士都被冠以“Ph D”的名号,学术总需要陷入一种本源性沉思,所以法学界各个部门法的不少学者都致力于宪法哲学、刑法哲学、民法哲学等体系建构问题。然而,仅仅以某部门法之名冠以哲学的后缀,就形成某部门法哲学,这种构想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确切的。何为经济法哲学,这的确是一个须要直面的问题,不是凭着一时感情冲动的抢帽子游戏。严肃的部门法哲学应该采取的路径是,对于哲学怀揣高山仰止的敬畏,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所谓“心向往之”,是指采取哲学的方法趋向于哲学问题。因此,我们探讨的不是在哲学之下探讨部门法问题,而是部门法之后的哲学问题。哲学之下的以哲学观点指导部门法研究仍然是以部门法问题为对象,而不是深入部门法问题之后,因而是形而下的器,不是形而上的道。易言之,不是“meta”问题(元问题、“之后”问题)。相对于部门法而言,部门法哲学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即是“之下”与“之上”的问题。部门法哲学最深层次的还是“纯哲学”,即哲学的本体部分,而基础理论是对部门法的构建,是法学,但还不够哲学,还没有达到不能再还原的终极的原点。它本质上还是部门法,而没有超越部门法。经济法哲学不等同于经济法基础理论。经济法哲学是法学基础理论中的“元理论”,可谓是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基础。经济法基础理论是经济法内部的“家务事”,至多涉及经济法理论的哲学基础等问题,而经济法哲学对于经济学而言,既入乎其内,又超乎其外,是对经济法基础理论本身的再反思,即“思想之思想”,否则将辱没其神圣使命,而与一般的经济法基础理论泯然无异。之所以要探讨经济法哲学,就在于其是一块具有学术投资价值的洼地,可以使得研究者和整个学科的思考跃升至一个“思想高原”。这不是在某种主义照观下或者在某种视域中的从大前提至具体结论的演绎,而是立足于经济法而积极抽绎、升华至哲学层面的问题研究,是从经济法中提炼出的哲学结晶。我们之所以不安本分地进行探索,就是不愿意故步自封于经济法本身框架内的问题。张立文的“和合论”虽然存在争议,但这确确实实是一种哲学理论的建构。刘文华的“公私结合论”亦然,即便未遑绵密论证,起码具有这种哲学化气概,“云彩之上的天空是一样的灿烂”。学生之辈总不该画虎不成反类犬。在德国,与法哲学最不易划界的学科是“法学理论”(Rechtstheorie)。法学理论,又称“一般法学”(allgemeine Rechtslehre),作为一门学科从哲学中迁出是非常晚近之事,产生于19世纪初。德国学界所谓的“法学理论”不将法哲学作为“法律伦理学”(Rechtsethik)所考察的范围,而是关于法和法学基本概念的分析理论,侧重于描述现存法(实在法)的概念和逻辑结构。
智小者不可以谋大,趣卑者不可以言高。晨鸡始唱,踞阜高吟。严复在点评《庄子·逍遥游》时说:学者一定要游心于至大之域,破除“拘虚”“笃时”“束教”“囿物”等各方面的偏狭,才有可能“闻道”,即达到一种主观的自由境界。形而上的研究较之简单的就事论事更为淋漓尽致。见微知著如果被理解为偏正结构的构词,那么就定然存在偏颇。这在方法论上是存在致命缺陷的,见微固然是达到知著目的的一个切入口,但并不能必然实现这一目的,见微与知著毕竟是两码事,两者之间并非是平滑的渐近线,得到的结局很可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间的壕沟需要极大的力气才能逾越。“合成谬误”(Composition Fallacy)认为个体的特质就是整体的特质,而“分割谬误”(Division Fallacy)认为整体的特质就是个体的特质。铢铢而称,寸寸而度,并不至钧必合,至丈不差。僻处草茅,可能最终未由仰见道枢。所以,见微知著在语法上是并列结构,不可偏废。柏拉图认为,哲学的最高表达方式不是直接论证,而是间接指涉。中国人也好讲登高见高。自周敦颐倡明“立人极”以来,宋明儒者的讲学不仅喜言“为学宗旨”,而且也颇重视“气象规模”,故在理论上也往往有其“整体结构”。
所有的科学都需要处理“相同”和“不同”的问题。正如生物学家理查德·莱文斯和理查德·列万廷所言:“事物是相似的:这使得科学成为可能。事物是不同的:这使得科学变得必要。”
部门法哲学实际上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相对于哲学而言,部门法哲学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是“之内”与“之外”的关系。部门法加哲学后缀的建构往往具有“拉大旗作虎皮”的瑕疵,空洞无物,是地地道道在哲学之外。这种研究往往在形式上模仿了哲学的研究,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等形式结构,但仍然是非常生硬和粗糙地移用理论而不是移用方法,有哲学思考之形而无哲学思考之实,不仅仍然“自化外于”哲学,而且脱离了部门法的内容,是“形而上学”的建构,几乎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令人无法从中汲取知识营养。相反,一些研究即便不采取哲学的名号,但圆润地运用哲学的方法解决部门法理论背后的问题,也不应该将其视为该部门法的范畴,如同法律经济学属于经济学而非法学一样,其真真切切地以哲学研究为本位,由内而外散发出哲学的光芒。经济法哲学不能过于求大、求全,缺乏独到深湛的研究、面面俱到的写作注定没有自己的鲜明个性和特色。所以,如何既“博通”又“约取”,这其中的张力,值得仔细斟酌。趋近于章太炎所说的“字字徵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这一境界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脱离了经济法的具体内容,只能泛泛而谈,难免存在隔靴搔痒的问题,讲得不彻底、不通透,没有讲到人们的心坎里去,不能以理服人,对经济法发展起不到实质的作用。从哲学、法哲学到部门法,其间尚有较大的距离和空间,需要部门法哲学作为桥梁,将两者连接、贯通起来。如若不然,部门法哲学就会混同于法哲学,难以体现出“部门法”的特定内涵,也就没有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如果把部门法哲学解释得太抽象,或理解得玄而又玄、难以捉摸,则不利于部门法哲学的深入研究,也不利于部门法自身的发展。“哲学主义”(Philosophismus)是只受哲学激励和引导的部门法哲学误区,不关心此时此刻法学对哲学提出的独特的法律问题,与特定的历史情势毫不相干。哲学可集象但不可离象。部门法哲学应该是部门法与哲学的有机结合。部门法哲学既要从部门法角度跃升至哲学层面的高远沉思,又要从哲学的角度深刻观照部门法的现实问题,这并非天马行空,其出乎部门法基础理论之外固然不易,而从哲学角度入乎部门法之中亦难。对此,中国经济法理论的建构不能依据西方的理论量体裁衣,而应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量体裁衣,部门法哲学的建构亦然,它不是按照哲学的理论量体裁衣,而应该根据经济法的实际情况量体裁衣。事实上,彻底地从部门法采取归纳法进行抽象化的萃取,绝对不可能遁入凌空蹈虚一途。这是一个理论建构和思想磨砺的进程,绝非先有成见后立学说、先架脊梁后奠基础的作业路径。
本书详情《经济法哲学贯通论》
本书系企业并购法贯通论、知识产权与竞争法贯通论的姊妹篇。作者以一贯的旁征博引,对经济法法益论、经济法秩序论、经济法正义论、经济法社会本位论、公私结合论、平衡协调论、制度保护论、目的论与结果论、人本论等经济法哲学理论进行了全面论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