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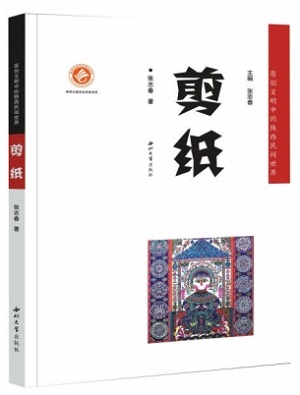
西北大学出版社《原创文明中的陕西民间世界:剪纸》(订购)
《原创文明中的陕西民间世界:剪纸》一书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切入,对剪纸进行多样态的系统研究和评说当代文化价值,着重对剪纸的人本性、仪式性、艺术性等特性予以解读。同时,从多重维度论述了剪纸在文明社会中的特殊作用,从剪纸与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对比中探讨了它对当代艺术的影响,也由巫术剪纸引发了民族实用理性等问题的新思考与辨析。
本书是陕西师范大学张志春教授在长期参与剪纸的非遗保护、非遗传承人口述史考察工作的基础上撰著,2021年出版以来,诸多媒体进行了推荐和报道。
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刊《民艺》(2021年第6期)杂志又刊登了陈曦题为《狂欢的艺术,沉重的图符——读张志春新著〈剪纸〉》的书评文章,全文如下:
剪纸的尴尬和悖谬在于,它一方面在传统中国社会的节俗和人生礼俗中承担着重要角色,几乎家家都离不开它的点缀,一方面又受到居于庙堂之高的社会上层和掌握话语权的文化精英有意无意的忽视。因为没有人真正将其作为一种艺术给予足够的珍重,充其量它就是一种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现象。以文字叙述的小传统总是要盖过以口头和图像叙述的大传统,而居于文化的主导地位,况且剪纸的创作者一般都是女性,而且是以闺房为创作平台的目不识丁的女性,所以剪纸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就可想而知了。
这种现象中体现的傲慢和偏见不仅是不公平的,有时甚至是荒谬的,当剪纸被我们的这个时代归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中的时候,它应该迎来重新解读和深入研究的春天。张志春教授的著作《剪纸》就好像是为了剪纸“正名”应运而生的,所以它令人感到尤为惊喜。虽然张教授并非第一个发掘剪纸价值的人,在他之前的几十年间也有文化艺术界的有识之士注意到民间剪纸非同寻常的意义,并且开始了比较深入的讲究,也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切入,对剪纸进行多样态的系统研究和评说,张教授恐怕是独领风骚了。
这本书既是对剪纸历史高屋建瓴和抽丝剥茧式的梳理分析,又是对剪纸的人本性、仪式性、艺术性等固有特性的深度的学理探究,还是按照文艺创作规律,对剪纸艺术家人生经历的个案分析和艺术理想的精深诠释。很明显,这需要多方面的人文素养和学理基础,张志春以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开阔的文化视野,游刃有余地解决了看似很难解决的问题,让这本书成了一部厚重的,既有学术性,又有文化性,还有文学性的奇书,它将学术论文、纪实文学、散文随笔的写作方法融为一炉,并在不同的章节各有侧重。作者的这种别样的体裁定位方式让整部著作形成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独特风格。作者将剪纸艺术放在和书法、绘画同等的高度上去进行审美关照,将剪纸艺人放在作家、诗人的高度去分析研判,既有激情洋溢的描摹和抒写,又有严谨而缜密的理性分析。从中我们能感受到一种浪漫的、洒脱的、唯美的诗意品质,也能品味到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思辨的理性力量,当然,更能体味到一种浩大的温暖的人文情怀。
看似平淡却奇崛的民间剪纸往往让这本书展现出一种思考的趣味。在说到巫术剪纸的时候,作者强调指出:“或许是实用理性的民族性思维特征根深蒂固,大传统中与超自然力量的对话也显得目的性很强,底气十足。普遍出现的巫术剪纸,并非意味着失去人的主体性而陷入非理性的迷狂,而是以另类思维驱使、强迫超自然对象来为人服务的。”剪纸中的瓜子娃娃、招魂娃娃等诸多实例都是证据。作者还讲到西安周至县的剪纸为龙以求雨的习俗,有意思的是他们让属龙男孩以擀面杖不断地戳腾龙王迫其下雨,并念叨着:戳龙王,惹龙王,惹得龙王心发慌。巧的是,《金枝》一书中也讲到中国人的求雨:“需要降雨时,他们就用纸或木头制作一条长龙,列队带它四处转。如果雨水迟迟未降,他们就撕碎或捣毁这条假龙,并威胁废黜他的神位。”通过这种有趣的现象,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中国人的求雨实际上是对龙王的利用,——你要真有用,我就尊你为神,你要不顶用,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我收拾的就是你!人有时候骗鬼,有时候还要骗神,实际上还在骗(安慰)自己。
当然,这些都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的疑惑是,虽然我们早就知道中国人习惯于利用神,他们的信仰在功利性面前随时都会崩盘。但是其他人群呢?他们难道对神只有尊重而没有利用吗?《金枝》一书告诉我们,在人类的野蛮时期,人和神的界限并不十分分明,有的特殊的人是被当做神来看的。但是他们对这些神的态度其实也是幽昧不清的。“柬埔寨的火王和水王是不允许自然死去的。因为他们中谁若患上重病,长老们认为他无法康复,就会将它刺死。刚果人相信,如果他们的大祭司自然死去,世界就要毁灭。因此当他生病很可能会死时,他的继承人就会带一根绳子或棍子到他房内,将他勒死或打死。”为什么要这么血腥暴力?因为只有如此,“人神”的灵魂才能传给下一个精力旺盛的人。这哪有什么神性的存在,赤裸裸的丛林法则而已。所有这些,不管是带有多少巫术的成分,无不是为了人的实际利益服务。如果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反观平时常挂在嘴边的实用理性的民族思维模式,好像不仅不符合客观实际,反倒是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误解。既然其他民族也均有这个特性,怎么它就成为我们民族固有的标签呢?这也许是《剪纸》一书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思考向度。
说到剪纸的艺术性,正如张志春所言,它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符号的艺术。“图像的能指与所指是人为的主观性建构,而并非必然的客观性链接。”这深刻地揭示了剪纸作为一种艺术品种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剪纸的内容和意义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比如蛇盘兔不意味着弱肉强食的恐怖,鱼戏莲不意味着自然环境的优美,抽烟和对烟不意味着对烟民动作的写实性描摹,他们分别对应的是对于富裕生活的追求,对于男欢女爱的渴望和对于传宗接代的精神诉求。这对西方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毫无逻辑的关系。但是中国人看到这些图符就会有心照不宣的心理认同。因此,如果不从符号的角度来理解剪纸,就永远看不懂剪纸。正如张志春所言,这种程式化的能指和所指往往是固定不变的。追根溯源,只能说这种特有的思维习惯来自遥远的古代,应该还是泰勒所说的幸存。
实际上不仅仅是剪纸,刺绣、布堆画、熏画等众多民间艺术,中国建筑的木雕和石雕艺术都具有和剪纸相同的符号式的思维模式,都会用固定的图符表达固定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诉求。比如蝙蝠寓意幸福,桃子寓意长寿,牡丹寓意富贵,鸳鸯、并蒂莲代表夫妻恩爱,百合、核桃代表百年好合,石榴、莲蓬代表子孙兴旺等等。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形成了民族的长期的文化积淀,可见,不了解文化特性,也就不了解艺术特性。这种思维惯性也浸透到中国的国画当中,比如,表现梅兰竹菊四君子的画作,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它们特别的、固定的寓意。
人们对剪纸艺术性的感受还在于它的多视角、多向度、多时空的表现手法。正如书中所说:“作者的目光好像全能叙述者的目光、神灵的目光一样,穿透一切空间建构,超越现实中的障碍,至于在一个空间里,时间可以浓缩状态呈现,譬如不同时间的花卉荷菊梅兰同时绽放,或同一枝杆上舒展不同的花叶,结出不同品种的果实;甚至一个事件不同时段的情节比并而出,瞬间爆场,在剪纸世界中更是司空见惯。”这种论述准确地概括了剪纸艺术性的一个本质特征,我将其概括为“全视角构图,全时间叙述”。每一个剪纸艺术家实际上在创作过程中好像都成了一个具有特异功能的人,能从一个物体的正面看到侧面和背面,从表面看到内部,从此时看到彼时,从现在看到未来。甚至她们都是一个个无所不能的神,可以对人间事项、现实物体任意安排和调度,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任意调序和穿越,只要是符合她们的主观意愿即可。所以剪纸表象是唯物的,本质是唯心的。剪纸就是典型的“相由心生,境随心转”的艺术实践活动。
人们总习惯于将西方现代艺术和中国剪纸进行对比,这当然是有充足的理由的。但是这种对比的目的是以现代艺术的高大上来烘托剪纸的文化价值,这在发掘和普及剪纸知识的时候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实际上是缺少自信的表现。西方的现代艺术是在曾经辉煌的写实传统基础上求新求变的结果,而中国的剪纸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延续至今,所以说,是西方的现代艺术靠近了中国的剪纸,而非中国的剪纸靠近了西方的现代艺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某剪纸艺人是中国的毕加索,不如说毕加索是中国的某剪纸艺人。
中国的剪纸老太太们从几岁开始就在搞“现代艺术”,他们的妈妈、奶奶、老奶奶从来都是这么搞,只是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艺术归纳为“野兽派”“立体主义”或者“超现实主义”而已,更没有觉得自己的艺术有多么“现代”。毕加索从小都有良好的美术教育条件,是在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宽松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而中国的老太太们大字不识一斗,普遍在饥寒交迫和缺少做人的尊严的窘境中长大,她们是在做饭、种地、织布间歇中,单纯靠着自己的悟性、老人的口传和剪纸的花样来从事自己的剪纸艺术的。实际上,她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从事的是艺术活动,就像前文所言,他们是为了生活而艺术,为了具体的张贴悬挂剪纸的实际需求而艺术。只是到后来,她们剪着剪着就爱上了,就当做心灵的寄托了。
毕加索们的作品是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传统的反动,是一种成熟的艺术发展到瓶颈期的自然突破。他们不愿意在传统透视法上耗时费力,他们不满足于固定的透视点,而要实现多重透视。他们不满足于自然界的色彩,而要自造属于自我意识的特有的色彩。他们有时候把在研究原始艺术时获得的灵感加以发挥改造,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是所有的这些对审美疲劳的西方人来讲属于戛戛独造的“天才”之作,在中国的大地上年常日久地存在了几千年。正如高凤莲所言,她的飞虎和飞马是从天上下来的,所以就要四蹄飞扬。她们的艺术是天马行空的艺术,是灵感的机关一旦触发就飞天入地,横扫四合的艺术,不是一般的学院派艺术家可以望其项背。因为学院派的思维轨迹和她们的思维轨迹没有交叉点,正相反,越是学院派,有时候反而越会受到局限,有谁见过用美声唱法能唱好陕北民歌的吗?《剪纸》一书中提到了剪艾虎的高金爱,人们担心她真的到动物园里看到了老虎,她就不会剪老虎了,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她剪的虎是意念中的虎,是生动活泼、可以任意变形的虎。
其实剪纸这种写意而非写实的艺术表现思路是中国艺术传统的一大特征,只是它表现得更加强烈,更加率性,当然也更加原始、质朴和自然。文人雅士的艺术到了成熟的阶段,逐渐地就会产生某种惰性和套路,就需要创新和突破。而剪纸这种完全来自民间的古老的“土物”为这种创新和突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和底气。泰勒曾经提醒我们,“有时候古老的思想和实践会重新爆发,由幸存转变为复兴。”作为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民间艺术,剪纸这种幸存技艺没有因为革命而被连根拔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幸事。它现在正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它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来源:西北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