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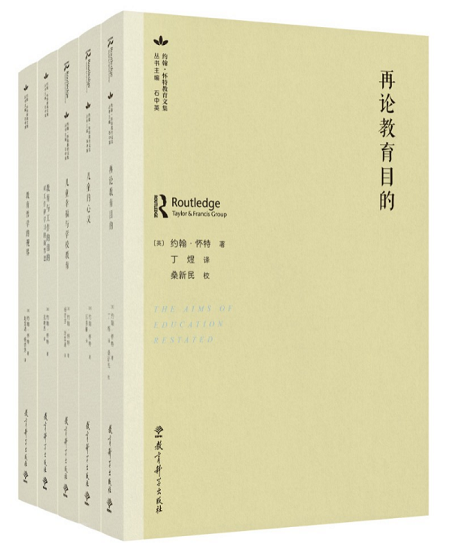
《约翰·怀特教育文集》(订购)
教育科学出版社
《约翰·怀特教育文集》涵盖了英国当代著名教育哲学家、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荣誉教授约翰·怀特的代表性著作和主要研究论文,共包含五个分册,分别为《再论教育目的》《教育与工作的目的:对工作和学习的新哲思》《儿童的心灵》《儿童幸福与学校教育》《教育哲学的视界》。在这些著作和文章中,约翰·怀特以引人入胜的语言探讨了学校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什么、何谓受过良好的教育、如何理解儿童的心灵、工作在个人生活中应居于何种地位等重要问题,为我们的教育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多元视角,能够促进从事或有志于从事教育工作的读者更深入、周全地思考各类教育现象和问题,启发和改善教育实践。
本文为约翰·怀特教授为《约翰·怀特教育文集》撰写的丛书序言。
我很荣幸有机会为《约翰·怀特教育文集》撰写序言。这套文集囊括的中文版著作和论文对应的外文版著作和论文是我在教育哲学领域主要的研究成果,它们的问世时间集中在1982—2016年。未来,它们将悉数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对此,我的内心充满感激和期待。我希望这套文集能够引起中国的教师、教育学专业的学生、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决策者的兴趣。我们生活在一个距离日益缩小的世界中,这使得跨越国界乃至洲界分享思想的机会日益增多,我很高兴目睹这一切并亲身参与这一全球性变革。我年轻时身处一个半封闭的族群之中,周围所见皆是白人面孔,很少能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交流并建立联系,来自东亚地区的朋友更是一个也没有,那时的我无法想象在我的有生之年人们的视野可以像今天这样开阔。
这也是我得知石中英教授意欲组织翻译并出版这套文集时非常高兴的一个原因。石中英教授现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也是中国的全国教育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我和石中英教授已认识多年,我一直对他怀有很深的敬意。2000—2001年,他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2014年与伦敦大学学院合并,更名为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访学时我认识了他。非常感谢他牵头组织了这项并不轻松的文集翻译工程,积极推动这套文集出版。
除了感谢石中英教授之外,我还想感谢李玢博士。李玢博士是教育科学出版社的前社长,也是《再论教育目的》(The Aims of Education Restated)早期中译本的责任编辑。她于1989—1990年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做访问学者,那时我经常看到她,也正是她激起了我想要更多地了解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的欲望。在这里,我也要向李永宏、沈昌胜、刘瑀、励达广和桑新民教授等人表达感谢,感谢他们为《再论教育目的》早期中译本的出版所付出的种种努力。
《再论教育目的》试图用哲学的视角探讨学校教育的目的应当是什么以及不同的教育目的之间如何关联。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本集中探讨“教育目的”这个主题的专著,这也许会让人感到惊讶。我在该书开篇部分批判了当时一个主流的观点,即教育具有内在目的,其与出于自身之故而追求有价值的活动有关。我接着探讨了教育在帮助人们创造条件,使每个人都能过上一种充实的生活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以及这些意味着什么。我在这本书中指出,教育不仅要关注个体的幸福,还要关注整体的社会福祉,这与此书的一个主题有关,即教育的经济目的应当是什么以及这类目的怎样与增进人的幸福相关联。该书的另一个主题是在一个目的——在逐渐扩大的范围内促进人们对他人幸福的关心——的指导下开展教育,例如,首先在家庭和当地社区中开展道德教育,进而扩展到国家层面的公民责任教育等方面。就道德教育的途径而言,英国的一些理想主义者和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对“社群关系”的重视启发了我,具体内容可参见我与彼得·戈登合著的《作为教育改革者的哲学家》(Philosophers as Educational Reformers)一书。在《再论教育目的》这本书中,我用了很大的篇幅论述各种教育目的之间的关系,包括个人的目的、道德的目的、经济的目的和公民的目的。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对受过教育的个体整体形象的描述。这又引出了其他一些主题,例如灌输、终身教育以及是否针对不同的学生应该有不同的教育目的等。我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探讨了教育目的的实现途径,这不仅涉及学校以及其他教育机构可以做些什么,也涉及整个社会需要做出哪些改变。
1997年,我出版了《教育与工作的目的:对工作和学习的新哲思》(Education and the End of Work:A New Philosophy of Work and Learning)一书,感谢沈阳师范大学迟艳杰教授着手翻译这本书。在这本书中,我进一步阐述了我在《再论教育目的》中提及的教育的经济目的,尤其是职业目的。此外,我还讨论了教育应当在使年轻人为今后的职业生活做准备方面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工作在生活中是否最优先,因而可以排在一切活动之首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首先澄清了工作的本质。很多工作都是有报酬的,有一些工作是我们不得不去做的。然而,并非所有工作都是如此,比如,一位热爱写作的业余作家夜以继日地写小说和写诗。在论述了不同工作有所区别之后,我就工作在生活中的地位展开了分析,探讨了汉娜·阿伦特等哲学家的观点。很多哲学家都认可工作在生活中居于中心地位的观点,多数人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这些观点反映了一种现象,即由于受到新教工作伦理的影响,在英国和北美等地的文化中工作都处于中心地位。但是,工作处于中心地位是对的吗?我们应当将活动而非工作视为我们人类本质的核心吗?这些导向了对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工作的前景以及教育在其中所要发挥的作用等问题的讨论。未来我们应该走向何方?是强化工作文化还是想办法用某物取代它?如何把以工作为取向的目的与让人们过上自主而幸福的生活这个目的关联起来?学生的学习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以功课为中心,尤其是他们不得不做而且往往不愿意做的功课?有无好的替代方案?
接下来要介绍的书是《儿童的心灵》(The Child’s Mind),感谢首都师范大学邵燕楠副教授把它翻译成中文。这本书反映了我在教育哲学领域中除了教育目的之外另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人类心灵的本质及其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当谈及心灵及其功能时,我们也许会认为它们完全属于心理学(一种实证科学)的研究范围,但其实也可以从哲学层面反思这类主题。哲学层面的反思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对自己所熟悉的一些相互关联的观念的非实证性反思有关。这些观念包括:“思考”“感到疼痛”“感到愤怒”“想要去做某件事”“运用想象力”等,而统领这一切的是“心灵”。这本书力图表明,明确这些观念对于弄清楚儿童是如何学习的非常重要。这本书的研究主题还包括:儿童如何学习概念,儿童如何形成信念、理解能力,儿童如何掌握知识和技能,技能是否可教,智力的本质及其测验,儿童情感的发展,儿童通过学习变得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激发儿童的动机……。这本书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对儿童的心灵做了非技术性的介绍,无论读者有无哲学背景,应该均能读懂。
第四本专著《儿童幸福与学校教育》(Exploring Well-being in Schools:A Guide to Making Children’s Lives More Fulfilling)是由杨杏芳教授和赵显通博士翻译的。杨杏芳教授就职于华中师范大学,曾于2013年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访学,我们也是在那个时候结识的;赵显通则是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的毕业生,目前在西南大学工作,从2014年起我和他就已经在很多事情上展开了合作。感谢他们不仅翻译了这本专著,还与石中英教授合作,为整套文集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
从我写第一本教育哲学专著《走向必修课程》(Towards a Compulsory Curriculum)起,我便一直把个人幸福视作教育目的的核心,读者从我之前对《再论教育目的》《教育与工作的目的:对工作和学习的新哲思》这两本书的有关介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儿童幸福与学校教育》是对“个人幸福”这个主题的全方位拓展,它反映了我从早年开始写教育哲学著作以来关于幸福的思考是如何变化的。像《儿童的心灵》一样,这本书的语言比较通俗易懂,适合教师和其他没有哲学背景的读者阅读。围绕幸福,该书探讨了与之高度相关的诸多内容,包括宗教思想及其精神遗产,基本需求的满足,幸福与道德规范的关系,生命的意义,快乐生活的内涵,有价值的活动的含义,人们追求名声、财富与“地位性商品”存在的一些问题,等等。
除了以上著作外,这套文集还收入了由我近些年所写的多篇文章组成的论文集的中文版——《教育哲学的视界》,感谢杨杏芳教授和赵显通博士为这本论文集所做的工作。这本论文集收入了《幸福中心主义》(The Centrality of Well-being)这篇文章的中文版,我在其中简短交代了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教育哲学领域所取得的研究进展。在其他几篇文章中,我从不同的方面探讨了教育与幸福之间的联系,并提出了诸如生活的意义、文化的功能,以及学生在多数人都陷入时间短缺的情况下如何过上充实的生活这类问题。此外,这本论文集中还有数篇论文涉及“何谓受过良好的教育”“学校教育的目的应当是什么”等问题,后者尤其关注在理论和政策层面小学阶段的教育目的。这本论文集中还有一些文章反映了我对教育领域中一些流行的理论、教育活动、教育制度等的看法,比如多元智能理论、儿童哲学、学校的考试制度等。这本论文集涉及的其他主题有:人文主义对教育的影响、民主社会的教育目的、教育哲学对于政策的重要性、当今世界的经济形势对于学生的影响等。
希望这套文集的出版,能够进一步巩固中英两国教育哲学领域的研究者之间的紧密联系。特别感谢这套文集的组织者,感谢这套文集众多优秀的译者,深深感谢你们以及我的其他中国朋友们,是你们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约翰·怀特(John White)
2020年11月
本文内容节选自《约翰·怀特教育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文章略有改动。
来源:教育科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