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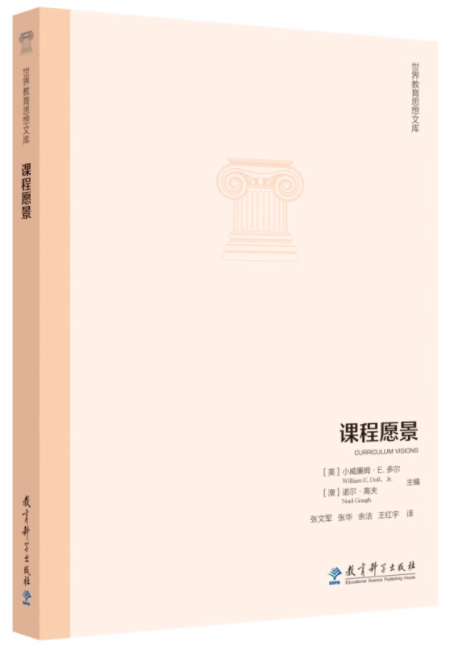
《课程愿景》(订购)
2025年6月出版
2004年《课程愿景》作为阐释西方教育科学领域尤其是课程研究领域范式转换的代表作,被纳入“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出版,成为我国学者研究西方课程研究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向、从课程开发范式向课程理解范式转换的重要参考著作之一。20年后教育科学出版社再版这本书,其价值和意义何在,请看译者之一张文军老师的介绍。
精彩试读
自《课程愿景》中文版首次面世,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的时光里,加速发展的世界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候的“愿景”现在还是“愿景”吗?再版《课程愿景》的意义何在?
《课程愿景》是一部以批判性与生成性为核心,试图突破现代课程论范式桎梏的著作。多位当代著名的课程学者,包括多尔、高夫、派纳、鲍尔斯、彻里霍尔姆斯等参与其中,开展了对课程本质,对课程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深度对话和探索。全书以多声部对话的形式,探讨了重塑课程愿景的必要性,并从课程的动态性、文化张力、具身性经验、生态转向、课程创生及内在使命等多个视角呈现了课程愿景建构的多种可能性。
高夫和多尔撰写的导论给其他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反思和建构课程愿景提供了基本的框架。高夫以威廉·布莱克与艾伦·金斯堡的诗歌为引,揭示了“愿景”的深层内涵。他指出,课程愿景绝非简单的未来蓝图,而是对现实的批判性洞察,其核心在于揭露社会中隐藏的痛苦与不公。他借用金斯堡《嚎叫》中的诗句(“我看到我们这一代最优秀的心灵被疯狂、饥饿、歇斯底里所摧毁”)来提醒我们,真正的课程愿景需直面现实的荒诞与断裂,而非沉溺于理想化的乌托邦。高夫进一步区分了“愿景”的两种形态:一是工具性愿景,即作为组织目标的规划;二是批判性愿景,即哈拉维所言的“揭露那些已成定论之物的混乱和谎言”。他号召作者们在构思各自课程愿景的过程中重视批判性愿景。他还通过电影《银翼杀手》,探讨了如何通过不同的视角和框架来重新审视课程中的“演员”(学生、教师等),并提出“如果我们把处在边缘的学生放到‘屏幕中心’会怎么样?我们的镜头在面对演员的时候是怎样‘定格’的?”等问题,引导读者思考如何通过课程愿景来关注那些在教育与课程中被忽视的问题和群体。他强调,课程愿景并非遥不可及,而是蕴含在当下的行动和存在中;倡导大家通过批判性和创造性的回应,探索可能的未来,而不是将未来的愿景强加给现实。
多尔的导论则以“幽灵”为隐喻,解构了课程的现代性根基。他指出,课程(curriculum)的词源“跑道”暗示了控制与秩序的传统逻辑,这种逻辑在16世纪拉米斯的“知识地图”与19世纪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中被不断强化,最终将教育异化为“工厂流水线”。他认为,杜威的幽灵始终在美国课程中徘徊,因其教育哲学从未被真正实现。杜威主张“教育即生活”,强调控制应该是源于情境互动的生成性的控制,而非外部强加。多尔提出,后现代课程需超越“跑道”的静态隐喻,转向动态生成。他以5c——currere(在跑道上跑)、complexity(复杂系统)、cosmology(宇宙观)、conversation(会话)与community(共同体)——重构课程框架,主张课程是复杂、自组织的系统,其意义在会话中不断涌现。
高夫与多尔的导论揭示了重塑课程愿景的双重使命:一方面,课程需如高夫所言,成为社会痛苦的显影剂,揭露权力结构与文化霸权;另一方面,课程需如多尔所倡,以生成性思维打破外部控制范式,构建动态的教育生态,从而使教育和课程成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与个体经验的觉醒场域。
在高夫和多尔的倡导下,学者们从各自的视角,用各种不同的理论与现实的棱镜考察了作为复杂系统的课程的多种面相并设想了未来的课程愿景。
鲍尔斯强调隐喻在课程建构中的核心作用。“当我们用这个隐喻而不是那个隐喻来描述事情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用这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建构现实。”西方文化长期将理性、进步视为教育的隐喻,却忽视了其与男权主义、技术控制的关联。鲍尔斯批判了“与情境无涉的隐喻”对生态关系的遮蔽,主张课程应关注“文化认知论”与自然界的依存关系,通过构想新的隐喻重构注重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关系的课程愿景。
布里茨曼以弗洛伊德的“哀悼的工作”为框架,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探讨课程中的迷失与失败。她指出课程已经成为自己的“掘墓人”,为了维护它自身,不断埋葬一些真正的知识与思想。面对课程领域的危机和濒死的状态,伤心和悲痛是没有出路的。课程研究者要进行“哀悼”的工作,和课程中那些不合理的方面道别,给“野的思想”以生存空间,然后重新出发,踏上“重新赋予意义”的旅程。派纳从自传课程理论的视角指出,把哀悼的工作和课程的濒死状态联系起来的课程愿景既是历史性的又是永久性的。他援引穆齐尔在小说语言的创新以及在理性与情感、科学与文学、表象与现实之间架起桥梁的努力,试图将“活生生的思想”和“野的思想”重新注入课程领域,使课程研究焕发活力。
作为后结构主义课程理论的代表人物,彻里霍尔姆斯引入了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的“擦除式阅读”理念,主张将课程视为“分散的和延误的”文本。他批判结构主义对显在课程、潜在课程与虚课程的机械区分,认为这种分类固化了知识的等级秩序。彻里霍尔姆斯以“跑道与奔跑”为喻,强调课程与学习过程的不可分割性,及其不断变化和迭代的特质。
科尔和奥瑞利用诗歌呈现了他们对现代课程以及以理性主义为主导的课程逻辑的批判。他们以北美原住民的口吻,通过诗歌、听觉、经验和想象来重构课程意义。通过原住民与“杜威”的对话,揭示了白人在教育原住民的过程中施加的文化暴力。在诗歌中,“杜威”试图以英语“框定”原住民的思维,却被反驳:“我们不想要tl’atl’imx语言中出现名词和动词”,因为“这没有任何意义”。
弗利纳更是结合杜威的逻辑与复杂科学理论,提出了“有机中心课程”的愿景。她主张课程应作为“有机体–环境复合体”,强调自组织性与适应性。她警示我们,如果课程仍困于知识消费的窠臼,学校将沦为精神荒原。
高夫以“全球化的长臂”这个隐喻,分析了全球化影响知识生产和课程的机制,批判了西方知识体系的霸权,指出全球化这个长臂既可以用于控制和扼杀,也可以用于拥抱。他指出,“也许全球化是另一个‘上帝的骗局’,一个超越了人类经验的,使人们觉得每个地方都是同一个地方的幻象”。在全球化长臂无处不在的情境下,保护地方知识体系,维护地方文化的生存空间,就成了课程的关键目标和使命之一。
在这种情形下,凯森与奥利弗重申了概念重构经验理论的必要性,指出需要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处理各种事务、讲故事及相关的仪式创生的经验置于课程的首要位置,通过谈话、故事、舞蹈、仪式、运动等开展课程创生。他们把这种经验理论称作“搏动理论”,将课程比作生命的脉动,倡导在教育过程中恢复“感官参与”的合法性,使课程创生成为在二元对立的现代社会重拾一体化的机制。
莫纳揭露了全球的学校商业化现象。他剖析了公共关系与广告将教育异化为商品的过程,指出“商业活动现在正在塑造学校的结构,影响学校课程的内容,并决定儿童是否能够接触到各种科学技术”。例如,独家软饮料合同与赞助性教育材料侵蚀了教育的公共性,使课程沦为利益冲突的战场。莫纳呼吁教育工作者抵制消费主义逻辑,审慎评估商业活动对于学校和学生的影响,重建“以儿童为中心”的伦理准则。
莫尔以一种类似于二元论的方式,从充满内在张力的四对矛盾,即复杂性与简单性、共同体与个体、对话与沉默、高潮与新起点出发,阐释对课程的重新理解,并通过四个c[complexity(复杂性)、community(共同体)、conversation(对话)、culmination(高潮)]构建课程愿景。
奎恩则以威廉·布莱克的艺术哲学为线索,批判牛顿式的机械隐喻。她指出传统的课程观的核心在于“致命的控制思想成为中心,强调人类对知识的全面掌控”。她主张课程应该激发想象的力量,成为精神与物质和谐统一的整体。奎恩呼吁教育者以“疯子的灯笼”照亮时代的贫乏,在技术化洪流中守护灵魂的骚动与新生,使课程成为穿过灵性和精神性森林的迷人旅程,成为精神修炼的道场。
如何看待课程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圣朱利安以狄更斯的《圣诞颂歌》为隐喻,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我们可以召唤出一种不同的愿景,但这一愿景必须由我们自己创造”。这一课程愿景需要从动态学视角去建构,注重复杂性、关联性和协作性,将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扎根于社会实践与互动中。为实现这样的愿景,教育工作者需要借助多种资源获取隐喻并创造新的意义模式。
楚特以“幽灵”隐喻课程的未完成性,批判视觉中心主义对知识的垄断。她指出,文字霸权贬低声音与沉默的价值,现代课程论的内在幽灵是柏拉图的理性逻辑而非缪斯,而缪斯对于我们建立新的课程愿景至为重要。静默和富有诗意的会话,使缪斯的精神和力量与各种可能性共舞。她以阴性书写为例,展现了身体写作和诗性表达对于避免单一意义、探索多重理解、塑造更鲜活生命精神的意义。
王红宇通过追溯休伯纳的著述和“异乡人”隐喻,探讨课程作为精神旅程的观点。她抨击了现代主义课程观对精神性和灵性的忽视、对儿童的自发性和创造性的扼杀,要求课程重视想象、意志、爱的能力的培养,并运用“异乡人”的隐喻来表征超越性的存在,呼吁在营造充满爱和关切的社区的基础上,使课程成为教师作为异乡人和学生相遇并共同探寻未知性、不确定性的精神旅程。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这本书的写作方式正如本书所倡导的那样,既像多声部的合唱,又像多主角互动的即兴生成的实验戏剧。书中的每一章都有两至三位作者,先是由主编提出问题阈,然后是该章的主要作者围绕问题阈阐释自己的课程愿景,最后是一位作者对主要作者的观点做出回应。这样动态生成式的学术对话,恰恰反映了多尔和高夫在导论中所倡导的反抗控制性的课程幽灵和工具性愿景、以一种批判性愿景观重构课程领域的方法论。
二十多年过去了,控制这一课程幽灵依然在全球的教育和课程领域游荡,并且随着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和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愈演愈烈。《课程愿景》中的反思和批判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依然振聋发聩,众多作者所倡导的注重动态性、注重生态性和关联性、注重课程的具身性和课程创生、呼吁文化的对话与共生,以及唤醒灵性和内在精神性的课程愿景对课程工作者依然富有启发意义,课程研究依然需要我们不断创设想象空间和新的愿景、方法与实践路径。
本文选自《课程愿景》教育科学出版社。
来源:教育科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