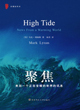 资深的气候问题专家马克·利纳斯通过一次追寻气温改变征候之旅,以一种令人瞩目的方式在《聚焦——来自一个正在变暖的世界的讯息》一书中为我们展示了有关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种种巨大危险、无可争议的事实和信息。本版选摘其中第3章部分。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最新翻译出版。
资深的气候问题专家马克·利纳斯通过一次追寻气温改变征候之旅,以一种令人瞩目的方式在《聚焦——来自一个正在变暖的世界的讯息》一书中为我们展示了有关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种种巨大危险、无可争议的事实和信息。本版选摘其中第3章部分。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最新翻译出版。
处于千万英里海洋怀抱之中的图瓦卢富纳富提环礁,感觉上就像一个小宇宙的中心一样,远离一个迅速变化着的外部世界的尘嚣。
然而,随着冰川的融化,海水的变暖,全球海平面也在缓慢上升。过去极其微小的增加量叠加起来,就产生了一种稳步累积的影响,已经开始对岛屿的生命造成破坏了。
岛上的人们现在面临着一个他们一直都害怕的抉择——要么搬走,背井离乡,背弃自己的文化到一个陌生的国家生活,要么留在祖辈开拓的土地上死亡。我在遥远的牛津家中听说他们终于做出了一个选择。
富纳富提环礁
我在图瓦卢认识的第一个人是帕尼·洛派帕,他是环境部的官员。很长时间以来,他是向世人反映他的国家所处困境的最为有力的声音之一。我曾见过他的话语被数不清的媒体引用,我也很期待进一步对他进行访谈。
“不,不,不,”他坚持说,“你必须先休息一下,我们有的是时间。”然后他就骑着他的摩托车——富纳富提岛上人人都有摩托车——匆匆走了,我别无选择,只好遵命。
天气热得有点太过分了。强烈的阳光刚刚开始收敛它的威力,我就走到外面去探个究竟。我左边100米处有个泻湖,湖边有一个窄窄的沙滩。海底有的地方是沙子,有的地方是石头,海水也相应地呈现出斑驳的紫或浅蓝。有几个女子站在水里闲谈,只有头露出泛起涟漪的水面上,神情就和伦敦的老太太们在公交车站打发一天时间那样自然。有时还有人从海水里站起身来,全副衣装,然后身上的水滴滴答答地往家里走去。她们这种几乎是水陆两栖的生活方式让我叹为观止,身上是湿的还是干的在赤道的酷暑环境下区别不是很大。
从岛的外沿到大海不过5分钟。高空中看下去,富纳富提宛如一滴泪珠,沿着环礁狭长的边缘还散布着一串小岛。平静的中央泻湖和大海之间有一些半淹在水中的礁石,其中一些较长的伸展出去,突破了环礁的外缘。从村里往湖上看,你会发现相邻的岛屿往相反的两个方向延伸,形成一条弧线。“泪珠”的两半在地平线上相交之处有一些棕榈树,看起来就像一些极小的尖朝下的图钉。
岛上有些地方形如条状,从一边到另一边仅有数米宽,而在最宽的地方,即城市和机场所在之处,富纳富提环礁的宽度也不超过500米。实际上,这个由9个小岛组成的国家陆地面积只有26平方公里。我在想,要是台风来袭的时候被困在这个地方会是什么感觉,想着想着我便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要人民离开他们的家园,这肯定是件很难接受的事情
我仍不知道即将撤离的传言是不是真的。因此,我去拜访了图瓦卢的最高公务人员帕那帕兹·纳里索尼。作为政府的秘书大臣,他是最有可能给出回答的人。
是真的,他说。图瓦卢确实在准备结束一切。
“我们总不能干坐着,什么都不做吧,”他解释说,语气温和。“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得到新西兰的同意,每年允许75人搬过去。”
“协议什么时候生效?”
“我们不大清楚,但应该会是今年。我们会尽力在今年了结一切事情,准许人民移民。”他顿了顿,然后告诉我一开始移民的人数配额是每年300人。但鉴于总人口只有1万,一次走掉这么多人很快就会让岛上人烟全无,社会支离破碎,政府的服务工作全部停顿。因此他们达成了一个更合理的数字,而且会敦促医生、教师和公务员留下来的时间长一些。
我还是不能相信我所听到的。“但要人民离开他们的家园,这肯定是件很难接受的事情吧?”
帕那帕兹又叹了口气,继续用他温和的语气说话。“确实如此。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可能会失去我们的文化,我们可能失去我们作为图瓦卢人的身份。一旦我们到了别的国家,要我们的人民接受这个事实肯定需要时间。”
我们的谈话结束时,我错误地用了“疏散”这个词。他尖锐地打断我:“并不是疏散。我们还没到要疏散民众的地步。我们知道全球变暖对我们的威胁,而政府并不想置身事外。所以这是一个移民计划,一个需要时间逐步进行的计划,它本身并不是疏散,因为疏散时需要做的是立即调动人民搬家。”
回到外面时,我发现刚刚在和帕那帕兹说话的时候已经刮起了大风。泻湖的水面起了波浪,开始阴沉下来,而不祥的乌云也正在聚集。预报说接下来几天会有今年最高的海浪。水位已经升到离政府办公室后面的泥路路沿只有1英尺左右的地方了。起伏的波浪偶尔会高过路沿,把落下的棕榈叶冲到干的陆地上。
走过泻湖的时候,我在想帕那帕兹拒绝使用“疏散”这个词是否明智。一方面,这样可以安抚民众,避免恐慌,而且对于那些在可预见的将来选择留在图瓦卢的人们来说,保持而不是破坏一个正常运作的社会也是很重要的。
但同时这样似乎对图瓦卢的危机过于轻描淡写了,而且有可能会让那些要为全球变暖负责的国家继续逃避责任。尤其是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更是铁定了心要这么做:它不仅拒绝了图瓦卢政府提出的商讨“移民”问题的要求,同时还拒绝批准有关气候变化的、约束力非常有限的《京都议定书》。
到这个时候我已来到了机场跑道顶端的一块草地。那里正在进行一场足球比赛,参与率还挺高的。约有50多个男子和男孩在追着足球,跳着,跑着,他们都离海洋只不过几步之遥。在他们和海浪之间有一个3米高的瓦砾长堤,形成了足球场的另一个边界,这是岛上陆地的最高点,是由飓风“比布”在1972年刮到沙滩上形成的。
那次风暴摧毁力极为惊人,直到今天每年的10月21日都被当作“飓风日”来纪念。我后来听帕尼称这个瓦砾堆为“霍华德山”,以澳大利亚总理命名,而且环境部里有人甚至要把“图瓦卢高山救援队”的字样印在T恤衫上。幽默与困境往往相伴而来,图瓦卢两者都不少。
那天晚上有个聚会,不过在图瓦卢只要有个合适的借口,每天晚上都会有聚会,帕尼邀请我一道去了。我所要做的只是踩着图瓦卢鼓的鼓点向巨大的马尼帕前进,这是个开放式墙体的茅草建筑,白天是这个国家的议会,晚上则兼作主要的聚会场所。舞者们以完美的节拍移动着步伐,每个人都穿着露兜叶编织的裙子,女人们还穿着精致的红白相间的上衣,而男人们除了身上有几片随意垂下的香蕉叶外都赤膊上阵。
我很快就被人发现了,结果被带到前排的贵宾椅那儿。一位看上去德高望重的老人,满头浓密的黑发,只有额头上有一丝白色,坐在我身边,开始低声地翻译这些歌曲。
我后来碰到了帕尼,他是仪式上的司仪,便问他我的邻座是谁。“那是托里皮·洛迪,1978年独立后第一任首相。明天早上你应该和他聊聊,他知识渊博,阅历也相当丰富。”
来源:《聚焦——来自一个正在变暖的世界的讯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1月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