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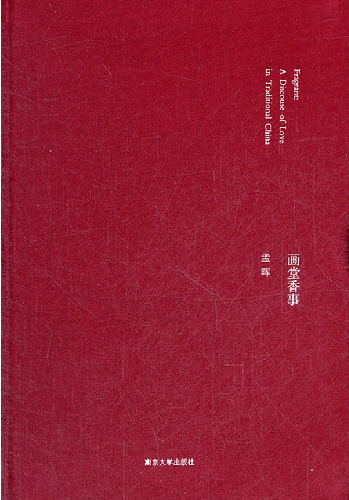

犹记张爱玲刚开始写的小说里,不是焚炉香,便是沏香片,故事还没开头,便先散放出一片香氛来。大概因为这世界太过浊臭污染,文人雅士或闺阁千金与“香”便有了不解之缘。孟晖女士这本《画堂香事》有如一只敛古小篮,将各种发生在古人身上的“香”作了收集。
这本书的好处,因为文字的简薄、配图的古雅情趣,倒使人信手翻来颇觉轻曼好读。是一个百宝箱,历数各件宝器珍玩,无一例外与“香”有关。从分类而言,全书于“香之事”、“香之容”、“香之食”、“香之居”四部分来归纳,每部分又列出各件物什,这些香玩原本只是古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却被应用于各个层面,饮食、居所、妆容、服饰、祛疾、争宠、装饰、御寒……而这些香的来源,多取自花草天然,不像如今,蒸馏技术一流的国际大都市,男女身上“穿香”都来自多重工艺和工业配方,缺了天然成份,人也少了柔软的部分。
从《诗经》中得来的植物情结:“折芳馨兮遗所思”,略带神秘色彩的芳香花草在一传一递间,已使男女芳心蠢动,时至今日的情人节,仍可见遗风愈盛,却因物质变相加剧的可能,使“送花”这一传情之举胜在数量而非心意,实在很让人匪夷所思。香,固然是香的,而且还有时间性,伴斯人而至,却不因斯人的离逝而消散,反让苟活之人闻香落泪——这又是香所犯的错事了。但大多的香,被制成香囊贴身佩戴,或藏于香屧里面、步步生香,更有皇戚贵妇沐香汤、生香炉,用产自东南亚、印度、非洲、西域等地的各种香料来描眉敷面,这一幕,在后宫争宠类的影视剧中可见一斑。再加上文学名著中巨细无遗的描绘,王孙没落前的繁华景象,或可通由女子手中的异国名香来得以映现,因为名贵,所以有材质牢固的器皿装填,得以成千上百年的湮没,一旦见光,仍能被考古学家顺藤摸瓜研究出整个世态情状来。曹雪芹举世巨著《红楼梦》中,就屡屡出现男女旖旎之情、衬以这片植物园般百般琳琅的香意来。
香,果然是外化的、充满人情味的物什,又是可闻不可见的。古人比今人更贴近自然,与植物的感情是不离片刻的,送别要折柳、传情递香花、院内植百花、言志寄花草,连爱国诗人杜甫也不能免俗的吟诵“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将有形之物制取无形之物,就是香的形成,然而这不能满足古代人执意追求雅致情趣的心理,就算再方便的做法,也是将这份香埋入食料中,消辗于唇舌之间。何况,他们还将装香的器皿、炉瓶、罩笼、香球、香屧加以工艺雕琢,来配衬香在心目当中的地位。香,是用来人际交流、调节身心的高洁物品,古人只能用手工艺的精湛来有形的呈现这份高洁,又将无形造成有形,视觉化的同时转化为艺术。
孟晖有如多年前的三毛来谈“我的宝贝”,一件件列出来,但并不罗嗦、由此及彼,慎言简语,似在摹仿一种幽香。因为它并非文学书,或是历史书,可以洋洋洒洒,更像一本画集配文,点到即止,没有多余的想象和赘语。所收之画大多来自吴友如《吴友如画谱》、佚名《深柳读书堂美人图》,以及出土文物照片、博物馆存品、各类古书籍中配图等,各种画里关于“香”的细节被拎将出来,让人化繁为简的对历史长河所沉积的文化一目了然,有如走入一个展览馆,各中情趣收获不小。
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古人已将制香的工艺从精到绝,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如书中的“香篆”,它并非一种字体,而是一种时间与香味结合的艺术,搁置画堂书房,让时间静静在空间里流淌。这是什么呢?原来,在西洋钟表还未传入之前,古人将调配好的香末倒入一种有回环花纹的花模里面,然后将模中的香粉末倒至香盘中,形成一个刚好够燃一昼夜的图纹,上面有记录时间的刻度。更绝的是,他们将模具里的粉倒至纸上,纸又放到水面上,纸会下沉,特制的香粉却不会,凝立在水面上,只需点燃,便成了水上摇曳的时钟了。大概因为这种香粉加入了粘性材质,不会被液体濡湿、冲散,又因为这些模具上的纹路多为篆体的字样,故称“香篆”吧。作者并未详细解读,倒是在扬之水先生的《香识》一书中有详细的诠释,在唐朝盛行,在两宋期间“打香印”还成为专门的技艺等等。作者有意不去复制或重复,只将你领进门,若你有意,再看他人的研究无妨。
当然,除了高洁,香在古代的野闻轶史中也充当着另一种功能,那便是男女情欲的挑拨物。《金瓶梅》里潘金莲、西门庆、李瓶儿等个中人物均受了此物的点染,细较下去竟又是一大堆的话题。由今及古,哎,古人的生活品质实在骄淫奢靡得可以,今人难以望其项背啊。
来源:范典新浪博客(2012-10-14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