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品读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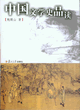
|
书名: |
中国文学史品读
|
| ISBN: | 978-7-309-05696-9/I.404 |
条码: | |
| 作者: |
鲍鹏山 著
相关图书
|
装订: | 平装 |
| 印次: | 1-1 |
开本: | 16开 |
| 定价: |
¥34.00
折扣价:¥32.30
折扣:0.95
节省了1.7元
|
字数: |
|
| 出版社: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页数: |
|
| 发行编号: | |
每包册数: |
|
| 出版日期: |
2007-10-01 |
|
|
| 内容简介: |
序一
余恕诚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几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的民族,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华民族所代表的文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记录这个民族几千年喜怒哀乐、体现这个民族几千年艺术才华的中国文学,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民族几千年来面对世界、面对自己命运时的表情;可以看到这个民族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对自身道德人生、道德实践的观照和剖析;对人性缺点与优点的揄扬。在中国文学史中,不仅有对“实有”的生活及世界的或依恋或批判,还有对“应有”的生活与世界的向往与想象。在中国文学史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民族对美好世界和完美人性的不懈追求。
由此,对这样的文学史作出描述和阐释,是一桩文化的大事业。而到这样的蕴含人类丰富情感的矿藏中开掘与炼取,找到对当代心灵的慰藉,更一直是一项充满诱惑的工作。同时,也是当代学者的责任。
通行的各种中国文学史,主要是作为教材来编写的。一般是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从对文学流派及作家、作品的阐释切入,以知识的灌输与认知作为基本落实点。这样的文学史,往往体现出强烈的传承文化的责任心,并以态度严肃、立场客观、立论科学、知识准确为自己坚定的学术追求。学术性强,理性精神突出,是其共同特点。
但是,文学史可以有不同的写法,而且,也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不同的写法,才可以展示文学史的不同侧面,勾勒出文学史的不同面貌,展示文学的多重魅力。实际上,作为描述文学现象,揭示作家内心世界,感悟作品艺术魅力的文学史,学术化的写法,在巨大的优点的背后,也有着明显的不足:过度的学术化,在揭示文学事实的同时,往往又遮蔽了文学自身的美丽;在冷静客观的学术化表达语境里,鲜活的文学自身却往往被遗弃在一边。作为认知与研究的功能突出了,而作为欣赏与感受的功能却退化了。而能否保持并提高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力,能否被文学作品感动,才是一个人的艺术鉴赏能力的天然尺度。同样,能否有助于帮助一般读者感受文学作品,提高他们文学感受的敏锐性,至少是文学史的责任之一。
另一方面,要真正实现对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的深度阐释并揭示其当代价值或普世价值,必须有思想的介入。这不仅仅因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武德语),而且,还因为,在历史学中,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只有思想才能在历史中发现思想。因为,如果没有思想的光芒的照耀,很多被学术充分而准确地揭示出的“文学事实”里,其中的价值,也仍将隐藏在字里行间,不能被我们发现。因为,“价
值”,往往是一种无形的存在,甚至,只在我们的阐释中存在。
鲍鹏山的这本《中国文学史品读》,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及价值,即是,一、体现了文学史的感性化特征;二、体现了历史学的思想性特征。
实际上,这不是一本体系性很强的文学史著作,严格地讲,它更像是一本文学史札记。但是,这五十多篇表达生动、新见迭出的札记,几乎涵盖了中国文学史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及流派。所以,已经足以架构一个文学史的框架。况且,这本文学史的结构,本来就不重线的勾勒,而重在点的描述与深度阐释。
鲍鹏山二十多年前在大学时即听我的课,这本书中的关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文章,就是那个时候写就的,算是本书中最早的篇章。二十多年过后,他又回母校,跟我攻读博士学位。其间的二十多年,他在高校任教,埋头学问,并出版过不少著作。现在,他的这本很有特色的《中国文学史品读》即将出版,读完书稿,我非常高兴。先睹为快之后,特写了以上这些话,奉献给读者。
2007年6月7日于安徽师大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序二
骆玉明
在中国,文学史类型著作的繁盛,大概是其他国度难以比拟的。或许这与中国人偏爱史学的传统有关,但另有些很实在的原因:中国文学经历的过程十分漫长,产生的作品数量极其庞大,用历史的线索来描述它的大概面目与发展变化,依照时间序列来了解和记忆作家与作品的情况,从掌握知识的角度来说,也是一种最为方便的方法。
中国文学史著作大多是以教材模式编撰的,即便有些书在写作时并未以充当教材为目标,但因为那一种模式流行甚广,成了习惯,也难免受其影响。于是,文学史著作常常会出现相似的毛病:一是照顾的面太广,有些基本的知识总是非讲不可,像一个时代的政治与文化背景呀,一个作家的主要生活经历呀;在篇章的分配上,名家名作固然占据大头,但二三流的也不好简单省略,哪怕蜻蜓点水,也要带上几笔。就怕知识不全面,读者应该知道的东西书里没有说。二是个性不突出,陈陈相因的内容太多。这当然可以指责作者的学力有问题,缺乏创见,但由于是教材模式而追求平稳,也是原因之一。我自己编过文学史,对此深有体会。有时,明明有一种特别的念头,在课堂上也讲过,写到书里就不免犹豫,怕调子奇怪,使用的人不容易理解和接受。
我们现在读到的鲍鹏山的这部书,可以说较好地避免了上面所说的文学史著作的常见毛病。它是不是也可以当教材使用暂且不论,作者没有按常规的教材模式来编写则是显而易见的。全书五十一个专题,既不按朝代也不按文学潮流加以分期,只是大略地依照时间顺序,挑出作者心目中最为杰出的作家与作品加以介绍和论析,而自然而然形成具有“史”的意味的流动。就好像在一大堆成色各异的珍珠中挑出了最漂亮的珠子贯穿成链,显得简洁而好看。
由于较一般文学史著作省略了许多内容,知识的“点”不那么密集,本书对于作品的解析就能做得相对充分一些。譬如《道德文章》一篇,选取了《孟子》书中的若干富有特色的章节,依着文脉逐层解析,论其思想主张,情感的表现,辩说的手段,逻辑上的得失,最后勾画出孟子为人的基本品格,读来觉得明白、可信且亲切,普通的文学史很难这样做。当然,这也不是篇幅稍为充裕一些就能做到的。这书总体规模不大,篇幅还是受限制的,能抓住要点,舍弃枝节,才能说得这般透彻。
写文学史要有见识,同时也要敢于坚持己见,这样才能显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譬如关于“历史上有无屈原”的争论,鲍鹏山是这样说的:
我们今天讲的这“屈原”,乃是一个“人文事实”。不管历史上——实际上也就是在楚怀王楚顷襄王时代——这个人物是谁,或根本不存在这个人,但至少从汉代贾谊、刘安开始,这“屈原”两个字就已作为一个“人文”符号而存在,并在不久得到了大史学家司马迁的认可,并为之作传。在贾谊、刘安和司马迁那里,“屈原”代表的是一种命运,一种精神,一种品性,这些东西让他们起了共鸣。而这些东西是抽象的,也就是说,他们感兴趣的就是这些“抽象”出来的东西,而不是那个已经消亡的肉体。自那时起,我们民族的记忆中就有了“这个人”,并且“这个人”还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施加了他的影响,也就是说,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人”的文化内涵越来越丰富,他的“抽象”意义越来越丰富,而成了一个无可否认的“人文事实”。
由于屈原被推崇为某种伟大精神的代表,许多人认为他在历史上必定具有如其指认的那样的真实性,否则的话,他所代表的那种伟大精神就不真实了。然而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任何“伟大精神”都代表了当下的价值,人们以此阐释历史,使“历史”成为“当下”的证明。阐释固然依据了历史提供的材料,但对这类材料的选择、推衍乃至注入新义,却是阐释活动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正因如此,西汉以来历
代文人依据同样材料所理解的屈原和他们描绘出来的屈原形象,往往面目各异。至于把“爱国”和“主张改革”作为屈原作品的核心精神,又是到了近现代才提出来的看法。而历史上的屈原(如果实有其人的话)究竟是什么样的,由于留存的史料不仅简略而且不尽可信,其实已经很难追究明白了。由于屈原的问题也像岳飞一样,牵涉太大且十分敏感,作为教材模式的文学史有时不得不迁就“共识”。但鲍鹏山却不管这个规矩,只管把他的想法写出来。他以“人文事实”这一概念来解释屈原在历史中的存在,在我所见过的论著中,我以为这是说得最妥当的。
通常说来,文学史研究亦如一般学术,重理性而轻感情。这有它的道理。但另一方面,文学本来就是情感的艺术形态,如果没有情感上的沟通、共鸣,又怎么能够激发封存于文字中的活的生命呢?没有情感的阅读,文字永远是死的。鲍鹏山是一个感情热烈的人,于人于事倘无爱憎,便几乎不能有所言。以前他在贾平凹主持的《美文》杂志上连续发表评说古贤的文章,就是以个性化的见解和热烈的情感引人注目,如今他写文学史,依然故我,无从改变。“这样的诗,真令我们心花怒放。这是一种彻底的享乐主义,享乐得如此心安理得,如此张扬而大放厥辞,不仅自己沾沾自喜,洋洋自得,而且对别人津津乐道,眉飞色舞”,这是在说李白《襄阳歌》。我们读到了李白的快乐与“大放厥辞”,也读到了鲍鹏山的快乐与“大放厥辞”。情感的特点是自以为是,它会不会影响评述的精确性呢?我想鲍鹏山会考虑到这一点。但纵使有所逸出,也不算是大不了的罪过吧。读者通过鲍鹏山的介绍与古人交友,见他说得如此动人,兴致也会跟着起来,这是开心的事情。
文学史是不是写成鲍鹏山这样的才算好?我没有那样的意思。我只是说,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文学史,跟常见的很不相同,而文学史应该有各种各样的面貌。因为我同鲍鹏山有长久的交情,不合适多加赞扬,所以主要是讲这部书的特色。
|
| 作者简介: |
|
|
| 章节目录: |
|
|
| 精彩片段: |
|
|
| 书 评: |
|
|
| 其 它: |
|
|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