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编辑出版学专业创建40周年
韶华流转,春秋更迭
四秩芳华,薪火相传
武汉大学出版社重点推荐
出版专业系列图书
《问学出版》(订购)
方卿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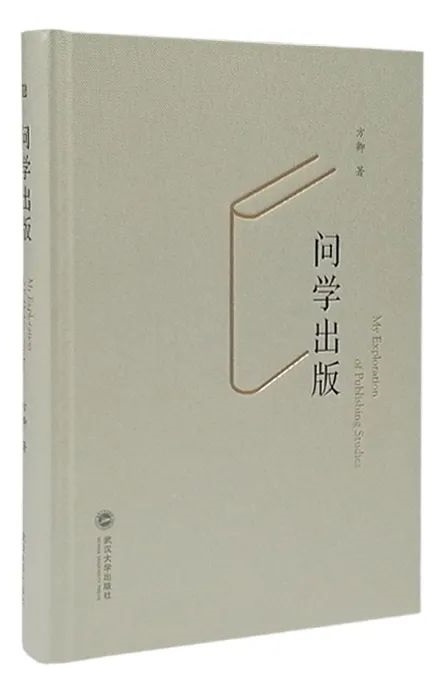
内容简介
《问学出版》收录作者30多篇文章,时间跨度近30年。文章的内容涉及出版和出版学的方方面面,早期的文章关注的主要是“图书营销”“发行代理制”“产业链”等出版产业微观或局部问题,中后期更多涉及的则是“发展战略”“专业出版”“产业资源”“出版服务”或学科建设等产业宏观或理论问题,其选题大体反映了我国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历程和出版学研究重点或热点的变迁。
目 录
代序:亲历“发行专业”二、三事
论出版学“话语权”的建构
关于出版学研究对象的思考
关于出版学学科性质的思考
关于出版学专业方向设置的思考
关于出版学“学科范式”的思考
关于出版学学科本体的思考
关于出版功能的再思考
浅论图书市场需求弹性及其营销价值
概论图书营销
论出版企业的目标市场战略
产品或服务:出版人的一个选择题
出版营销的“融”路径
论发行代理制
论出版产业链的基本属性
产业链分类与出版产业链的类别归属
论出版产业链建设
论出版工作室发展的产业链意义
论书业产销关系的进一步整合
论外商投资我国出版业的产业链战略
资源、技术与共享:数字出版的三种基本模式
论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中的五大关系
学术出版:功能的异化、回归与建构
论科技出版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创新
论科技出版的制度竞争力
提升我国科技出版国际竞争力研究
中国学术期刊同行评审的实践与研究
学术出版体制机制的形成与演化
基于制度视角的开放存取期刊学术质量控制
基于出版流程的开放存取期刊学术质量控制
基于技术视角的开放存取期刊学术质量控制框架
关于我国出版业发展战略的思考(一):出版产业布局
关于我国出版业发展战略的思考(二):出版企业组织建设
关于我国出版业发展战略的思考(三):出版产业升级
新时代出版业发展的新要求、新目标、新任务与新举措
展 读
代序:亲历“发行专业”二、三事
武汉大学的发行专业(现在的编辑出版学专业,但大家都习惯这么称呼她),在业界小有名气。院友们总自豪地将其比作发行行业的“黄埔军校”。可惜了,我不是这个“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是杂牌军,在发行专业的院友面前总觉得低人一等。但值得庆幸的是,“革命不分先后”,后来我总算混进了这个专业,而且一混就是整整30年,也沾上了“黄埔军校”的一点仙气。因此,也就有了机会,聊聊发行专业的一些事儿。
一、闹心的“颜值”
有人说,当今是个看脸的时代,高“颜值”是走向成功的通行证。我想说的第一件事,就与“颜值”有关。虽然纯粹是件自黑的事儿,但还蛮好玩的,给我混迹于发行专业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大家都知道,高校招生录取的依据肯定是高考成绩,高分进名校好专业,低分只能听任“调剂”,与“颜值”应该没有多大关系(艺术类考生不在此列哈,你懂的)。事实证明,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我原本有机会改写自己结缘发行专业的历史,提前七年进入这个专业,成为“黄埔军校”的一期生,但因为低“颜值”而错过。当然,这一切我都被蒙在鼓里,并不知情。谜底的揭晓,则是七年后研究生毕业留发行专业任教时的事了。
武大发行专业,1983年首次招生。同年,我考入武大图专,与发行专业同在一个系——图书馆学系。就学科而言,也算得上是根正苗红了。当时就听老师们讲,武大图专很牛。77年恢复高考后,图专的录取分数是武大文科最高的专业之一,比什么什么专业都高。自己考分不高,进了这么牛的专业,自豪呀!于是,一口气念了七年。1990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我被安排到了发行专业任教。这样就与发行专业结下了缘分,也才有了后来所谓闹心的“颜值”故事。
我留校时,发行教研室有十几位教师,有孙冰炎老师、乔好勤老师、罗紫初老师、黄凯卿老师、吴平老师、彭建炎老师、卿家康老师、余世英老师、朱静雯老师、黄先蓉老师等。教研室的氛围不是一般的好,大家没大没小,什么玩笑都可以开,什么话都可以说。那时,政治学习不多,周四例会大家以聊天为主,而聊天又以损人为乐。罗紫初老师,我们都叫他老罗,学生们称他罗爷爷,军人出身,豪爽得很,损人也没底线。我的闹心“颜值”故事,就是他揭晓的谜底。
据老罗讲,他是1983年武大招生组成员,全权负责当年图书馆学系的招生录取工作。录入图书馆学系的新生分专业就是他操刀的(估计,他是吹牛的)。他说,因为自己是发行专业的人,为发行专业招人,他有私心。要进这个专业得符合两个条件,或者其中的一个非常突出。一是考分高;二是“颜值”高(他的原话是要长得好看,长得丑的不要)。因为这两条件你都不具备,所以就没有把你放到发行专业。他这么一讲,把大家给乐坏了。我是因为长得丑而没有被录入发行专业的说法,也就这么传开了。大家乐了,我可不开心呀。回家对着镜子反复照,五官该有的都有呀,摆的也算是地方,怎么就成了老罗眼中的“长得丑”呢?三人成虎呀,坐实了事儿,想不通也不行呀。看看当时我们教研室的各位老师,个个仪表堂堂、一表人才,老罗的说法也不算太离谱。再看看今天的网红,人家靠“颜值”带货几分钟就能赚你一辈子都挣不到的钱。这样一想,我也就慢慢心安了,接受了这个低“颜值”的美名。
以貌取人,貌似不妥,但强调一个人的气质却是必须的。发行专业虽没有“美颜”“整容”之功能,也绝不是老罗所说的“以貌取人”,但它在培养一个人的气质方面发行专业却有自己一套。发行专业,培养的是文化商人,也就是“儒商”呀,必须内外兼修才行。不是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吗?培养得好,也是可以提升“颜值”的。这些年来,武大发行专业的毕业生一直很抢手,步入社会后大多也“混”得不错,不知跟“颜值”和气质有没有点关系。如果有的话,那我这个“颜值”的故事就有了正面的意义了。
二、永远的“情缘”
扯完闲篇,再说点正经的。头一件正事就是武大发行专业与新华书店的情缘。
发行专业来的不易。武汉大学这个专业能办起来,得益于两位先生。一位是时任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汪轶千先生,一位是武汉大学时任校长刘道玉先生。不是汪先生的执著,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不一定会有图书发行这个专业;没有刘道玉校长的开明,这个专业也不一定就办在了珞珈山、办在武汉大学。发行专业和武大的结缘,得益于汪轶千先生和刘道玉先生。
作为时任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汪先生为争取高校设立发行专业,付出了太多。先生曾与我谈及过其中的一些细节。从1981年起,他就开始积极寻求与高校合作开设相关专业,但遗憾的是,相关高校都不积极,始终没有得到响应。直到他亲自找到武汉大学时任校长刘道玉先生,才得以玉成此事。1983年4月,教育部正式复函同意武汉大学设立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要选择有条件的大学设立图书发行专业”,终于写入了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这一官方文件。
为支持这一专业建设,全国新华书店系统从办学经费、师资培训、课程教学和实习实训等方面给予了武大发行专业大量无私的支持。办学经费方面,1983年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向武汉大学无偿提供280多万的共建经费。师资培训方面,总店下文要求全国新华书店系统无条件接受武大发行专业教师的专业学习和调研工作。办学初期,教研室规定凡留发行专业任课的教师都必须深入新华书店进行发行业务学习。可以说,我们第一批发行专业教师的成长都是与新华书店的培养分不开的。课程教学方面,由于新办专业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新华书店总店从全国选派理论素养好专业技能过硬的发行专业人员参与学校的教学活动。学生实习实训方面,全国所有新华书店无条件接收发行专业毕业生的实习,而且指派最好的实习指导教师,不少书店甚至还提供免费食宿。我成为发行专业的教师后,就先后去过数十家新华书店调研学习,得到了所有书店的热情接待和专业指导,亲历和见证过与新华书店系统的这种深厚情谊。
虽然发行业的市场化发展,改变新华书店原有的计划体制,但却没有改变新华书店与武大发行专业的这种情谊。新华书店总店,始终牵挂着武大发行专业的发展。2018年,我还曾收到新华书店总店发来的公函,咨询发行专业名称变化的相关情况,希望武大发行专业继续在发行人才培养上做出新的贡献。我们武大发行专业,当然不会辜负这种期待和和重托。虽然学科专业名称受教育部相关要求的限制,但我们还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力保“发行”这一关键词。记得2002年,教育部启动研究生学科专业备案时,其它高校均将硕博士研究生专业名称确定为“编辑出版学”(与本科专业名称一致),但我们确定坚持保留“发行”这一关键词,将硕博士研究生专业定名为“出版发行学”,而且一直坚持至今。这是全国高校唯一带有“发行”字样的硕博士研究生专业。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很简单,为的就是这份情谊。
三、尚需努力的“户口”
高校的人都清楚,业界的不一定了解,学科地位是与《学科目录》直接相关的。这里的所谓《学科目录》是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颁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早期叫《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严格意义上讲,只有上了这个目录的学科专业,才算有了“户口”,才能培养硕博士研究生,或者说,上了目录、有了“户口”,才有地位,否则就不能招收研究生,就没有地位。这个目录并不是每年都更新或曰调整的,一般十年才有一次调整的可能。
与发行相关的学科,如所谓编辑学、出版学、发行学或编辑出版学等,都没进这个目录,也就是说没有解决“户口”问题。因此,我们说,发行学等学科没有学科地位。
既然这个目录这么重要,我们为什么不进去呢?不是不想进,是人家不让。为进这个目录,编辑、出版、发行业界和学界一直都在努力,但至今仍然被挡在门外。这是几十年来我们发行专业的一大烦恼。
自1983和1984年发行学和编辑学相继进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获得正式的本科生招生权之后,出版学进入《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争取研究生招生权,就得以提上出版学高等教育的日程。90年代初期,我刚留校时,发行专业的负责人是黄凯卿老师。关于发行专业的一些学术活动,他都放手让年轻人参加。因此,刚进入发行专业,我就有不少亲历学科建设的各类学术活动。近30余年来,我亲历过出版管理层、业界和学界为出版学进《目录》所做过的各种努力,但遗憾的是,每一次都是从希望到失望。
在我经历过这些活动中,有两次活动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较早的一次是1992年5月在武汉大学召开的各有关大学参加的“全国高等学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建设座谈会”。会议是由中文系编辑学专业承办的,负责人是向新阳老师。新闻出版署分管教育和干部工作的卢玉忆时任副署长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座谈会还形成了《高等学校编辑学专业座谈会纪要》,纪要后来还报到了教育部,作为争取进目录的支撑材料。虽然座谈会讨论的议题,主要编辑学本科专业建设,但同时大家也呼吁要“在研究生专业目录上增加编辑学”,“改变目前借用其他学科培养编辑学专业研究生的`借窝下蛋’的办法”。那时,我还是刚刚留校不到两年的青年教师,没有发言的机会,说是亲历是为了好听,实际上不过是旁听了这次会而已。当时的感觉就是,副署长亲自出席,咋们这个专业有希望了。正是这次会议,让我树立了对专业的信心。我就这样一直活在希望之中。
另一次是2004年8月在北京印刷学院召开的“纪念编辑出版学专业创办二十周年座谈会”。这次会议的层级更高,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和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两大部委领导同时出席。在此次座谈会上,多位重量级专家,如宋木文就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和学科进《目录》展开过深入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已经办了20年,培养研究生的条件已经成熟,编辑出版学完全应该进《目录》。在我印象中,吴启迪副部长当时还明确表态支持编辑出版学进《目录》的建议。这是我在经历过的多次座谈会中感觉希望最大的一次,但还是无疾而终,我们至今仍然游离在《目录》之外,始终没有获得我们期待的所谓“户口”。
此后,学科建设方面的座谈会、研讨会几乎年年都有,参加会议的新人也越来越多。2007年总署人事司成立的“全国高校出版专业学科建设协作小组”、2013年改名为“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2010年教育部成立的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教指委、2016年中国新闻史学会设立的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等,每每开会讨论出版人才培养问题。几乎每次会议,都会涉及出版学进《目录》的问题。这些活动讨论的很多问题,也都是在“炒现饭”。因为我入行早,绝对算得上是参加此类活动的老人了,没有了年轻人的那种冲劲,对学科进《目录》一事也已不再抱太大希望了,只是抱一种平常心听听而已。
中国编辑学会的孙文科先生、张曾顺先生等领导曾多次联系我,希望在学会里牵头成立一个高教分会,大家一起努力争取进目录的事。我对他们的信任万分感谢,但我积极性并不高,一直就没有行动,实在是辜负了他们的这种信任。因为长期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那点热情也就被浇灭了。
2002年初的一个深夜,传夫院长突然电话我,说是教育部启动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备案制度,可在一级学科内自设二级学科,而且只剩两天时间就要截止了。陈院长和我连夜赶材料,第二天办完学校的手续,晚上就乘火车往北京赶。早上7点钟我们就到了教育部门口。零下20多度的气温,我俩想找个避风的地方都找不着。冻得实在受不了了,我们就叫了辆的士,在的士上带来半个多小时。后来终于在截止日前将自主设置出版发行学和信息资源管理二级学科授权点的两份材料递到相关部门。材料虽然收了,但结果却不得而知。我们当时的心情犹如北京的天气,一点都轻松不起来。可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我们竟然顺利地获得了在“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自主设立“出版发行学”硕博士点的权利。虽然不算正式“户口”,但我们毕竟可以自主招收硕博士研究生了。与我们同年获得首批研究生招生权的还有北京广播学院,它们是在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自主设立的“编辑出版学”学科点。我们的出版发行学虽然是寄生在“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之下,我竟有了一种“大树底下好乘凉”的轻松感。是武汉大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这个一级学科收留了我们,因此,我始终对“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和信息管理学院心存感激。
一想到出版发行专业成功备案这件事儿,我总会联想起另外一件事,而且身怀负罪感。那还是世纪之交,作为发行专业教研室主任,我曾挑头要离开当时的图书情报学院,想加入新闻学院。可人算不如天算,刚刚闹出点动静时,图书情报学院就与的新闻学院合并了,让我就这样避免了闹分裂和影响学科发展的骂名。2000年,新武汉大学成立后,两个学院又要分开。校学科办专门派人来学院征求意见,了解发行专业是留还是去的意愿。此时,我挺身而出,组织老师们统一口径,向听取意见的领导表达了大家全部希望留在图书情报学院的愿望。这才有了发行专业今天的发展。想起这件事儿,真是觉得很可笑。从发行专业初创时期的图书馆学系,到后来的图书情报学院,一路走来院系的主要领导黄宗忠主任、彭斐章院长、马费成院长、陈传夫院长等,对发行专业其实一直照顾有加。在早期研究生招生指标极其有限、发行专业也没有获得研究生招生授权的情况下,我们专业很早就挂靠在图书馆学之下开始培养研究生。如果放在其他学院,这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了。真是少不更事,险些闹成大祸。这算是学科建设中的一个小插曲吧。
还是回到自主设立出版发行学研究生专业。备案制度,并不是所有高校都像我们一样幸运,大多数高校并不具备自主设置研究生学科专业的条件。因此,这个制度虽然解决了我们的问题,但解决不了大多数高校的问题。因此,进《目录》仍然是困扰出版学发展的一大难题,还需要大家共同来面对。
2019年底,风传新一轮的学科目录调整工作又要启动了。不知是哪来的冲动,我竟又鼓起勇气给相关主管部门写了份《关于加强出版学科建设和建议》,而且很快就得到了高层领导的批示。因为与以往选择的途径不同,而且相关部门又很重视,希望再一次被燃起。受相关部门的委托,整个武汉封城期间,我多半的时间都在折腾这件事。当然结果仍然还只是个未知数。都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成不成也就只有看天意了,只要努力了也就问心无愧。
这就是我亲历发行专业的二、三事,都是些成谷子烂芝麻的事儿,说道说道也就完了,并不指望它什么意义,就算是对发行专业30多年发展的一点纪念吧。
原载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百年纪念丛书:世纪华章》,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
以上章节选自《问学出版》
来源:武汉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