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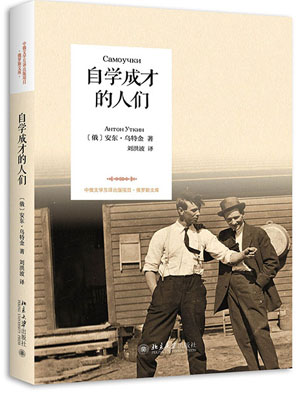 (订购) (订购)
《自学成才的人们》(Самоучки,1997-1998)是俄罗斯当代作家安东·亚历山德罗维奇·乌特金(Анто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Уткин,р. 1967)的成名作之一,1998年首发于《新世界》杂志第12期,1999年出单行本,2002年译成德语在维也纳出版。这部小说和199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环舞》(Хоровод,1991-1995)一起为乌特金赢得了文学声誉。
乌特金是70后作家,虽然出生于莫斯科,但是就像作家自己说的:“我是在白俄罗斯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还有顿河和库班河岸边,童年时常常去那里。我对世界最初的记忆和印象是与这些很不一样的地方的自然和人有关。我用眼睛、耳朵和肺腑爱这一切。”[1]这种对世界的最初体验和记忆后来在他的作品中也留下了印记,在《自学成才的人们》中,一些富于地方色彩的语汇的运用以及作家对时空感的表达都体现了这一点。
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的乌特金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除前文提到的《环舞》和《自学成才的人们》,还著有长篇小说《怀疑之堡》(Крепостью сомнения,2000-2006)、《通往下雪的路》(Дорога в снегопад,2008-10)以及中短篇小说集《南方日历》(Южный Календарь,2005)、《靠近坚德拉》(Приближение к Тендре,2010)等,1996年和2003年度获《新世界》杂志奖,1997年入围布克奖,2004年获“雅斯纳亚·波利亚纳”文学奖。同时他还学过编剧,对纪录片情有独钟,2005年拍摄了自己的纪录片处女作《草原》(Степь),2007-2008年——《明王》(Царь-Свет),2009年——《周围的世界》(Окружающий мир),2012年——《谷物》(Жито),2013年——《留鸟》(Неперелетные птицы)。
文学创作和纪录片拍摄的双轨并行,给乌特金的小说增添了很强烈的画面感和镜头感,而历史专业的出身也赋予了他的创作以取材上的独到眼光,再加上获得评论界一致好评的文笔,使得他拥有了较高的文学声誉,其作品被翻译成法语、德语、捷克语、波兰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语言。在被问及西方读者对他作品的反应时,乌特金认为西方读者并不接受他的大部头作品,他说:“坦白地讲,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翻译我的东西。看来是出于学术兴趣。”这话听起来颇有种“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意味,但是当真拿起他的长篇小说来读,不得不承认作家的话不无道理,因为读他的作品确实需要有点闻弦音知雅意的心领神会才行,不是在俄罗斯文化的池水里浸润过的读者的确难得其妙。因此,仿佛是佐证乌特金的话一样,同龄作家德米特里·贝科夫在评论他时说:“他是历史学家,这对于俄罗斯读者来说总是很有益的,也是思想家,这在现如今是很少见的。”
《自学成才的人们》被认为是作家描绘当代俄罗斯社会生活的三部曲(其他两部分别是《怀疑之堡》和《通往下雪的路》)的开篇之作。《文学报》对其的评论是:“安东·乌特金的长篇小说《自学成才的人们》拥有一个极其重要(而且在当今是非常罕见)的优点——它读起来从头至尾都很有趣。”这部小说反映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是很贴近生活的那种写法,很传统,能明确地感觉到它与19世纪文学是一脉相承的:写实、人文关怀、对美和艺术的崇尚、对人生意义的探求……小说描写了两个昔日的战友——今日的大学生和药品商人——在莫斯科意外重逢后交往的故事,主要是大学生带着他的文学艺术内存和旁观者的眼光,走进了药品商人的世界。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格林等作家笔下的人物和故事渐次渗透进商人贫瘠的精神世界,搅动得他春心荡漾。这种精神重塑的主题让我们不由自主就联想到19世纪的经典之作。而商人并不是单向度的被拯救者,小说中有一个情景——商人巴维尔在一个菜市场上对一个穷苦的老太太动了恻隐之心,想偷偷塞钱给她,被老太太拒绝了,这之后巴维尔无措地杵在那里,莫名就令人想起《白痴》里的梅什金。这种种似曾相识之感在阅读和翻译的过程中屡屡出现,可见其与文学传统的密切联系。
但同时这部小说与经典文学又很不一样。小说中随处埋藏着“暗桩”,而这些暗桩看起来又是作者漫不经心、信马由缰地随意安插的,它们并不像经典文学中挂在墙上的猎枪那样,在结尾的某处会一鸣惊人,而是常常消失得跟出现时一样地任性和毫无来由,我认为,这正是这部小说尽管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上非常真实、传统,但总给人一种似是而非之感的一个原因。而从翻译的角度而言,这些暗桩恰恰是“老鼠拖木锨——大头儿在后面”的“大头儿”和难点。但是,当它们在文本中都被呈现出来之后,小说也便神奇地拥有了厚重感。这些暗桩既包括主人公们在飞驰的汽车里谈到的俄罗斯文学画廊里那一帧帧不朽的图画,也包罗了世界文化花园中的各种奇花异草,这也是我在译文中不得不做很多注释的原因。这份上天入地、天马行空的潇洒随意,即便是被编织进传统的肌质里,也依然有着很强的存在感。再就是小说在总体叙述上属于插叙形式,间或又有点意识流,或者说是有意支离情节的意味,感觉上是现实主义和现代、后现代主义的综合,玩的就是含混。当然,在这部小说中,现实主义还是占主导地位的。这就使得这部小说既好读、有趣,又不那么陈腐,正如当代俄罗斯女作家奥尔加·斯拉夫尼科娃认为的那样,“安东·乌特金在追求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他在力图消灭当前出现在“大众”消遣文学和原则上忽视情节的“高级”文学之间的鸿沟。”
俄罗斯有评论说,在《自学成才的人们》中,作家像一个编年史家,把他所处时代的生活反映在纸上,但是没有触及所写事件的原因和后果;在《怀疑之堡》中已经有了对之的反思和对错失的机会进行的独特核查,而在《通往下雪的道路》中我们可以找到对事件的总结。[2]也许吧,目前我们所能凭借的仅仅是这一部作品而已,而仅就一部作品谈观感就像盲人摸象,纵然是有的放矢,也可能因比例关系不对而有失偏颇。不管怎样,对乌特金的兴趣是被这部小说挑起来了,既然它是作家的三部曲之一,那么余下的两部,也许应该很值得期待吧。
[1] Беседа с Захаром Прилепиным. http://zaharprilepin.ru/ru/litprocess/intervju-o-literature/anton-utkin.html
[2] 《“连道路也难以看清……”——评安东·乌特金的长篇小说<通往下雪的道路>》(И трудно различить дорогу... О романе Антона Уткина “Дорога в снегопад” .) http://www.liveinternet.ru/users/eleroum/post220265265/
本文原载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第八期)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