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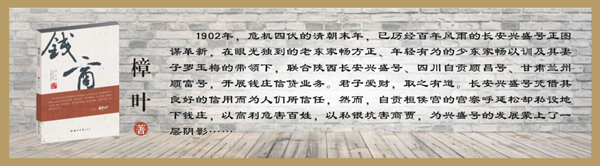
陕西商人的特异风采
——读樟叶的长篇小说《钱商》
白 烨
在我的印象中,樟叶的长篇小说写作,或在题材上写人所少写,或在内蕴上言人所未言,常有令人意外的拓辟与发见。他的《五福》,写近代陕西的辛亥革命,《晚春》写民国期间的西安围城,《石语》写景教碑的盗与护的交锋,都是他擅于开生面,走蹊径的一个个例证。新近推出的长篇新作《钱商》,又聚焦于晚清时期的陕西钱庄商人的货殖营生,写陕西渭南的畅氏家族在生财求利中的励精图治,励精图治中的与时俱进,由此描摹出了一幅晚晴时期陕西商人锐意进取的壮阔画卷。
我在阅读中感受较为突出,印象也更为深刻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作品对于晚晴时期陕西钱商影影绰绰的历史的钩沉与打捞,二是对于陕西关中钱商从性格到精神的内在歌吟。这样两点,就使得这部历史题材的作品,做到了常中有异、平中见奇。
对于陕西人,一般人都会有一种误解,那就是精于文墨,而拙于经商。实际上,自明清时期起,陕西商帮就名闻天下,以“西秦大贾”、“关秦商人”的名头,跻身于全国十大商帮之列,甚至与晋商、徽商相齐名。清初的科学家宋应星就曾说过:“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但这样一些崛起于西北、影响至全国的史实与史事,在今人的笔下,多见于史著与史料,很少见诸于文学作品,因此,陕西商人曾有的辉煌本事,就鲜为人知。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钱商》一作显示出了他的独步一时和无可替代。作者不仅饱带一种为历史上的陕西商人鼓呼和代言的热切激情,而且也发挥了他着意为陕西商人描形造影的文学才情。他在深入调研和细切爬梳陕西商人的史迹与史料的基础上,切近着历史本相和人物原型,进行艺术概括和文学想象,由渭南畅氏家族为主干,连缀起兴盛号钱庄西延兰州,南下自贡的两条线索,勾勒出晚晴时期陕西商人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作为与意义。可以说,仅就使陕西商人进入文学殿堂而言,这部作品就自有其重要的价值。
当然,《钱商》一作不只是以点带面地再现了陕西商人的辉煌历史,描画了陕西商人的幢幢身影,作品更令人为之惊喜的是,还以如椽的大笔塑造了畅方正、畅以训、杨茂堂、罗玉梅等栩栩如生的陕西商人群像。畅方正运筹帷幄中的持重儒雅、畅以训精明强干中的高瞻远瞩,罗玉梅贤淑良慧中的不让须眉,都以高人一筹的智商与情商,既构成了畅氏家族的骨干力量,又代表了陕西商人的精英群体。他们顺应着时局的发展和适应着市场的变化,不断调整经营方略,使长安兴盛号钱庄由钱币流通向小额贷款转换,又由贷款向茶叶、石油领域倾斜,写出了他们在审时度势的运作中,使传统的的金融业务走向复式的实业与工业的过程。如果说经由烟麻丝茶的经营和陕北石油的开发,显现了以畅氏家族为代表的陕西商人由传统型商贾向现代性商人转变的的话,那么,与地下钱庄的殊死较量,与潜藏的不法之徒呼延松的周旋斗争,又体现了陕西商人的征恶扬善与去邪扶正。这样一些持守规则和维护正义之举,又使以畅氏父子为代表的陕西商人,充满了秦人的刚劲豪气与民族的沛然正气。明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曾经说过:“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钱商》里的畅方正、畅以训等人,低调而实干,言利又言义,都堪为秦人里的豪士,商人里的君子。
《钱商》一作细细读来,也还会有描写不够细切,看来不够过瘾的缺欠。这主要是作者把笔墨过多地放置于各种事件和各地实业的铺陈上,使得主要人物在血肉丰满和气韵生动上,都留有明显的不足。这也给作者在这一题材上的继续开掘,留下了一定的余地。因而,我满怀希望地期待着作者在这一题材领域里的新的探索与新的成果。
(白烨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

陕商精神的生动摹写
——读长篇小说《钱商》
允 之
端午小长假,我和家人一起赴西安旅游,随身携带着樟叶的长篇小说《钱商》。樟叶是陕西作家,《钱商》写的是陕西的事。到陕西旅游,读陕西小说,用现实所见印证书中所写,似乎是再合适不过的事。我没想到,书里书外的世界相距那么遥远。白天,我们登古城墙,观兵马俑,游华清池,品陕西小吃,尽情领略自然风光,欣赏人文历史;晚上,我展卷阅读《钱商》,则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世界。
读《钱商》,我的感觉很新鲜,又略微有点吃力。新鲜和吃力,都是缘于同一个原因:我读到的,不是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们笔下习见的陕西农村与城市,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商业世界;我看到的不是柳青他们多次描写过的憨厚朴实的陕西农民和市民,而是一群积极进取、头脑灵活的陕西商人;我感受到的不是陕西博大厚重的历史文化,而是诚实守信、开拓进取的陕商精神。可以说,这部小说彻底颠覆了我对陕西、对陕西人的固有印象,让我从此对他们刮目相看。
19世纪中后期,以渭南商人组成的陕商钱庄发展成为和晋商票号、滦冀帮钱业齐名的金融巨子。《钱商》描述的是1902年至1905年,长安兴盛号钱庄在其第三代掌门人畅方正的率领及其高参汪立玄的协助下,其子畅以训、儿媳罗玉梅夫妇以及兰州分号掌柜杨茂堂等人苦心经营创业发展的故事,其中穿插陕西、兰州、自贡三地业务拓展、人物活动,以及与地下钱庄不法之徒的周旋斗争,呈现出一幅幅百年前陕商锐意进取的历史画面。
这部小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
一是全面展现了一百年前陕西商人诚实创业、锐意进取的奋斗历史。
提起近代中国商业发展史,我们所熟知的是徽商、粤商、沪商、晋商,而对西部商业、商人则所知不多。读了《钱商》我才知道,在近代中国商业发展史上,陕西商人占有重要的份量。他们紧跟时代潮流,立足实业发展,脚踏实地艰苦创业,敢于拼搏,敢于担当,与时俱进,探索创新,表现了积极进取、诚实创业的陕商精神。
樟叶将故事的发生选定在1902年到1905年这个时间段,其时正是“庚子事变,两宫西狩”后清廷变法诏书推行新政之际。上面改弦更张,局面稍开,兴盛号就乘势而上、兴业图强,演绎出一连串生动艰辛而又荡气回肠的故事来。尽管作者截取的只是五年不到的时段,但是却深入就里地铺垫勾勒出钱商扎实经营多年的厚重足迹,描绘了他们因势而应、知困勉行的创业风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是生动塑造了一批个性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钱商》以百年前活跃在中国西部的陕西钱庄商人为原型,以清末中国社会生态为时间节点,以陕西商人驰骋商海的奋斗史为故事脉络,在挖掘和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生灵活现地塑造了以畅方正父子为代表的陕西商人历史形象。
樟叶擅长对人物形象的细部描写。畅方正无疑是《钱商》的主要人物。他善良正派,运筹帷幄;既坚守商业运营应有的制度规矩,又善于根据市时局的变化不断调整经营方略。比如,四川的卷烟、甘肃的水烟本来是畅方正钱庄贷款的主要对象,但是他发现进口香烟已经在沿海地区的年轻人中大受欢迎,畅方正敏锐地认识到:人心趋势最不牢靠,口味终究会变,必须未雨绸缪,及时帮助内地的烟草企业作出调整。再比如,畅家起家是从无须担保的小额贷款开始的,主要做本地的棉花小麦等农产品。但是现代工业浪潮西风劲吹,如果还停留在农产品手工作坊加工的原始阶段,如何能重振陕商的雄风?畅方正选择了从恢复本省茶叶名牌开始,摸索现代工商业项目的建设经验。
其他人物形象也各有特色。比如“高参”汪玄立的足智多谋与沉稳干练;畅家二公子畅以训的朝气蓬勃与勇于探索;二儿媳罗玉梅的秀美贤慧;兰州顺福号掌柜杨茂堂的敬业与风流;桓侯宫宫察呼延松的狡恶阴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丁喜坤这个神秘人物的安排。作者借用了清末长安发生的一件震惊全国的钱庄诈票大案为故事原型,书中丁喜坤受命追查原凶,并不见黑风雪夜的刀光剑影,更多的是丁喜坤笑傲江湖,仙路寻踪,让人在感受神秘中仿佛看到了一个百姓社会嫉恶如仇、身怀绝技、忠于职守的大侠,读来使人不忍释手。
当然,这部小说也还有可以改进之处。比如,小说中出场的人物众多,作者在每个人物身上用力稍显平均,故而使主要人物的形象不够鲜明、丰满;再如,小说涉及事件很多,脉络不够分明,给阅读造成一定障碍。这些给作者进一步完善作品提供了空间,相信作者在这一题材的发掘上会有更大收获。
(允之 《文艺报》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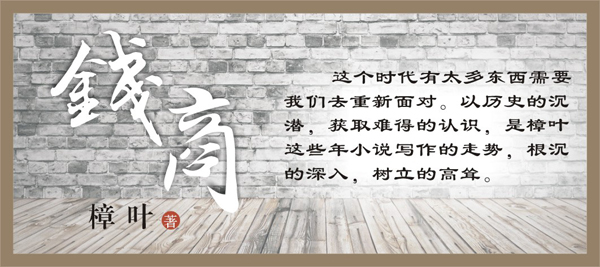
主题先行和形象虚构
——关于长篇小说《钱商》
刘 琼
小说怎么写?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起、落笔,即便同一个作家在不同文本里因为具体的写作动机不同,而使有不同的起落方式。樟叶的长篇小说《钱商》较为明显地呈现了一个有意思的流程:即由一个主题到一组形象到一篇作品的完成。
先有主题,后有形象,这当然就是主题先行。主题先行在文艺创作领域的名声不好,一直被质疑存在的合理性、文本的文学性,被批判观念大于艺术。为这个质疑和批判提供的振振有词的证据是,文艺创作必须用艺术形象再现和表现生活。
这个“必须”当然没错。艺术形象是文艺创作的成果,也是文艺作品的美学体现,艺术形象在文本中当然是老大。在文学作品中,这个艺术形象,是以语言为手段创造的美学形象。多数作家的创作经验,都是先有感性生活和具体的生活形象,然后通过典型化和艺术化,成长为文学形象。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吸引人并打动人,一定是作家用美妙的文学语言塑造了各种生动奇特的艺术形象以及这些艺术形象所承载的生命经验。
承认文艺创作中艺术形象的不可忽缺,并不必然否定主题先行的创作合理性。从形象到作品这种创作历程是坦途,没有异议,但是不是所有的优秀作品都是遵循这样的创作经验?是不是“主题先行”就一定出不了好作品?创作中的主题先行又是如何进行的?我的理解是,创作者的大脑里存在对某种生活经验和观念的深刻认识,并有表达和传播的强烈愿望,然后开始虚构艺术形象,通过艺术文本还原和表现这种经验和认知。在当代文艺实践中,特别是在影视和舞台艺术创作领域,这种“主题先行”法大家都不陌生,比如过去的一些“样板戏”创作,比如现在的一些重大题材创作。关键是,影视和舞台艺术用这种方式创作,有不成功的案例,但也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这说明这种创作方式本身是可行的。当然,影视和舞台艺术创作的特点是“综合性”“工业性”特质,即一个作品的完成要经由多种艺术门类的共同组装,即在同一个主题下,用不同艺术形式还原和塑造形象。这种创作特质决定了流程往往是从效果感受“逆生”形象,加工,组装,设计,等等,即具有“工厂”性。那么,主题先行能不能产生优秀的文学作品?理论上是可以的,虽然这个过程往往更费力气。比如,柳青创作《创业史》之前为什么要下到西安郊区皇甫屯生活?当时柳青在《中国青年报》工作,但他一直在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农村的道路问题,特别是出访苏联时对于苏联农村的变化、农业集体化和农村政策有了一些认识和研究,他决心一部反映中国农村道路的小说。在这种写作愿望支持下,他选择到皇甫屯生活,跟农民一起,感受农业合作社的成长风雨,写出了《创业史》第一部。
《钱商》的作者樟叶是柳青的陕西乡党,也是带着为陕商立传的写作愿望,到川甘等地调研,体验和寻找生活形象。明清以来,“资本”和“市场”萌发出活力,一些以地域而集聚和命名的商帮,比如徽商、晋商包括陕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一方水土一方人,这是文学写作的兴趣点。商帮也各有主导业务,各有文化特点,比如徽商以“儒商”“红顶商人”而名,晋商以“勤俭”“钱庄”而名。比较起来,《钱商》的陕商名气虽然小,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开拓川陕甘“茶马交易”道路上的盐业、烟业和金融业,厚重质朴,坚忍不拔。本书作者显然对陕西近现代历史特别是经济领域进行过深入研究,对于在具体的环境里如何因地制宜、开发资源优势、运筹经营有自己的见解。从这个研究和见解出发,他到四川、甘肃调研,收集素材。作家最后在文本里创造了三个空间:陕西渭南,四川自贡,甘肃兰州。联系这三个空间的线索,是渭南兴盛号钱庄的畅家及畅家的社会关系。这个视角是完整和巧妙的,看似是家族史写法,其实不然,作家的兴趣是写“金融行业”。选取“钱庄”这种金融实体为对象,可以把书写触角伸入到盐矿、水烟业等众多工业,通过勾勒一幅相对完整的经济运营实况,写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转型时期的秦人风范。这群秦人身上,既有儒家文化的进取,也有各种局限和束缚,既有变革的图谋,也会力有不逮。这种辩证法,恰恰体现了作者的历史正确——把人放在具体的环境里考察。与此同时,小说对于甘川秦三地风俗文化的描写也有一定的特色,说明作家写作之前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努力为人物构筑具体的独特的生活环境,生活环境也是艺术形象的内容。小说在具体的人物形象创造方面有收获,比如对两位女主角李凤英和罗玉梅的塑造很有地域文化特点,对于自贡和兰州两处商人群体的差别性塑造,等等。
从形象创造这个角度,这篇小说的不足是“散点”大于“焦点”,出场人物众多,笔墨平均分配之后主要人物的性格完成不够,导致人物形象不够丰满,也就显得不够出彩。可以写群像,但群像也需要骨肉停匀,要有相对的焦点。为什么会造成小说这种局面,不是“主题先行”的错,而是作家急于表达的东西太多,有时候就忍不住发出大段大短的对话,戕害了细节和动作。因此,“主题先行”在创作时,一定要摁住“主题”,让形象做主。当然,我也是忍不住指出这一点,期待作家的下一部作品更加出彩。
(刘琼 《人民日报》文艺理论评论室主任,《人民日报》文艺部高级编辑)

疏可走马 密不透风
——读樟叶小说《钱商》
戴晓斌
樟叶先生的长篇小说《钱商》在正式交付出版社前,我曾有幸先睹书稿,《钱商》让我了解到另一个我的城市,我的故土,我的先辈。
小说《钱商》以百年前活跃在中国西部的陕西钱庄商人为原型,以清末中国社会生态为时间节点,以陕西商人驰骋商海的奋斗史为故事脉络,在挖掘和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生灵活现地塑造了以畅方正父子为代表的陕西商人历史形象,读来使人感触良多。
说到近代中国商业发展史,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多是精明强干通江达海的山西票号,气势恢宏富可敌国的徽商盐商,以及最早占领对外贸易先机的海派商人和经营洋货的广东士绅商贾。对陕西商人的历史记忆,大多是一星半点的盛唐故事和只言片语的安吴夫人。樟叶先生《钱商》一书的出版发行,把历史上的陕西商人纵横潮头,接地气、走江湖、性耿直、敢担当,立足实业发展,脚踏实地艰苦创业,与时俱进探索创新的陕商精神通过一个个人物故事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明清农耕文明年代,烟茶盐是通行全国的大商品。那个时代以陕西茯砖茶和棉布,兰州水烟,四川井盐及丝麻为代表的名优商品,更是行销神州的大宗商品,无论是老辈人的记忆还是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都可以找到“由于陕西商人的介入,”始得这些商品壮大发展的历史记录。陕西商人的历史功绩和显赫作为,在于他们掌握了这几样关乎民生的大宗商品。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也许行销全国几百年的水烟制品属于有碍健康的另类,但它行销数百年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却是在改革开放前期各省陆续兴建卷烟工厂后发生的事。
明清时期中国有十大商帮,陕商(秦商)是其中之一。清嘉庆年间以渭南帮为主的钱庄商人走上了历史舞台。如同陕人义薄云天、吃苦耐劳接地气的厚重敦朴,这些旧式钱庄一开始就祭起“小额信贷”的大旗,进千家门、结万户情,把钱庄的营销重点放在商品生产作坊和种植大户,形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色,也是陕西钱商与其它钱庄票号的区别。“小额信贷”至今仍然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全民创业”和“三农”发展的重要信贷产品,也是各级政府和银行业监管部门鼓励商业银行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和个人创业的政策导向。作为一名银行从业人员,我十分看重樟叶先生在其《钱商》一书中所描述的“小额信贷”立足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钱庄从业人员不辞辛苦、靠两条腿深入田间地头和商铺矿区,考察论证项目,确定贷款对象和利率的特质。樟叶先生在《钱商》一书中以文学形式不厌其烦地描写钱庄各项交易过程,事无巨细地算计毫毫银文文钱,在密不透风的钱庄交易中,用商界人物的喜怒乐和生意场上买卖进出,揭示出先辈钱商推行小额信贷的庐山真面目,挖掘出陕西钱商在商贸经营活动中的天地良心。
樟叶先生的文学创作具备把控大时代、大事件、大场景的能力,在已经发表的几部长篇小说中,有《五福》式辛亥革命的恢宏,有《晚春》般西安护城战争的摧枯拉朽,有《石语》中古城长安百姓护宝的传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作者运用如椽之笔品读历史的心志。小说就是讲故事,把一段历史中发生的大事件通过人物和故事展现给现代读者,是件不易的事。《钱商》用了仅仅二十余万文字,采用了“疏可跑马,密不透风”的艺术手法,展现了清朝末年陕西钱商在长安、自贡、兰州三地的钱庄经营活动及人物故事和风土人情,从中还原出陕西钱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艰苦创业奋发有为的历史风采。
对于辛亥革命前夜中国社会商业的生存状况,樟叶先生选定了1902年到1905年这个时间段,着意刻画出中国社会在大革命暴发前夕中国工商业的发展状况和朝廷进行推进改革的无奈,无论从历史线索和社会形态看,都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钱庄》使用笔墨不可谓不疏。在人物的选择和故事的安排方面,《钱庄》一书安排众多人物跃然纸上,读者看到的往往只有连环画式的一个个截面,不如一般小说主要人物来去归宿描写的细腻,小说故事不能说不疏。但当百姓社会例如陕甘川三省的民俗生活画面填充其间时,《钱庄》的故事可读性和完整性显现出来,达到了“疏可跑马”的艺术效果。
樟叶先生在文学创作中擅长人物形象丰满的细部描写,《钱商》书中畅方正的善良正气运筹帷幄;汪玄立的足智多谋沉稳干练;畅以训的朝气善学勇于探索;罗玉梅的秀美贤慧;杨茂堂的敬业与风流;呼延松的狡恶阴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行为作派和丰满脸谱。书中人物刻画入木三分,密不透风。特别是丁喜坤这个神秘人物安排,作者借用了清末长安发生过的一件震惊全国的钱庄诈票大案为故事原型,书中丁喜坤受命追查原凶,并不见黑风雪夜的刀光剑影,更多的是丁喜坤笑傲江湖,仙路寻踪。让人在感受神秘中仿佛看到了一个百姓社会嫉恶如仇、身怀绝技、忠于职守的大侠,读来使人不忍释手。
在祝贺樟叶先生小说《钱商》出版发行的同时,我们希望樟叶先生在今后的创作过程中,更多地关注现代生活题材,用平实的故事和语言,写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丰彩。
来源:西北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