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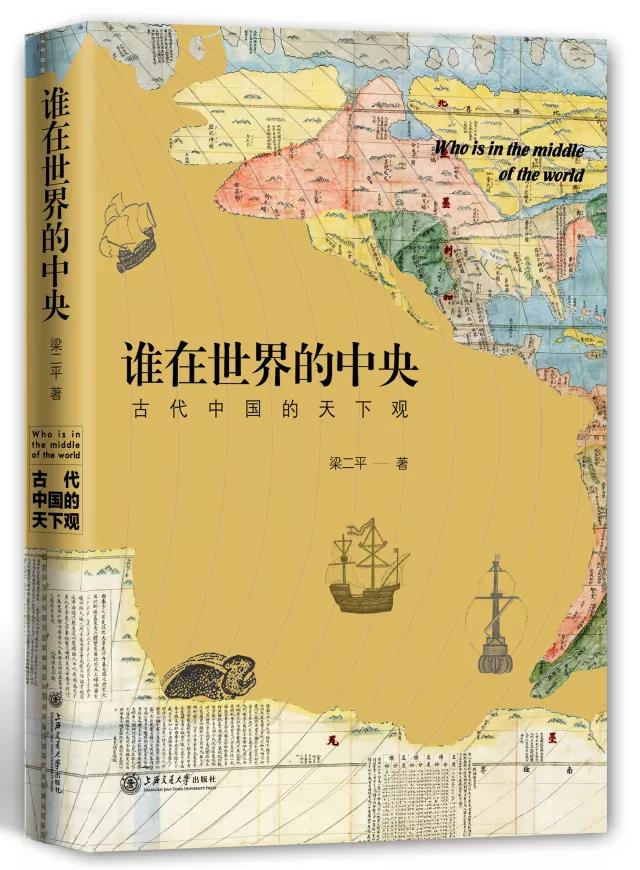
《谁在世界中央:古代中国的天下观》
“西域”到底有多远?
西域,最早指周朝诸地。自汉代以来,西域狭义上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地区等。西域到了后来演变为我国的西部地区的含义,所以青海、西藏亦是属于西域的范围。
经过高祖高后、文帝景帝等几代领导人的经营,汉至武帝,政府已有消除边患的资本,但对待风一样飘来飘去的匈奴,刘彻还是寻不到一个彻底根除边患的办法;思来想去,还是先秦远交近攻的老办法—选使西去和匈奴身后的游牧政权大月氏联盟,即使构不成夹击之势,至少也可钳制匈奴。这个算不上英明的决定,却为后世留下了一个伟大壮举——“张骞通西域”。
公元前138 年离开长安西行的张骞,没等走到大月氏,就如预料的那样被匈奴抓到了。张骞不仅做了俘虏,还被“和亲”,娶妻生子了。后来,张骞成功逃亡,辗转找到了大月氏。但已定居西域的大月氏,无意再做行国,也不愿回师东进与匈奴为敌。灰心丧气的张骞靠着运气逃回阔别了13 年的长安。虽然联盟失败,但大汉却从张骞那里得到了闻所未闻的玉门关以西的信息。这些信息后来成为《汉书·西域传》的原始线索,“西域”这个新鲜的地理名词,也是从这里第一次载入历史。
张骞赴西域之前,汉朝投向西方的视野,基本上停留在玉门关一带,没能跳出《禹贡》所说的九州。公元前119 年,朝廷决定派张骞率领300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再赴西域,游说乌孙王东返。乌孙虽然没有答应东归,但却派使者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其中,大汉与西域马的“贸易”,成为双方最初的交换。1969 年在甘肃武威发掘的东汉“守张掖长张君”墓葬中出土的铜奔马,即后来被命名为“马踏飞燕”(中国旅游标志)。它反映的不仅是汉代“通西域”的良马贸易和尚马之风的延续,同时也反映了武威因汉人尚马,而发展成“凉州畜牧甲天下”的良马交易、繁殖基地的历史事实。
1969 年在甘肃武威发掘的东汉“守张掖长张君”墓葬中出土的铜奔马,反映出汉代“通西域”的良马贸易和尚马之风的延续。
汉朝派出的使者与西域通商……这些交流所带来的地理大发现是前无古人的,西域,渐渐进入了大汉的掌控之中。公元前60 年,匈奴内部裂,对西域的控制瓦解。汉宣帝任命卫司马郑吉为西域都护。这是“西域”一词,作为行政名词的首次使用。其治所在乌垒城,即唐代诗人岑参所说的“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的轮台,地处今天的乌鲁木齐以西360 公里处。西域都护所辖的地区,史称“西域三十六国”,大约是现在的新疆南疆地区。
在敦煌莫高窟第323 窟北壁西端,有一幅壁画表现的就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此图是现存最早的“张骞出使西域图”。
在敦煌莫高窟第323 窟北壁西端,有一幅壁画表现的就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此图是现存最早的“张骞出使西域图”。这个佛教史迹壁画以山峦分隔故事情节,共四组画面,每组画面都有榜题。第一组画面位于全图右侧:上部是一座宫殿,殿内立金像两尊,匾额上书“甘泉宫”三字。榜题仅存方框。下面是一王者,手敬香炉,跪拜顶礼;左右各立三臣,躬身合掌,持笏顶礼。榜题:“汉武帝将其部众讨凶奴,并获得二金[人]长丈余,列之于甘泉宫,帝为大神,常行拜谒时。”第二组画面位于全图下层:一王者骑于马上,臣八人跟随左右,后有侍者执曲柄伞盖。王者对面,一人手持笏,跪拜辞行。后有二侍从,持双节,牵四马。马上驮着物品。榜题:“前汉中宗既得金人,莫知名号,乃使博望侯张骞往西域大夏[国]问名号时”。第三组画面位于全图左侧下部:一人骑马在先,二侍从持节骑马随后,穿行在荒无人烟的山峦中。榜题仅存方框。第四组画面位于全图左侧上部:三人行至一西域方城,两人手持双节。城内佛塔高耸,城外两僧人向城内观望。榜题仅存四字:“[至]大夏时”。这组画表现的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题记中“前汉中宗”应是画工笔误,“问金像名号”是唐朝人为造像需要编的故事,将张骞去西域招兵卖马,改成请佛问号,借此扩大佛教的影响。
画中说的大夏国是西域古国,在今阿富汗一带。从政治地理的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张骞把“西域”这片陌生的大陆带进了中原政权的视野。自《汉书》以来,“西域”一直是古代中的一个特殊地理名词,在历朝历代的《地理志》中,西域都是单列一章,都是浓墨重彩,都有故事可说……这个“西”到底有多远,“域”到底有多大,随着祖先的探索脚步,它不是不变的,而是一步步移动着的,从历史的时空讲,“西域”是漂移的地理概念。
汉代的“西域三十六国”:南缘有楼兰(鄯善,在罗布泊附近)、菇羌、且末、于阗(今和田)、莎车等,习称“南道诸国”;北缘有姑师(今吐鲁番)、尉犁、焉耆、龟兹(今库车)、温宿、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等,习称“北道诸国”。此外,天山北麓有前、后蒲额和东西且弥等。当时的一个“国”,也就万人左右;龟兹人口最多,约八万余。所以,“国”之兴灭,转眼之间。
北魏时的“西域”分为“四域”:一域“自葱岭以东,流沙以西”;二域“自葱岭以西、河曲以东”;三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四域“西海之间,水泽以南”。这是《北史·西域传》的记载,其中的后三域,在今天的帕米尔高原以西以东。今天的中亚许多地区,被看作是“西域”的范围。
大唐的“西域”范围很大,在《旧唐书》列传中,尚无外国概念,用的是夷、狄,还有西域。当时的西域为:敦煌以西、天山南北、中亚、西亚地区均为“西域”。唐代的大西域概念,来自初唐的广阔疆域,当时设有安东、安西等六大边疆督护府和许多边州督护府,其西边势力,一度远达大食(波斯)。
经历了元蒙西征,“西域”的概念更加广阔。《新元史·外国》将西域放在“外国列传”中,这个西域甚至包括了东罗马(今土耳其)。
清代初的地理观念是最接近当时的西方地理,这一时期的“西域”,在乾隆时期撰修的《西域图志》中,有明确解释:“其地在肃州嘉峪关外,东南接肃州,东北至喀尔喀(今蒙古国)、西接葱岭,北抵俄罗斯、南接蕃藏,轮广二万余里”。也是在这一时期,西域作为前朝故土,始被“新疆”一词取代;嘉庆时,“新疆”一词就完全代替了“西域”。1884 年,清政府正式在新疆设省,并取“故土新归”之意,改称西域为“新疆”。
明史中的西域与外国同置于《列传》之中,在外国之后,单列西域。但在《清史稿·地理卷》中,不再单设“西域”一栏,代之以天朝诸省中的“新疆”。从此“西域”成为不再飘移的地理名词,凝固于历史文献之中。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