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是一种从书面语言和其他书面符号中获得意义的社会行为、实践活动和心理过程。作为一个术语,“全民阅读”十多年来频繁出现于各类媒体,成为新闻出版、公共文化服务、图书馆服务等领域的关键词。
该词的正式来源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46年成立以来,就将阅读推广工程视为促进人类文化传承、传播与创新的基础性工作而不遗余力地向世界各地推广。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对多国(尤其是亚非拉地区)的阅读和出版情况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人人有书看”(Books for All)的口号,并把1972年定为“国际图书年”。1995年,该组织宣布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1997年,该组织又正式发起“全民阅读”(Reading for All)项目,并在世界范围内持续推广。
2019年4月23日是第24个“世界读书日”。今天我们分享的文章出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民阅读推广路径研究》一书。文章对中国传统阅读思想进行了梳理,认为阅读始终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重视阅读是古人做人治学的重要一环,重视阅读是我们的一个文化传统。

阅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路径、阶梯和动力。自从有了阅读,人们的知识就不再随着自然生命的结束而结束,而是通过文字符号传递下去,将前人达到的高度作为自己前进的起点。在一定意义上,阅读使人类进入文明史,文明的奠基和大厦是靠阅读支撑起来的。人类依靠阅读摆脱了蒙昧,进入了文明状态,也靠阅读推动着文明不断发展。拥有阅读后的文明时代,使得人类的进化方式由自然选择进入文化选择的新模式。
从中国思想史上来看,书跟“学习”的关系,很早以前就成为中国文化中受关注的问题,有关的讨论也就变成中国思想史的一个传统,孔子《论语》上来就讲“学而时习”,不是偶然的。孔子时代,子路提出了“何必读书”的问题。他认为,帮助老百姓干点事,做官就可以了,何必读书? 结果遭到孔子怒斥。从这个经典的例子可以看出,学习和读书早已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孔子的思想体系,应该说如果从伦理道德观念来看,“仁”是最主要的,但是如果从整体上看,从后来的学术发展的争论来讲,“学”也是核心的观念之一。孔子时代的“学”是“六艺”,但这里也包含了人文知识的学习,其中读书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读书在孔子以后越来越重要,直到宋明理学,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辩,陆九渊针对朱子强调读书、主张读书才能成圣人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尖锐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尧舜之前有何书可读”,尧和舜如何成为圣人的呢? 就是说,陆九渊认为读书不是成圣成贤的必要条件或者是首要条件。因此,在中国哲学史上,即使像儒家这么重视学习的一个传统学派,读书仍然被当作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在讨论,这个恐怕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不多见。总体来说,儒家有重视读书、重视学习的文化传统。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他的形象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形象。所以他最重视的一个德行,就是是否“好学”。别人问他的弟子里边谁好学? 他说只有一个人,就是颜回,颜回死了就再也没有听说有好学的了。他说忠信的人很多,不远的地方里都能找到忠信的人,但是要找到像我一样好学的人,很难。从这个角度来讲,整个《论语》体系,他把“好学”当成一个非常难得的德行。从这个角度来讲,孔子是学习文化的奠基人。我国重视读书学习的文化,到了宋代进一步得到加强,特别是朱子把孔子学习读书的传统大大加强。朱子学宣扬《大学》,讲究“格物致知”,“格物”归根究底最重要的就是读书学习。整体上来讲,朱子学说体系的背景就是学习,是对学习的精神、学习的必要性做哲学的论证。所以在整个中国思想史里,从孔子到朱子的基调是强调学习、强调读书。今天讲建构学习型社会、书香社会,必须继承和借鉴我国学习文化和读书的传统。“读书人”在历代基层社会中都是受到尊重的。
近代以来,民族的先知先觉者们,就一直在号召人们多读书多学习,通过读书和学习来了解西方,来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不足,从而向西方学习。魏源正是在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潮流。近代以来读书范围更广,主张中国的书和西方的书都要读,19世纪末,外国传记作品在那一代人中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哲学史奠基人冯友兰先生曾讲到,青年时对他影响特别大的是富兰克林的自传。宋史研究专家邓广铭先生,也谈到他年轻的时候在山东济南一中读书的经历,是看《贝多芬传》受到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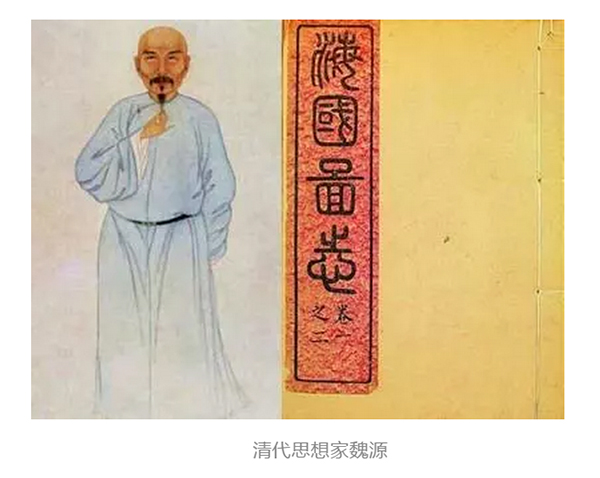
读书和学习已成了思想史演进和发展的一部分,如同历史上发生过的相关争论一样,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也发生过关于读书与学习的争论。比如抗日战争时期,就发生过“读史救亡”的争论。当时一些学者发表文章,主张“读史救亡”,他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深谙“灭人之国者,先灭其历史”的道理,极力否认和歪曲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以为他们侵略、占领中国服务,要挫败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就必须提倡读史,通过读史来树立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加强民族的凝聚力。同时,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过无数的英勇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通过读史,我们可以从这些民族英雄的身上吸取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树立起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勇气和信心。当然,在具体读哪些书以及如何读的问题上,学者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读二十四史,尤其是司马迁的《史记》,有的主张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的主张读儒家的“六经”,有的主张我们不仅要读中国的历史书,还要读外国的历史书,尤其是日本的历史书,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要抗战建国,就必须读书,了解民族的历史,树立起民族的自信心,而民族自信心的有无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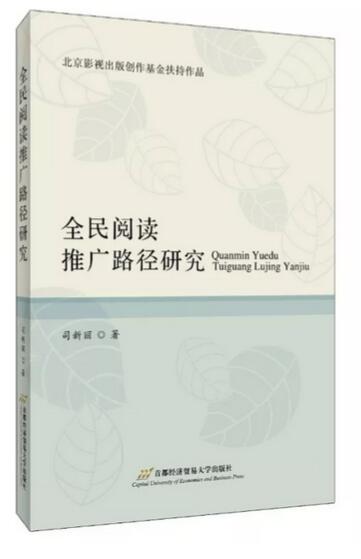
一个民族的阅读史即该民族的精神发育史。深化全民阅读推广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在提高民众整体素养方面的一项带有战略意义的文化导向政策。
本书立足“为什么推广”“推广什么”“怎么推广”等全民阅读推广的核心问题,从阅读理念、推广活动、阅读立法、推广机制、阅读读物、硬件设施、队伍建设、绩效评估八个方面阐述了深化全民阅读推广的体系保障。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点面结合,既有理论逻辑上的系统化视角,又有实证基础上的现实关照,注重对各种阅读现象的梳理、分析和解读,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具有问题导向意义上的学术价值和较强的应用价值。
作者司新丽,文学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后备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阅读文化以及全民阅读推广研究。
来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