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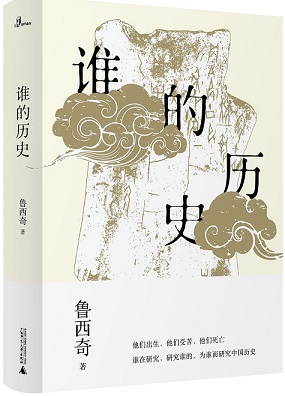
《人的历史与人的历史学》鲁西奇
生存、交往、控制与求知,可能是人类最基本的四种欲求,也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出发点:因生存欲求而产生了生计方式,进而形成了经济形态;因交往愿望而产生了关系网络与组织,进而发展为“社会”;因控制而产生权力,由权力的分配与争夺而形成政治、产生国家;因求知欲望而产生了学问,并进而形成系统的知识、技术与思想。这些因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生存需要交往与合作,交往当然以生存为前提;同样,对他人的控制是在交往过程中实现的,交往本身又必然包含着控制与被控制;而求知正是在生存、交往与控制的过程中孕育成形并付诸实现的。正是因为此,立基于生存欲求的生计方式与经济形态,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关系网络与社会结构,为了控制他人以及在控制过程中形成的权力结构和制度体系,以及在探索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的知识、技术与思想体系,这四个人类
社会的基本方面是交织在一起、互为前提与结果的。
显然,并非所有的欲望都有可能实现。首先,死亡必然终结生存状态。死生事大,无常迅速。社会不会死,制度、国家与思想也不会死,会死的是个人,所以死亡具有独特性;而每个人都会死,这是死亡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死亡了结个人的生命,意味着人生的尽头,围绕它的恐惧和忧虑,便是个人意识形成的关键;它把人从社会与历史中抽离出来,使之强烈关注自己的命运。这是信仰与宗教之个人性的根源或根源之一。死亡的必然性与普遍性则推动了不同文化中诸种正式与非正式仪式的形成,并催生了关于死后或来生世界的集体性想象,这些仪式和想象被用以缓减度过这个人生最大和最后分水岭的焦虑,并最终用于延续因死亡而被打断了的生命及其蕴涵的文化使命。如所周知,信仰、仪式是宗教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组织却并非宗教所必需)。在这个意义上,因为必须面对死亡、处理死亡,从而形成的关于死后世界的想象(关于另一个世界的构想)以及处理死亡的仪式,很可能是宗教产生的根源之一。
其次,控制的对立面是抗拒。有控制,就会有抗拒、反抗或者至少是“不从”(不服从)。“据希伯来和希腊神话所载,人类历史的开创源于一种不从的行为。生活在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曾与自然和谐地相融一处,他们并未超越自然。在本性上,他们如同母亲子宫中的胎儿,既是人同时又不是人。只是由于他们不顺从某种命令,才使这一状况发生了改观。他们挣脱了与大地和母亲的维系,剪断了脐带,使人从一种前人类的和谐中突现出来,并得以向独立和自由迈出了第一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洛姆说:“人类历史肇始于一种不从的行为”,“全部人类文明都建立在一种不从行为的基础之上”,“人类因不从的行为得以不断地进化,不仅精神得到了尽可能的发展,而且智力也得到了发展。 ”而当人的“不从”超越了精神与智力的层面,将“不从”付诸社会实践与行动,就形成了社会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变革:激烈的“不从”导致革命或暴乱,温和的“不从”则催生改良,也可能孕育革命,两者都以不同形式推动历史前进。因此,对控制的抗拒,亦即“不从”,是推动人类历史进程的能动性要素之一。
死亡与不从,作为生存与控制的对立面,也可以说是生存与控制的衍生物:生死相倚,控制与抗拒共存。因此,死亡与不从,也是人类历史的基本要素。面对死亡的恐惧而形成的个人生命体验与意识,处理死亡的仪式,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以及建基于其上的信仰和宗教,乃是人类历史的重要方面;而不同形式的不从或抗拒,则以革命或改良的方式推动历史前进,也是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
因此,如果我们站在“人”的立场上,从“人”出发,以历史上的“人”为中心,将历史看作生命的体现,叙述并分析历史过程,那么,生存—生计—经济、交往—关系—社会、控制—权力—政治、求知—学术—思想、死亡—仪式—宗教、不从(抗拒) —革命或改良—进步等六个方面及其过程,就应当是历史叙述与分析的主要内容。这就是“人为本位的历史学”最基本的内涵。
《变幻的空间与空间结构的“解构”》
我本来无意于“建构”这个“结构”。在我早年的学习与研究生涯中,我曾徜徉于襄阳城下的鱼梁洲滩头,看落日舟渡,听逝水呜咽;也曾站在五门堰的堰坝上,遥想前人生计之艰,费力之巨,技艺之精;偶尔,我会抬起头来,看山峦起伏,草木无言,或者满天星斗,宇宙空寂。直到今天,我也更愿意停在路边,仔细观察一草一木,以及碌碌奔波的蜜蜂蚂蚁,而不愿在空中飞行,俯瞰苍茫大地。地方差异、文化多样、对地方感知的差别,对我而言,是生活的经验而不是学理的探究。我更愿意从生活的经验出发,想象自己就如曾经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生活过的一个不曾留下姓名的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自己的草庐前和邻居大碗喝水(没有酒),共话桑麻,听婆娘唠叨、儿女哭闹,一起痛骂官府老财。然后死去,归于黄土。我非常羡慕研究中古北族的罗新教授,如苍鹰一般掠过草原、沙漠,纵横万里千年,看狼烟起灭,天下浮沉。但我终不过是南方山谷里的一只燕雀而已。
可这是一只“中国燕雀”,生活在中国南方山谷里的一只燕雀。我不能不去想:我所生活的这个山谷,在这个世界的什么地方,它的(不是我的)往世与今生又是如何。我需要确定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我与他人间的距离,以及我可能盘旋或飞翔的方向。同时,作为教师,我还有责任和同学们一起去思考并讨论这样的问题。虽然自己是燕雀,却不得不努力鼓励、引导同学们成为鸿鹄苍鹰。
“结构主义”的思想方法早已受到广泛而深入的质疑与批判,今天,即使是“老牌的结构主义者”,也不再着意于揭示并描述某种“结构”,而更侧重于分析、阐释“结构”形成并演化的过程,亦即所谓“结构过程”或“结构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的思想方法并不新颖。虽然我将“结构”放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去考察,但着眼点并不在于这个结构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与演变的过程,而是它在历史进程中的展现。换言之,我所探讨的是中国历史进程所展现出来的“结构性”倾向,而并非这种结构的形成与演进。所以,我还没有走到“结构过程”这一思想阶段上,仍基本停留在“结构”本身的揭示(或建构)、描述与阐释阶段。
现实中的教室,大多是排定好桌椅的,老师和学生一般都处在排定的位置上,不太可能“任意选择一个位置”。教室更是按规制建好并配备相应的设施。显然,这个空间以及在这个空间中的位置、距离、方向都是预设的、给定的,是早已“被结构”的。这个“结构”既不来自老师、同学,也不来自“我”(外来的观察者),而来自先于老师、同学以及“我”存在的“制度”与“文化”,在“制度”与“文化”的背后又是“思维方式”在发挥作用。分析这个教室的“空间结构”固然可以窥见其背后的制度、文化乃至“制作”这个教室的人群的“思维方式”,但更重要的问题却是:处在教室中的老师和同学为什么会“心甘情愿”或不得不“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教室,遵守、执行乃至强化其所给定的“秩序”?这种“空间结构”所给定的秩序与规范,又将以怎样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制约着老师和同学们的人生?把这个问题转换到中国历史的讨论上来,就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空间结构(区域多样性,核心与边缘的差异,城市与乡村及其各自的差别),究竟是怎样“塑造”了中国、中国历史与文化以及“中国人”?它将以怎样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或制约着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现在与未来?为了思考这一方向上的问题,我尝试着转换观察视角,不再从空间的角度观察人与社会,而站在人的立场上,去思考空间的意义。
人类生活在地球的球面上,这与我们的经验世界没有太大关联,且置于一旁。我们经验中的直线是有限的,其有限度取决于目力、望远镜及想象力;将限度极致的各点连接起来,就是一个封闭的圆圈(未必规则)。在现实社会中,很多“直线”并不平行却从不相交:芸芸众生的生命轨迹,从没有交汇,却完全不同。
“距离”也有完全不同的含义而且无法度量:同枕共席的夫妻可能相隔万里,从未谋面、完全没有利益相关的两个人,却可能生死与共。许多研究指出,人类交往、组织与社会的基本形态是“圆形”: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施坚雅的“基层市场社区”,到台湾学者的“祭祀圈”,以及“核心”与“边缘”,等等,都是“圆圈”。在以往的学习、思考与研究中,我和许多学者一样,设想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基本方法,是以“我”为中心,画一个或多个圆圈,自内而外,关系由紧密而疏远,认知由清晰而模糊。并且,我们相信,“我”总是处于某些性质不同的“圆圈”里,并因此而获得生存空间和安全感。现在,我更愿意想象自己处在由空间中一个曲面(不一定是球面)组成的世界上,是那个曲面上的一个点,其运动的方向取决于“邻域曲面”的性质,以及“充满曲面的物质”的性质:“我”可能随时“滑落”或者“被抛出”,也可能“永远”停留在某一个“双曲点”上。进而,我去构想历史过程中的个体、人群以及他们“制造”或“参与”的事件,发现它们在我的“视野”中全部“晃动”起来或处于准备“晃动”的状态中: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可能随时被抛弃、掩埋,当然,也随时又可能被“挖掘出来”,用聚光灯照射,“闪亮登场”。处在“曲面”世界上的个体、人群,都有诸多的可能性方向,却无法确定,更无以描述。
在上述自学的、一知半解的数学(以及更少的物理学)知识与思想方法的启发下,我思考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我曾经赖以建构“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的基石——空间分划、位置、距离、方向,在我“建构”它们的同时,就已经“晃动”起来,这两年,“晃动”得更厉害了。而且,我因此而把自己置于另一个我无法知道“邻域”的曲面上,使我在诸多不可知的恐惧之上,增添了另一份不可知的恐惧。
2014年,我写了一篇文章,《中古时代滨海地域的“水上人群”》。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通过解析文献中所见的“海上人”“白水郎”以及海螺姑娘的故事、“漂浮的罗浮山”的传说,去探究中古时代活动在滨海地域的“水上人群”的生活与流动,看他们与王朝国家间的关系,以及自我组织的方式。这是一篇立足于文献梳理与考证的文章,因为史料不足,证据不能完全落实,我不得不使用一些神话、传说“原型”解析的方法,并尝试着将“想象”运用到材料的处理与分析以及事实的构想上来。我知道这存在着一些危险,却仍然努力试图去突破自己。受到论文形式的限制,我不能在文中描绘我真正希望描述的一个图景:一个暴风雨的夜晚,乌云早已遮蔽了星空,一叶孤舟,漂荡在茫茫的大海上。他们的罗盘坏了,或者本来就没有罗盘。水手们疲倦至极,早已放弃了努力,任凭小船随波漂荡。后来,他们都死了,因为没有人会写字,也就没有“漂流瓶”留下他们的遗言。他们出海时并未登记,再完备的官府档案也不会有他们的踪影。但在那个夜晚,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那叶孤舟,孤舟上的水手,的确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没有位置,没有距离,没有方向,他们不处在任何一个“结构”里,无论是地理的,还是政治的、社会的乃至文化的。但他们确然“存在”过。时光穿越,一道闪电划过,我们瞥见了海面上的那叶孤舟,一闪即逝。当然,这不过是我在电脑前打了个盹而已。
在寂寥甚至略显空灵的暨南国际大学校园,随着那叶孤舟的亡魂,我越过南海,来到苏门答腊、爪哇、柬埔寨,开始研读这些地区发现的中古时代的碑铭。这些用梵文、巴利文、吉蔑文、泰文等文字书写的古代碑铭,经过 Georges Coedès,J.G.de Casparis等西方学者的整理、注释与研究,使我这个仅受中国正统史学训练的学者勉强可以阅读。有一方碑铭,发现于苏门答腊巨港附近的格杜干吉夫,它告诉我们: 682年 4月 23日(或 683年 4月 13日,不同学者的推算结果不同),一位国王乘船出发去远征。 5月 19日(或 5月 3日),他离开一个小港湾;一个月后,他胜利回归,赢得了巨大的财富、权力和荣耀。学者们相信,碑铭中未具名的这位国王,就是中国求法僧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所描述过的佛逝(室利佛逝)的国王阇耶那沙。两年以后,他又让人立了一方碑,上面铭刻着祈愿文,祝愿他的事业与功德能够普济众生,使他们开悟。我借助辞典,吃力地一点一点地读这些相关研究,有时一天只能读一页。恍惚间,我能感受到阇耶那沙国王可能正在瞪视着我,眼光里饱含着愤怒:这个待在台湾南投县埔里镇桃米坑的家伙,在企图把我放在一个怎样的“结构”里?内亚的、中国的、海域亚洲的,这个“三分结构”,是我这两年来逐步关注、有些朦胧认识的一个更为宏大的“结构”。可以断言,我永远不会真的试图去建构或研究这个“结构”,而将一直停留在阅读与思考的层面上。这不仅因为我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与精力,更因为如上所言,我已经对“结构”及其思想方法失去了信心。可是,我一定要说明,把“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置入一个更为宏大的“结构”中去观察,也是对“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的一种“解构”。
《历史中的“时间”与“人”》
现在,我们在这里读《汉书》,这是一个事件,就如同把石头投入池塘一样。这个事件有它的将来:读书的涟漪将在空间与时间里散布开来,形成一个圆锥。它的顶点是《汉书》。《汉书》的形成是一个圆锥:这个圆锥里包括了其所记载的诸多人与事,以及其他。通过阅读《汉书》,我们在现在的阅读、阅读的对象(《汉书》),以及《汉书》所记载的人与事等之间,建立起以时间为轴线的、由一连串圆锥所组成的图画。这个图画,将历史认知与历史过程联结起来,也就是将站在今天的池塘边的我们、池塘里不息的涟漪,池塘与石头以及他们的生成与关联,串联在一起;将之串联在一起的,就是时间。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不仅是在时间里展开的,而且是在时间里被认识的。
霍金以太阳熄灭为例,讲现在与过去的关系。他说:假定太阳就在此刻停止发光,它不会对此刻的地球上的事情产生影响,因为它们是在太阳熄灭这一事件的他处。我们只能在 8分钟之后才知道这一事件,这是光从太阳到达我们地球所花费的时间。只有到那时候,地球上的事件才在太阳熄灭这一事件的将来光锥之内。类似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一时刻发生在宇宙中更远处的事:我们看到的从遥远星系来的光是在几百万年前发出的,发出那些光的星体也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当我们看宇宙时,我们是在看它的过去”。
同样,当我们看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时,我们是在看它的过去。当我们透过池塘边的涟漪认识到石头扔入池塘这一事件时,这个事件早已成为过去,导致这一事件发生的诸多事件与因素更是在这一过去的事件之先。事实上,当我们观察这个世界时,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事件,都如同石头落入池塘的事件那样,均已是过去发生的事件。而我们之所以要去看这个世界,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所发生的诸多事件都与我们相关——或者影响到我们,或者我们就是事件的参与者,或者两者兼具。
我们就处在历史认识与历史过程的圆锥链中,是这个圆锥链的一个点。正因为此,在讲义里,我一直强调,我们读史书,是给自己读的,不是给古人读的。我们之所以要从池塘的涟漪去追溯石头扔入池塘事件,是因为我们站在池塘边,而即使我们自己没有扔,也还是有很多石头被扔到池塘里。如果今天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石头掉入池塘的事件发生,我们大约也不会注意到池塘里很久以前落入石头所留下的涟漪。或者,这个世界竟是没有了池塘,也没有了石头,当年石头落入池塘的涟漪也更无从寻踪了。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可能曾经有很多的“太阳”熄灭了,也有无数的“池塘”和“石头”不再存在。它们没有留下光,没有留下涟漪,所以,它们不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也可能不在我们的认知世界里,它们在“他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论断曾经给我很大的影响。有所不同的是:我相信在过去与现在所组成的圆锥链之外,有“他处”的存在。“他处”在过去存在过,当下却已经没有了;而且由于没有留下“光”或“涟漪”,我们也无从认知它。但是,“他处”绝不是没有意义的,它包含了历史发展的其他可能性。在没有或只有较少“光”与“涟漪”,甚至没有池塘与石头的情况下,去追寻“他处”的石头扔入池塘事件,并追问此类事件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原因,亦即探究“不在当代”的过去的历史,常常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汉书》讲义中有所涉及的一些“绝响”,就是这种吸引所留下的结果。
因此,当我们看这个世界时,不仅看到的是这个世界的过去,还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他处”——它告诉我们,世界原来还可能成为另一种样子的,甚至可能成为好几种样子。另一种样子的世界的可能存在,给我们一个或更多的梦想,使我们对世界的未来抱持着希望。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在特别重要的事情将要发生之前,时间过得非常慢,时钟的分针与秒针好像都黏滞了,走不动,所谓“度日如年”就是对这种感觉的描述;而在紧张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往往感觉不到,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当我们回首往事,对人生中某些重要的时刻及其所发生的事情,记忆深刻而清晰,我们甚至可以以小时为单元回顾某些重大事件;而对于大部分平淡的岁月,却往往只是一闪而过,用几句轻描淡写的话,就“顺”过去了。
这里,我谈到的是两种感知的时间:前者是在历史过程中的时间感知,是历史过程中的人所感知的时间,它本身就有慢与快两种,其快慢之别,主要取决于人在这一事件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以及事件对于感知者的意义。后者则是记忆中的时间感知,是记忆者对历史过程中时间结构的记忆、想象与重建,在这个过程中,时间被拉长、放慢或压缩、加快,其快慢之别,取决于回忆者对历史过程的记忆及其对记忆内容的主观判断。
历史学是一门关于时间的学问。从近代科学理念与方法出发,人们强调时间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均质的,因而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加以度量的。但是,这个均质的时间,却与我们感知中的时间并不一致,我们在日常生活与阅读中,时常感受到这种冲突。如何解释这种冲突呢?
我们知道,广义相对论的预言之一,是说在像地球这样的大质量的物体附近,时间显得流逝得更慢一些,因为光能量和它的频率有一种关系:能量越大,则频率越高;当光从地球的引力场往上行进,它失去能量,因而其频率下降,这表明两个相邻波峰之间的时间间隔变大。人们利用一对安装在水塔顶上和底下的非常准确的钟,证明了这个预言:水塔底下那只更接近地球的钟走得较慢。地球上不同高度的钟的速度存在差异,现在已成为常识。
受到这些想法的启发,我去思考:不仅在我们的感知中,时间是不均质的,有快慢之别,即便在客观的历史过程中,时间很可能也不是均质的。在历史过程中的某一个时间段内,事件发生的频率相当高,各种人物、人群密集交会在一起,在每一个固定的时间单元里,都有非常多的事件发生,有非常多的人参与其中,从而使时间放慢了步伐。时间是慢的。反之,在更长而事件发生较少的时间段里,时间悄悄地流逝,它是快的。换言之,历史过程中时间的快慢,是与参与其中的人与所发生的事件的密集程度成反比的:人物与事件越密集,时间越慢;反之亦然。当然,这是就同一个空间下不同的时间而言的。
2015年4月,我随同暨南国际大学的师生,到南投县山区布农人的部落里去实习。我们这一群人的到来,不仅打破了山谷的宁静,还很可能改变了布农人的时间: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天有了太多的事情要做,要说更多的话,时间因此而变得漫长。不仅如此,这些学生晚上还升起了篝火,拉着他们聊天,从而在客观上也拉长了他们的一天。
我们都熟悉所谓“天上一年,地上百年”的说法。在很多神仙的故事里,描述一个人因缘际会,来到神仙洞府或天上仙界,与神仙下了一局棋,之后,回到家乡,却早已物是人非,几代人过去了。很长时间里,我不能明白这类故事里时间发生变化的原因。现在,我可以给出的解释是:天上的神仙太少了,而且他们无事可做。
时间的相对性既表现在我们的感知里与认识里,也表现在客观的历史过程中,更重要的,它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它让我们去思考:对于不同时空下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生存环境与行为方式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时间测量、理解与认识,而只有这样的时间对他们来说,才有意义。
所以,如果说在《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中,隐含于各种论述背后的,是空间的相对性的话,那么,在这本讲义里,我隐藏着一个思考的前提:时间的相对性。在我的思考中,时空都是相对的:空间不再仅仅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舞台,而更多的是由人类参与设计、制作并改造的生存场所以及生存方式;同样,时间也不再仅仅是历史过程得以展开的纵向轴,而更多的是由人类及其不同群体给予界定、划分并可以随其感知与愿望而拉长或压缩的一个因素。时间与空间不再是人类历史的背景,而是人类历史的动因之一,时空的结构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同时又在历史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结构。换言之,时间与空间不仅影响着人类的历史进程,而且被历史过程的每一件事或人所影响着
夜晚的星星,是最有魅力的。我把它们比作人类的思想者。我希望自己在天空中看到的,是思想的光芒。帕斯卡尔说:“人显然是为了思想而生的;这就是他全部的尊严和他全部的优越性;并且他全部的义务就是要像他所应该的那样去思想。”我们(特别是作为读书人)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如果人类没有思想者,也许就不成其为人类;而如果我们(读书人)没有思想,我们将失去尊严乃至生存的意义。思想的永恒性,也许不过是一个读书人的自我期许或梦想吧。
而且,一个历史学者,应当同时或者首先需要是一个思想者。他需要确定哪些历史事项是可供研究的、研究它有什么意义,以及怎样才能弄清它。这里涉及对历史过程的基本认识、过去与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历史文献记载与真实的历史过程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既有历史本体论,也有历史认识论。何兆武先生说:“对历史理解的高下和深浅,首先取决于历史学者本人思想的高下和深浅。”我赞同这一认识,并且尽可能朝成为一个有见识、有思想的历史学者的方向去努力。
当然,天空中最为耀眼的,是太阳。我很少看见,偶尔想看看,也无法细看,因为它太过耀眼。如果把“虚无”换成“短暂”,也许更能表达我的真实想法。任何功业都是短暂的,它从孕育、养成、成就,到极盛、衰退与崩解,是一个生命历程。王朝、国家亦复如是。人生苦短,功业自然如过眼烟云。同样,如果把“永恒”换成“久远”,也许更好一些,因为我前面已经提到,我相信时间是有始终的,所以无所谓“永恒”或“无限的时间”。久远的思想,是指对人类能够产生久远影响的思想,因而也就是具有普适性的思想。
关键在于多么长的时间是短暂的,多么长的时间又可以称作为久远的?布罗代尔曾经谈到:任何历史研究都关心如何分解过去的时间,根据或多或少有意识的偏爱或排斥,选择不同的编年现实。他说:传统历史学(他那个时代的传统历史学)关心的是短时段、个人和事件,其叙述节奏往往是急匆匆的、短促的,其所描述的历史侧重于历史这场大戏中的一个或几个场次,一幕或几幕戏(折子)。短时段对应的是个人(先不说是怎样的个人)与事件。这样,历史过程就可以看作由几幕戏(折子)串联而成的一出大戏,它由一堆各种各样的事实与人物构成,它们构成所谓微观史学的研究对象。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微观史学不免会受到“碎片化”的批评。但是,时间毕竟是由一天天积累而成的,历史过程也毕竟是通过具体的人与事件展开的,微观史学的魅力正在这里。
王朝史或断代史实际上可以视为一种中时段的研究,其所探究的核心,乃是王朝国家兴衰的周期性,既包括政治变迁的周期性,也包括经济与社会变化的周期性(在中国古代史中,后两者往往被看作是从属于前者的)。经济与社会史研究侧重于经济与社会变化的周期性运动,其所关注的相应时段从数十年到数百年不等。中时段的研究撇开或不停留在对具体事件与短暂的政治、经济或社会变动的分析上,把着眼点放在总体局势及其变动的把握方面,并最终指向“结构”或“形态”——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乃至文化结构,或者最后归结为特定时段内的“历史结构”——及其变动上。
对于“结构”或“形态”变动的考察,理所当然地把研究时段拉得更长,从而引出了“长时段”的概念。它试图在周期性变化的基础上,探讨超越周期性变化的长期趋势,并进而追寻制约或影响此种长期性趋势的内在因素——这并不必然导致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也可能找到其他的解释,比如社会形态或文化,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以及文化史观指导下的历史叙述与阐释,都属于长时段的研究范畴。“结构”、“形态”与“文化”三个概念,支配着长时段研究的思路。其中,“结构”是近二十年来对中国史学研究影响最突出的概念。布罗代尔说:结构是在一段长时期里由时间任意支配并连续传递的一种实在;某些结构有很长的寿命,因而它们成为历经无数代人而稳定不变的因素;它们挡在历史的路上,阻遏历史的流逝,并以此规定历史。结构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制约或规定历史的发展。这一思想对我影响很大,在《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中有比较明显的表现。
在文化史观指导下对某些文化要素的分析,逐步超越了长时段研究的目标,因为它必然要进一步追问:哪些文化(广义的文化)因素不仅在长时段的结构、形态或文化演变中发挥作用,而且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中,一直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虽然作用的方式与意义可能不同)?这就是对人类发展的终极动因、关怀的追寻。其中可供历史学者研究的部分,主要是久远不变的需求、情感、行为模式以及久远发生作用的知识、思想和隐藏在其后的思维方式等。
历史过程中的人,是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怎样落实它呢?我们知道,进入历史学家视野或者说在历史文献中得到记载的“人”,绝大部分是从国家(王朝国家或民族国家)的立场予以界定并描述的,所以,我们必然要从其“国家身份”入手。我们分析汉高祖、武帝的“人”的一面,当然要先看他们皇帝的一面。剥掉其皇帝的外衣,才能看到他们的躯体;透过其威权的势场,才能洞察其心理、情感与思想。但即便剥掉他的皇袍与光环,他也还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因为他的“人性”被“皇帝性”所覆盖了。我会说:皇帝不是人。虽然有些极端,但意思是明白的。同样的,官僚和准官僚也不是人,因为其行事与思想的根本原则,是官场规则或政治理性,而不是人性。《汉书》讲义中的编户齐民,也主要或首先是“民”,而不是“人”。我们现在要从这些“人”的国家身份——皇帝、官僚、侠客、儒士以及编户齐民——入手,将他们“还原”为“人”。当我看到汉武帝发愁(虽然是为怎样做皇帝发愁)、后悔、怕死,我相信(没有充足证据地相信)他这个时候是人,不全是皇帝。同样,那位告别妻子、挟剑而去的侠客也是人,唠唠叨叨地让百姓种菜养鸡的龚遂也是人(不全是渤海太守了)。至于肤色较黑的王女、耳和孙时、第卿,就更是人了。
更具体地说,在研究过程中,我试图首先弄清楚历史过程中的一些人或人群,他们的国家身份是如何获取的,具有怎样的意义,然后去窥视其在国家身份的背后作为“人”的真实状况。而最好的办法,显然是看他们在获得特定的国家身份之前的“自然人”状态。在《释“蛮”》《“越”与“百越”:历史叙述中的中国南方“古族”》《中古时代滨海地域的“水上人群”》《楚秦汉之际的“楚人”》等论文中,我一直尝试用不同路径,去观察那些未进入或尚未被全部纳入国家控制体系中的各种人及人群,看他们的本初或自然状态。至于我所看到的和描述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他们的本初或自然状态,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除了国家力量所未及、逃亡等可能的形式使历史过程中的人可能未获得、脱离或暂时脱离“国家身份”之外,还有一种脱离方式,那就是死亡。在死亡面前,人基本上是平等的,而死亡使人程度不同地得以脱离其国家身份。关于死亡的构想以及死亡的处理方式,可能使我们能够观察人的部分本来状态。在关于买地券的研究中,我注意到这种可能性。
我们去讲历史过程中的人,无论是个人还是人群(群体的人),都只是历史过程中人的一部分,极少的一部分,每个人或人群都有自己的特征、利益诉求、行为方式,并因此而结合成不同的社会,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揭示这种多样性固然极具魅力,由此而形成的历史叙述虽然丰富却不免枝蔓零碎;而建立在多样性历史叙述的基础上,必然会提出多样而多元的历史分析与解释,历史解释的多样性与多元化则必然会加剧这种研究的碎片化。那么,我们怎样塔建这种研究的架构,以使它不至于太过零碎呢?
我本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姚大力老师的提问促使我去思考。我目前大致的想法,是想以出生、受苦、死亡三个环节,作为构想人的历史的基本框架。他们出生,他们受苦,他们死亡,是句老套的话,却正可以看作人的基本轨迹。每一个人,每一代人,每一群人,以及人类总体,都无法逃脱这句老话的桎梏。我相信逐步的研究会给这三个环节赋予越来越丰富的内涵,比如出生,不仅是指一个自然人的出生,他的政治与社会身份的获取,都可以看作“出生”的过程。同样,受苦与死亡的内涵就更为丰富了。如果我们根据人在这三个环节中的生命轨迹来叙述历史过程,那会是一种怎样的历史呢?有可能做到吗?我还完全不知道,但这种可能的前景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
《学问须于不疑处有疑》
历史著述中最多而且也是最难理清的“增益”,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造神运动”而在本来比较简单的历史事件、人物或其思想身上堆积了越来越厚的粉彩,这些粉彩一层层地累积起来,遮盖了历史的真相,并且形成了更为庞大的历史叙述与阐释系统,常常使我们在读书时不知所云,无所适从。
讲到这个问题,当然不能不提到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顾先生对于古史最早的怀疑,“是由《尧典》中的古史事实与《诗经》中的古史观念相冲突而来”。他将《诗》《书》和《论语》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作比较,发现禹的传说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的传说到春秋末年才产生,这个古帝的传说越是后起,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禹又是晚辈了。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与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这个假设的意思是:战国、秦、汉以后的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是由先后的不同时代的神话一层一层累积起来的,不同的古帝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具体地说: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了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等。因此,他主张将古史的传说层层剥离,把每一件史实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研究其渐渐演进的过程。顾先生关于古史的许多具体论点,现在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但他的这种思想方法,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不仅古史如此。事实上,历史知识系统中相当大部分的“阐释”,特别是关于历史原因与意义的解释,很多都是“增益”上去的。以五四运动为例。在我们的心目中,五四运动的伟大及其划时代意义是无可怀疑的。但五四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并没有太多的伟大感,也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在从事一项将改变历史的伟大事业。舒衡哲在《五四运动新探》中指出: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为数不多的一批知识分子为唤醒自我而进行的一场软弱无力且混乱不堪的运动”。随着五四运动成为一个伟大的事件,围绕着它无数的人写下无数的文章与著作,其中有多少是五四运动的“本事”,有多少是后人为适应某种需要而加上去的?我想,可以直白地说:增益的部分,要多于属于其“本事”的部分。而且,也如古史系统的层累一样,对同一历史事件、事实或过程的阐释,也是越晚出的阐释(或者说越“新”的阐释)越居于历史知识体系的最上层,并广为传播,成为构成大众历史知识体系的最主要部分。
其次,历史学这门学问,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最大特征之一,乃是我们知道“结果”,那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界。历史学家们知道“结果”,是从“结果”出发,去探究形成这个结果的“过程”,分析其“原因”,赋予其“意义”。一个历史学家撰写一个朝代的历史,这个朝代已经灭亡了,所以他自然而然地、轻而易举地将它划分为“兴起、鼎盛与衰落”三个时期,然后具体落实到时段上,并分析每个时期的特征及其原因。显然,你很难相信一个生活在乾隆时代的人,知道自己正处在大清盛世,过些年,清朝就要走下坡路了。这种在知道“结果”的前提下,构建出来的叙述框架或者结构,是历史学家加于历史过程之上的,但历史的结果却并不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唯一的可能,而只是诸多可能性的一个而已。因为知道“结果”,从而使历史学家可以将前后发生的一些在当时看来也许并不相关的事件联系起来,并赋予在事件发生的当时并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可能为事件的参与者所知的意义。
不仅如此。所有的历史著作(即使是其中最出色的那些)也都是对过去的高度简化与浓缩,而不是对所有历史现象、事件、人物及其思想的重现。实际上,“按原样恢复历史”是不可能的。当我们谈论历史时,更多的时候并不是指实际发生的事情,也不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宇宙乱象,而是经过整理后写进书中去的历史,是历史学家对时空和人物的观察与叙述。任何历史著作都是对过去的一种叙述与解释,而事实是错综复杂的。换言之,历史过程是凌乱、复杂和不明晰的,而历史著作则是把杂乱无章的历史过程条理化和明晰化了。以义和团运动为例,我们知道,一个人参加义和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饥饿、仇恨外国人、复仇、不参加会给家人带来不幸等,研究义和团运动就是要在诸多的动机中找出一些有意义的范式,把特别复杂和混乱的事件清楚而完整地描述出来,且能言之成理。这样,一个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者就要回答:义和团运动为什么会爆发?它怎样爆发的?它为什么失败?这样,历史学家们就写了很多书、文章。最后,历史著述范式对历史事实与记载的改造,使历史著述对历史的叙述与阐释很可能程度不同地偏离了历史本身。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所谓“规范”,有的还称之为“家法”。任公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及清代正统派学风之特点,举出十点:
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
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文体贵朴实简絜,最忌“言有枝叶”。
这里虽然有十条之多,其要旨却只有一条:“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这一条,真可说是历史研究的根蒂所在,所以,有人说,历史学是一门讲究证据的学问,或者是以证据为基础的学问。看上去这里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在我们上面讲了那些原始材料之不足信之后,又有谁敢说那些证据就是那么可靠呢?孤证不为定说,诚然,所以历史研究就是要罗列尽可能多的证据,然而,这里的前提果真就没有问题吗?证据越多,就越真实?“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也是不错的,但谁又能确定一个汉代人的胡说八道,就一定比一个唐人的胡说八道更有道理呢?“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那么,如果公布证据或正解证据,是有害的,可怎么办呢?所以,历史研究的讲究证据,是有限度的,也可能不全是有道理的,它可能带来一些混乱,认为有证据就是可靠的、真实的,甚至是真理,就太过绝对了。
《秦汉帝国的形成及其他》
澎湃新闻:为什么古代史书里主要记载的是帝王将相,而缺少平民百姓的生活?
鲁西奇:第一,那些史书是写给帝王将相或帝王将相的候选人看的(至于他们看不看,那是另一个问题),是为他们总结治理国家与社会的经验教训的,写史书的人,一般也是帝国将相集团的一分子。这里补充一句,所谓帝王将相的候选人,也就是陈胜、吴广、赤眉、绿林之类,他们是作为王朝国家的对立面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并被记录下来的,是贼、盗、寇。如果他们成功了,就会成为另一批帝王将相。他们曾经是普通百姓,但在历史叙述中,却是作为失败的帝王将相候选人而得到记录的,已经不再是普通百姓。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只是作为王朝国家的“编户齐民”,也就是在国家户籍编排、管理、统计册上被记录的符号,以及需要向王朝国家纳税服役的“户口”而存在的,并不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
第二,平民百姓没有话语权,他们甚至没有话语愿望。前一句话不需要说明,关于后一点,在《汉书》讲义里,我曾经这样写道:千篇一律的图景、日复一日没有变化的生活、面貌性情均雷同相似的人,都很难引起我们的回忆。长期生活在单调“正常”环境中的人,生命的轨迹既然已经确定,回忆也就变得越来越奢侈,从而逐渐失去回忆的愿望,最后导致了回忆能力的衰退。这就是“淡漠”。“淡漠”包涵了三层含义:一是生活的平淡,生命轨迹的模式化;二是人与事件的类同,过去与现在乃至未来也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三是回忆能力的衰退,偶有回忆,也不再能转化为记忆,更不能成为生命和历史中的记忆。在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中,有关芸芸众生的叙述非常之少,有很多原因,最根本性的原因,大概是他们的生活不被他人所“回忆”,他们自己的回忆则得不到记录,其总的根源,在于他人以及他们自身的“淡漠”。一句话: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太单调枯燥了,我们自己都不想提起它,更不觉得有写下来的必要。更何况,我们想写下来也做不到,说不定还会惹来祸端。
第三,偶或有之,也不会被不是平民百姓的后世史家所注意。古代史书中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关于平民百姓的记载,认真看看,还是挺多的,只是后世读书的人,有谁是甘于做平民百姓的呢?带着不想做平民百姓的心去读史书,遇见平民百姓的记载,也不会留心的。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