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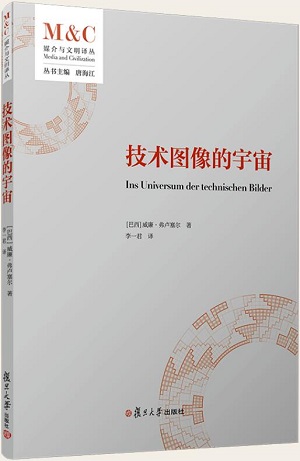
复旦大学出版社《技术图像的宇宙》(订购)
视频或者购物软件总是给你推送你想看到的内容或商品,家庭聚会中大家各自玩手机却不与彼此交流……
这些眼下社会中常见的社会现象,早在1985年,就已经被巴西哲学家威廉·弗卢塞尔预见了。他在书中提出:未来社会中人与技术图像之间的互动最终是导致两者的无限趋近,这种传播方式也使得社会愈发分散、人们愈发孤独。
媒介技术是怎样深深地影响社会的?我们需要去它们的源头——“技术”中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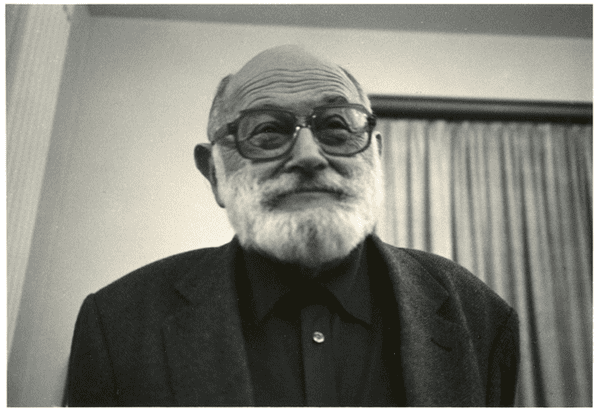
威廉·弗卢塞尔
“在当代社会中,处于中心位置的是技术图像,而不是人。这意味着在未来社会学研究中,人们必将被驱离中心,走向边缘。”
——威廉·弗卢塞尔
1 无法逃离的图像
人与技术图像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是未来文化批评的核心,这种互动中最发人深思的,就是其特殊的投射方向。技术形象指向一个人,挤压着他,在哪怕最隐秘的私人空间里找到他。
技术图像通过无数渠道(电视频道、图片杂志、电脑终端)嵌入私人生活,它们取代和改变了原本存在于公共空间的信息传播,同时也封锁了公共空间。由此,人们不再从私人场所走向公共空间,这既是由于人们能在家里更好地获得信息,也是因为公共空间已不复存在。
技术图像的渗透力将接收者逼到角落,它会使人们承受压力,诱导他们按下按键,从而让图像在角落里浮现。因此,“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不开电视、不订报纸、不拍照片”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乐观的无稽之谈。人们如果要对抗技术图像的渗透力,就要脱离社会。技术图像的确孤立了那些蜷缩在角落的接收者,但它把更严酷的孤立施加在那些远遁于它的少数人身上。
2 形成闭环的图像与人
然而,技术图像的接收并不是传播的终点。接收者不是粗放吸收信息的海绵,相反,他们一定会作出反应。在外部层面,他们会根据自己接收到的技术图像采取行动:他们买某种肥皂,去某地度假,为某个政党投票。但是,对于我们正讨论的图像与人的互动而言,关键在于接收者对图像会作出一种内在的反应:他们“哺养”图像。在图像与接收者之间存在一种反馈的回路,它使图像越来越冗余和累赘。图像拥有反馈渠道,这种渠道的运作与信息散播的渠道相反:它将接收者的反应传递给信源,比如市场分析、人口统计和政治选举。这些反馈使图像应势而变,日渐精进,变成接收者所希望的样子。这样一来,图像越来越贴近接收者的希求,而接收者也越来越贴近图像的希求。简言之,这就是人与图像的互动。
让我来举两个这种互动关系的例子:一个是电影,一个是电视节目。
电影
人们坐在昏暗的屋子里,盯着闪光的、展现着巨幅图像的银幕,为了坐在那里,他们得站成一行,然后被分配到几何排布的座位上。在此,一个算术意义上的行就成了一个几何结构,被几何式排布之后,人们就安排自己舒适地接收节目(也接受编排)。他们从思考的实体变成一种几何式延展的实体。笛卡尔关于思考主体与延展客体的同化问题在影院里得以印证。当银幕上的形象开始跳动而不是滑动时,接收者就知道放映机出了问题。如果接收者是柏拉图式洞穴中的奴隶,那么他们会欢迎这种情况,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从“看影子”的囚禁中解脱出来一步。然而,这时,影迷们往往会调头对着放映机大发雷霆,因为他们买了票却被辜负。观众与辜负观众的银幕之间存在着一种共识,那是一种在银幕与观众间的反馈中建立起来的契约。当前的影迷是由此前的电影“哺养”的,而当前的电影则是由以前的影迷“哺养”的,这种相互哺养的关系越是绵延不绝,这种图像与人的共识就越是稳如磐石。
电视
巴西足球队与德国足球队在东京比赛,一个巴西科学家通过家里的电视观看这场比赛。他是那群试图逃离技术图像宇宙的人之一,对他而言,球赛是使人异化的手段,他蔑视它。但是,迫于技术图像的压力,他还是打开了电视并被节目迷住了。为了抑制自己的激情,他开始计算球员影子的长度,推算在夏季巴西的晚上与冬季日本的白天里影子长度的差异。他想要赶走魔法(即科学地解释它),打破咒语,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屈服于这些魔咒,因为节目激活了他埋藏已久的性格层面(例如爱国情怀与好胜心)。起初,他以为自己的激情是来自激情洋溢的巴西运动员,但经过一番批评性分析,他发现这些运动员之所以激情洋溢,是因为他们知道,同样激情洋溢的观众正在看着他们。这些运动员的行为并不是作为比赛的功能而是作为图像传播的功能而存在的,他们所做的不是(或不主要是)参与游戏,而是参与电视图像。因此,这些热情是图像与人之间反馈回路的一个侧面:图像越是激动人心,接收者就越亢奋,接收者越是亢奋,图像也就越是激动人心。甚至当人想要抗拒这种图像的魅力时,这种反馈依然运转不息,人与图像之间的这种共识通过反馈而被自动加强,使每个人都成为接收者——无论他最初是否愿意。这种共识构建了技术图像主导的社会核心。
图像和人之间似乎已经建立了一种闭环式的反馈回路:图像展示了一台洗衣机,想让我们买它,我们也想让图像展示那台洗衣机,因为我们想买它;或者说,图像展示了一个政党,想让我们选它,而我们想让图像展示那个政党,因为我们想要选它。但是,实际上这个线路是不能封闭的,因为到那时,图像就会陷入一种熵的衰变之中。这意味着它们会始终是同样的图像,无休无止地重复显现着。为了让情况变得更好(即为了给接收者带来新的内容,为了能够以新的方式编排程序),图像必须从接收者以外的其他地方获得反馈。
图像在历史中,在政治、科学与艺术中,也在所谓日常生活的事件中获得哺养,它们不仅从当下取材,也挖掘往事。一张照片可能展现一场政治游行,一场电影可以讲述本周的战事,一个电视节目可能重现19世纪的实验室,一盘录像带则可以使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跃然于屏幕。这样看来,技术图像似乎是一个窗口,那些蜷缩在角落的接收者可以通过它们观察到外界正发生的事情。同时,这些图像似乎可以永远自动更新,因为外面的世界总是日新月异,图像内容的来源(过去的历史)似乎取之不竭。然而,仔细观察之后,人们却发现技术图像类似于窗口的属性以及过去与未来历史的无尽性,其实都是谬误。
3 孤独的大众
技术图像位于社会中心,但因为它们向四周渗透,所以人们并不会拥挤在它们周围,而是向后退,进入各自的角落。技术图像辐射四周,每条射线的一端都单独坐着一个接收者。就这样,技术图像把社会掰碎,散播到各个角落。每幅/套技术图像(除了上文所述的电影)都被射线的端点,即一种“终端”接收。所以,这种涣散社会所生成的并非不规则的元素堆;相反,角落依照从中心向外围的辐射结构进行分布。这些射线(渠道、媒体)像磁铁吸引铁屑那样构造了社会,技术图像如磁力般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把社会分散开来。这样的社会是有结构的。通过分析媒体,这种结构就能浮出水面。媒体组成束,从发送者,也就是中心发射。在拉丁语中,“束”对应的词是“fasces”。因此,一个由技术图像统治的社会结构是法西斯式的。这不是出于任何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技术原因。伴随着技术图像的运作,社会走向法西斯化。
这种社会结构是在几十年前才开始出现的,它就像潜水艇一样破冰而出,冲碎了以前的社会结构。随着它的突现,家庭、民族、阶级这些捆束着人类互动的社会性群体分崩离析。然而,相比于新社会结构的兴起,社会学家和文化批评家更关心旧社会结构的衰落;相比于冲破冰面的潜水艇,他们更关注支离破碎的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称其为一个衰落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新兴的社会。他们评判着已经逝去的而非新兴的社会结构:在家庭方面,他们批判极端的男性霸权;在民族方面,他们谈论沙文主义;在阶级方面,他们畅聊阶级斗争。他们抨击逝去之物,就像猛踢一匹已死的马。
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批判的盲点,因为人们的熟悉感使得已经衰朽的社会形态显得神圣,比新的社会形态更引人注目。举例来说,家庭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人们重视构成家庭的人际关系(例如男女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当家庭分崩,其包含的价值也随之逝去。因此,对衰落的家庭提出建设性意见(例如,建议采用其他家庭模式,如开放型或合作型)似乎是有道理的。事实上,把家庭从电视或计算机的影响中拯救出来的每一次尝试都是无望且反动的。旧的社会形态如海上漂浮和溶解的冰片。
当前的文化革命是技术上的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因此,诸如“自由党”和“社会主义者”及“保守党”和“改革派”这些我们承袭的政治范畴不再适用。这可能会让批评者感到困惑,但真正彻底的变革总是技术性的变革。以新石器时代革命这个据我们所知最翻天覆地的变革为例,这场革命萌发于对新农业和畜牧业技术的使用。
这些技术瓦解了中石器时代早期形成的社会结构,引领新的家庭、村庄、战争、私有制和奴隶制产生。革命之后,这些新的社会形式被神圣化,被赋予价值。所以,真正的革命者并非新石器时代精神信仰的创始人,而是奶牛和面粉的发明者。如果从过时的意识形态立场来评价这场革命(例如,评判猎人的价值),当代批评家们就会错过要点。第一次工业革命也能证明这一点,它也是技术性的,其革命者是机器的发明者,而且他们创造的社会形式(例如,无产阶级)只有在马克思或列宁这些虔诚的思想家们回顾历史时才显得熠熠生辉。
当今的革命者不是卡扎菲或梅茵霍芙,而是技术图像的发明者,尼埃普斯、卢米埃尔以及无数鲜为人知的计算机技术发明者。正是这些人带来了新的社会形式。因此,如果想要建立一个人道的社会,我们必须了解新技术,而不是更崇高的价值,例如,我们需要探寻是否可能在技术层面修改辐射状图像构成的法西斯式结构。
从过去的角度来看,通过技术图像解构传统社会群体(例如,通过电视打破家庭或通过卫星解构国界)的行为似乎是一种堕落:社会堕入角落,困在“孤独的大众”中间,人际关系、社会组织也都消融了;那些在电脑前背向而坐的加州年轻人没有社会意识,他们不属于任何家庭,也无法通过国籍或阶级进行区分。从非意识形态的、现象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会认识到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组织的表象,也可以摸索出将这些新用户绑定成束、连接到技术图像发送者的那些线。从当下看,我们所面对的不是非社会化的人,尽管看上去形单影只,但在新的意义上,他们实际上是深度社会化的。这种社会化程度之深,使面对这群人的我们有理由为他们是否还保有个性而担忧。
本文节选自复旦大学出版社《技术图像的宇宙》(订购)
来源:复旦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