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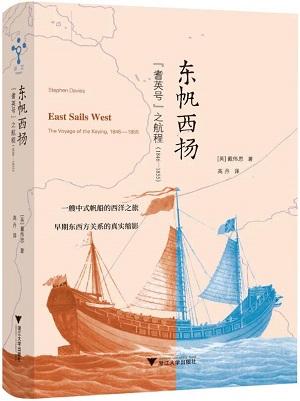
浙江大学出版社《东帆西扬:耆英号之航程》(订购)
鸦片战争结束后,一群想发财的人聚集在香港,投资建造了一艘准备驶向远洋的中式帆船。他们给这艘船以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的大名命名,这艘船也成为第一艘也是唯一一艘自行从中国出发经好望角驶入北大西洋的中式帆船,同时,它也是有史以来第一艘既抵达了英国又造访了美国东海岸的中式帆船……
《东帆西扬:耆英号之航程》完整记录了这艘中式帆船的历史:在1846年至1848年间,耆英号的这次航行由一群香港投资人组织,他们中有些人后来成了香港一些主要机构的创始人。执行航行任务的船员东西方混杂,其中一小部分是英国高级船员和水手,大部分是广东水手及其船长。随同航行的还有少许乘客,包括一些投资人、一名真伪莫辨的五品文官、一名画师,甚至还有一名裁缝、一名道具商人和一个有名的戏班子。由于天气和帆船性能的双重原因,这艘船不得不折向美国东海岸,分别在纽约和波士顿停留,经历多起船员闹事分裂和起诉事件之后,这艘船最终抵达伦敦。
这是唯一经证实驶入过大西洋并抵达美国和欧洲的中式帆船。其目的既非科考也非探险——此二者是十九世纪非商业非战斗航海活动的主要目的,这次航行具有典型的香港特色:“它是一项商业策划,意在通过向游客展示船员们在甲板上的生活场景以及甲板下面船舱内收集的古怪的中式物品来赢利。”这艘船的航行过程非常缓慢,它临时绕道美国,再加上船员间发生纠纷以至于在纽约对簿公堂,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它的航程的拖延。预期4到6个月的航程实际花费了15个月。而在伦敦,一项过于冒险的商业计划让整个项目每况愈下……
在《东帆西扬》一书的作者看来,“耆英号”的故事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其一,有一艘中国帆船进行了一场独特的史无前例的航行,无意之间实施了一次跨文化合作的实验——鉴于当时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其结果就像航船驶入了黑夜,除了零星的记录,几乎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其二,这艘船是抵达欧洲的唯一一艘尺寸完整且运转正常的中式帆船,代表了中国传统的造船工艺。“它抵达欧洲的时间恰逢维多利亚时代对一切事物的科学兴趣使得建造浪潮达到顶点之际,然而,它的故事不论从科学角度还是民族学角度来讲,都全然被忽视了。”
“为什么这次航行没有造成持久的波澜——就我们所知,它在中国甚至没有掀起短暂的涟漪?海洋社会学为什么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不论是对这次航行还是对这艘船,东西方几乎都没有产生重要的学术或大众兴趣?”这是该书作者的疑问,也是该书所解读的历史。“这艘帆船及其船员于1846年12月6日离开香港维多利亚城的新码头之后便踪迹皆无:没有留下故事;没有人研究它、建造复制品;没有一家机构从这个冒险故事中发现一个可供宣传、为自己的社会责任博取赞扬并通过副产品获取收益的载体;没有一家电视或电影公司从中预见到一部扣人心弦的纪实系列片及利润丰厚的衍生商品,并为此激动不已;没有一个政府从中看到提升本国航海实力、获取远方殖民地的机会……”160多年后,这本《东帆西扬》打捞出了这艘帆船的故事。
在该书作者看来,“耆英号”为解析中西方船舶建造的差异提供了一个独具吸引力的机会,假如能被善加利用,维多利亚时代的造船师将会大为吃惊,因为当时是19世纪40年代,铁制(再后来是钢制)船舶正迅速取代木制船舶,西方造船技术正面临一个困扰他们了半个多世纪的难题。简单说来,西方造船师的困惑是:要继续采用“先造骨架”的方式用金属和铆钉打造一艘金属船舶吗?从建筑学角度而言,这些船舶跟木头、螺栓和钉子没有什么区别,这种造船方式是最好的吗?该建造方式自17世纪晚期以来就处于主导地位,而且随着船舶体积的增大而变得越来越复杂。木船时代间隔密集的横向架构对钢铁而言是最合适的吗?
另外,“耆英号”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是因为尽管有当时的文件记录,但人们对于它究竟是一艘什么样的船缺乏细节上的认知。那些船员到底是谁?它空前绝后的旅程又经历了怎样的人事波折?航程结束之后,它和它的船员们有何遭遇?这些我们几乎都无从知晓。而且对于大多数中国船员的命运,除了零星的报道,我们更是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它没有留下日记或航海日志,不过也许可以期待有一天在阁楼和拍卖行里能偶然发现一点蛛丝马迹。现存的文件记录包括:新闻报道、一两种宣传册、一些信件和日记(条目)、一份庭审记录、一封公开信,以及从杂七杂八的档案和口述中采集的信息。它们都过于笼统,不够具体,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是:“耆英号”的旅程不过是昙花一现,不具有什么历史价值。记录中的漏洞甚至比记录本身还多。用该书作者的话说,恰恰因为明显地缺乏证据,这艘帆船才具有启发意义。
该书从这艘船的建造到启航,在海上漫长的航行中的点滴,以及到最后被拆解的命运做了详细的梳理,譬如“耆英号”在纽约停留期间的故事,从每天到船上参观的人数和收入,到船员的诉讼,等等,都做了细致的分析,例如该船在纽约大约四个月时间,“其间一定有所盈利,因为有些报道称它每天有4000人参观,每人须交费0.25美元。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也在参观者之列,不过他对这艘船的看法未见报道。”“耆英号”抵达纽约后大概一个月,26名船员试图让他们的船长遵守他们所认为的合约内容。他们声称,船长没有付给他们钱,他们希望离开这艘船,按照约定讨回返程路费……在随后的法庭审判中,杰出的纽约律师丹尼尔·洛德免费代理七名水手出庭。介入案件之后,洛德逐渐意识到同时代水手的生活贫困,这些人需要救助,于是他找到了卫三畏,后者在中国做了十二年传教士,对中国足够了解……
纽约的庭审案件结束后,“耆英号”载着剩余的英国船员和不超过14名的中国船员启程前往波士顿。1847年11月18日该船抵达波士顿,并在此度过了入冬前和初冬季节的3个月时间。“令人惊讶的是,接下来它竟然离开了这个安全的冬季避风港,不可思议地在一年中最糟糕的季节出发前往英国,以完成自己的航程。”这艘船在伦敦的第一年无疑是引人注目的明星,上船参观的不仅有维多利亚女王、女王丈夫以及其他王室成员,还包括年迈的威灵顿公爵以及著名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不过,他是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参观“耆英号”的。
该书作者说:“耆英号”故事中最令人感伤的地方就在于对中国船员的情况了解是多么匮乏。他们为何签约受雇?出于绝望或好奇?出于对把头的忠诚?他们怎么看待这整场闹剧?在纽约离开的大多数人怎么看待留下来的少数人,后者又如何看待前者……阅读该书,这些中国船员在海上漫长的生活和他们的模糊面容确实令人伤感。
来源:浙江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