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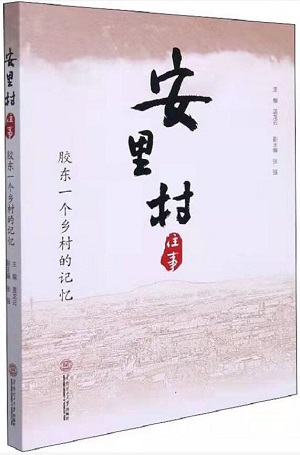
《安里村往事:胶东一个乡村的记忆》(订购)
盖龙云 主编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驴之名
1958年前后,农村成立了人民公社,每个生产队都有饲养场,饲养牛、马、毛驴、骡子等牲畜。它们都是劳动的好帮手,尤其是毛驴,往山上送肥、往家里运农作物、拉碌崮碾麦穗、拉磨等都离不开它,甚至小媳妇回娘家也要骑毛驴。
入社前,我们家养了一头毛驴,浑身毛色油黑锃亮,白肚皮、白嘴巴,双眼叠皮,大眼睛长睫毛“扑刹扑刹”的,我们都叫它“大黑”。人入社,驴也入社,大黑和其他各家各户的驴都牵到饲养场里。
大黑在我家时,住在西厢房里,大约10平方米,宽敞明亮干净。每天干活回来,爸爸就给它喂上饲草,加进麸皮等细料,大黑惬意地享受着单身“王老五”的幸福时光。
入社后大黑住“集体宿舍”,十几头驴全都拴在一长溜石槽头上,互相离得很近。吃食时,左边那个讨厌的驴小子,时不时地伸过它那三尺半长的脑袋来,抢吃好饲料;右边那个老驴家伙更可恶,经常用它那扁不拉塌的驴鼻子“打喷嚏”,鼻涕星子乱飞。
大黑也有自己的驴脾气,就是“尥蹄子”,凡有靠近它的,不论是人是驴,都“腾”地尥起蹄子一通乱踢,今天踢了人,明天又踢了驴,很快饲养员上门告状了。
饲养员是我的本家大哥盖洪宽,他找我奶奶“投诉”。
奶奶忍住笑,出主意:“孩子,你就不能使劲揍它一顿?”
洪宽哥说:“二奶奶,你不知道它的蹄子多有劲,再说它现在是集体驴,哪能随便揍?”
奶奶笑得不行,大声说:“哪天我去帮着你揍它。”我和妈妈也笑得不行。
奶奶又说:“宽儿这孩子真好,心眼实在。”
十几头驴集中在一个饲养室里,干活时一般由像我这样十几岁的学生牵出驴棚,赶驴上山。毛驴通常不是黑色,就是灰色,或者黑灰相间的颜色,大小也差不多,这样麻烦就来了——在分配学生拉驴上山干农活时,怎么办呢?起名字。
到我能赶驴上山送肥时,毛驴已经入社七八年了,队里的毛驴都有了自己的名字,构成格式是“某某某驴”,前面是驴入社前家主人的名字。
比如,我们家的大黑,因为我爸爸叫盖世华,就叫“盖世华驴”;盖任群家的驴,就叫“盖任群驴”。还有“盖中西驴”“盖洪国驴”“盖大群驴”等。
后来我发现,别人当着我的面说他去牵“盖世华驴”,我没有生气;队长当着盖大群家里人的面,安排人“赶着‘盖大群驴’去吧”,盖大群家人听见也没生气。
在山里地里劳动时,大家都这样毫无顾忌、大声喊叫“某某某驴”,“某某某”或其家人都从来没有当成骂人的话。不只是我们生产队的驴被这样“命名”,我赶驴上山送肥时,听见村里其他生产队也是这样叫。
我们赶驴上山送肥,或者是往回拉玉米秸秆。队长根据路程远近定下趟数,早完成,早收工。于是,抢到一头走路快捷、干活利索的好驴,是很重要的。这是我12岁后参加劳动时,小伙伴永红告诉我的秘诀:每天要早早去抢驴。可我总是抢不到,那些好驴都被别人抢走了,每天收工我总是落在最后。
麦收季节,有一天都大晌歪(方言,过了中午12点)了,我才完成上午的三趟送肥任务,等我赶着驴回来时,看到乳名叫“山”的小子(方言,男孩)已经吃完午饭,在饲养室门口等着抢驴了,好早早完成下午的送肥趟数。
他以胜利者的姿态看着我,我想想自己抢不到好驴,回回落后头、晚回家,心里不禁难过起来。难过有什么用?我暗暗发誓一定好好读书,一辈子决不送粪跟驴腚。
逮河蟹
玉岱河在瑶头村前拐个弯儿,向南流去。那些年雨水丰沛,玉岱河常年流水,碧波清清,河岸柳枝摇曳,芦苇茂盛,小河是鱼虾蟹蚌的乐园。姜疃粮所东面的位置,最适合下挂网逮河蟹。
那时候每年中秋节前后,爸爸都会去那里下一个挂网。“挂网”就是先在河的一边找一个位置,砸进一根木橛子,将网的一端挂在上面,再到河对岸也砸下一根木橛子,拴上渔网的另一端。网的底部有铅坠沉到河底,挂网横拦在水中。下挂网要在傍晚时分进行,下好网就回家。一夜过后,河蟹就会挂在网上,第二天要早早来收网。
有一年中秋节前几天,我爸照例又去下了挂网。第二天一早,爸爸就把我叫起来去捡河蟹。爸爸拿着大小油篓出了门,邻居盖中玉和我本家三哥盖洪棣,已经在场院西头等着一起去。爸说,这回需要三四个人。
一路上,我听他们边走边讨论下挂网逮河蟹的细节。他们说,昨晚咱们这里光打雷,没下雨,估计上游下雨了,河里一定会发水。还说,如果水太大,河水会冲下树枝等杂物戳破挂网。水太小,河蟹躲在洞里不挪窝,不出来网就挂不到。只有下不大不小的雨,发不大不小的水,才会有很多河蟹挂网,否则捡不到几个河蟹。
三哥有腿疾走不快,我俩落在后面十几步。爸爸和中玉先到,听见他俩高兴地惊呼连连,喊我“快跑快跑”。我连跑带蹦急急赶过去,爸爸和中玉已经下水提起了挂网。
我在岸上守着一个大油篓,三哥下到临近水面的地方,等待爸和中玉摘河蟹。昨天夜里上游确实下了雨,河里也发了水,都不算太大,三哥说这是老天赐福,天遂人愿。河水差不多到了爸的腰部,他和中玉弯着腰,打底下掀起挂网来,天哪!年年来挂网,这次收获最多,只见网上挂满了河蟹,一色的青皮、白肚、钢毛,大的有手掌那么大,小的也有鸡蛋大。
“发财了!发财了!”我和三哥开心地大叫起来。只见爸爸和中玉每人脖子上挂着一个小油篓,将挂在网上的河蟹一只只摘下来,他俩还一边说话——爸说:“怎么今年这些家伙和傻子一样,都跑出来撞网啊?”中玉说:“雨水合适了,敢保是急着到你家锅里去洗澡吧。”他俩开心地哈哈大笑。
一年级时洪棣三哥教过我,在学校我叫他老师,回家喊他三哥。他高兴之下,念叨了几句诗:“秋风起,蟹爬叉;菊花开,吃蟹来。”我问他这是不是《红楼梦》里的诗,三哥说是他自己编的;接着,他又念:“饕餮王孙应有酒,横行公子竟无肠”,说这才是《红楼梦》里写河蟹的诗。我虽听不大懂,但很佩服三哥肚子里有墨水。
爸爸和中玉把小油篓装满了,就从脖子上取下,转手交给守在河岸下边的三哥,三哥举过头顶,递给岸上的我。我便把小油篓里的河蟹,倒进大油篓里。这样重复三四回,大油篓很快装满了。河蟹们在油篓里你踩着我,我踏着你,拼命往上爬。我找根儿小树棍把它们一个一个捅下去,后来索性将一件旧衣服揉搓几下,塞住了大油篓的嘴儿。
回家后,爸爸将河蟹三家平分,大家都很高兴。这一年的中秋节,我们家的东西实在丰盛,姜疃食品站的猪肉五六毛钱一斤,爸爸割了半斤。地里采摘的豆角,有老的,有嫩的,妈妈包了带肉的豆角包子,每个包子两头塞两块肥肉。
我帮着妈妈好不容易把河蟹倒进大锅,妈妈开始烧火,风匣“鼓哒鼓哒”响着,灶底下柴草“噼里啪啦”燃着火苗,大锅终于烧开了。眼看那籽满肥美的大河蟹马上就能吃到嘴里了,哪承想,早晨回来后,我竟然受凉感冒发烧了,鼻子一闻(蟹味)竟然很反胃,白瞎好东西了。
整整一锅河蟹,直到第二天全家都没吃完。
本文节选自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安里村往事:胶东一个乡村的记忆》。
来源: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