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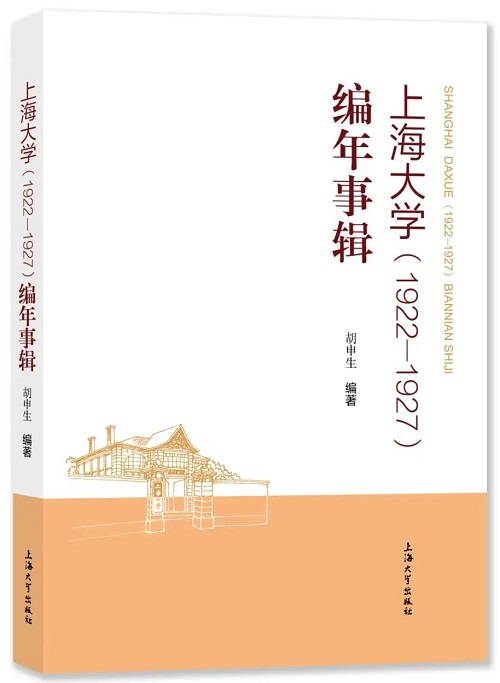
《上海大学(1922—1927)编年事辑》(订购)
胡申生 编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22年7月出版
大凡为人物立传,为团体、单位作史,其基础是详尽地搜集占有资料,再行排比梳理,在此基础上撰成年谱或辑成编年事,纵向叙年,横向辑事,冀使读者得以了解传主或为史团体、单位之全貌。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中说:“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岁月,以备后人之考证,而刊传前达文字,慎勿轻削题注与夫题跋评论之附见者,以使后人得而考镜焉。”(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章学诚这里讲“年谱之体”对于立传作史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976年以后,上海历史研究所方诗铭恢复《竹书纪年》的辑证工作,并得同所王修龄的大力帮助,撰成《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于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责任编辑为内子姜俊俊,我因得以了解这本书撰述、编辑、出版的全过程,并从中略窥散佚典籍搜集辨证之门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出版后,蒙方诗铭先生错爱,邀我协助他作《东观汉记》辑佚工作。几年中,在方诗铭先生的耳提面命下,遍访典籍,搜寻耙梳,认真抄录,辑成《东观汉记》佚文一册呈方诗铭先生。不料方先生尚未及作辑证工作,于2000年遽然西去,《东观汉记辑证》遂成方先生未竟之愿。然而,几年跟随方先生做辑佚“笨”工作,却使我从中学到了一些史料搜集校正的粗略功夫,懂得踏踏实实地做好史料基础工作对为史作传所具有的重要性。
2013年,上海大学建“溯园”,由我和党委宣传部的谢瑾撰《上海大学(1922—1927)大事记》。稿成以后,遂发愤撰《上海大学(1922—1927)编年事辑》。在学者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按年月逐日查寻辑事,于2018年9月撰成初稿,得十余万字。2020年编著出版之《从上海大学(1922—1927)走出来的英雄烈士》、2021年编著出版之《他们从上海大学(1922—1927)走进新中国》、2021年编注出版之《上海大学(1922—1927)师生诗文书信选》以及2022年所著之《上海大学(1922—1927)全史》,无不得益于《上海大学(1922—1927)编年事辑》稿本。
从2020年开始,上海大学推出“校史工程”计划,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在党委宣传部、文学院、档案馆、博物馆以及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陆续从全国各地(包括台湾地区)革命纪念馆、陈列馆、校友后人,以及俄罗斯等新搜集到许多珍贵的史料、资料和档案,于是,又对《上海大学(1922—1927)编年事辑》初稿作了修订补充。在此过程中,得上海大学档案馆副研究馆员洪佳惠襄助甚多,通过电话、微信沟通,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良有以也。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存世时间五年不到,先后两次遭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当局的武力封闭,档案遭毁散失,后又遇兵燹之祸,档案在运行途中罹难,现存档案不及原十分之一。有人编史,往往虑史料过多而愁精选之难,但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则每每有史料疏阔之叹。因此,凡事涉上海大学,即便细枝末节,均不忍弃去而编入书中。集腋成裘之念,还望读者体谅。
2022年是上海大学建校100周年。《上海大学(1922—1927)编年事辑》的出版,可对这所红色学府的了解和研究多一份资助。然而限于著者的视野与水平,难免会有疏漏舛错之处,还望读者多予指正和补充,不胜感谢。
本文为上海大学出版社《上海大学(1922—1927)编年事辑》自序。
来源: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