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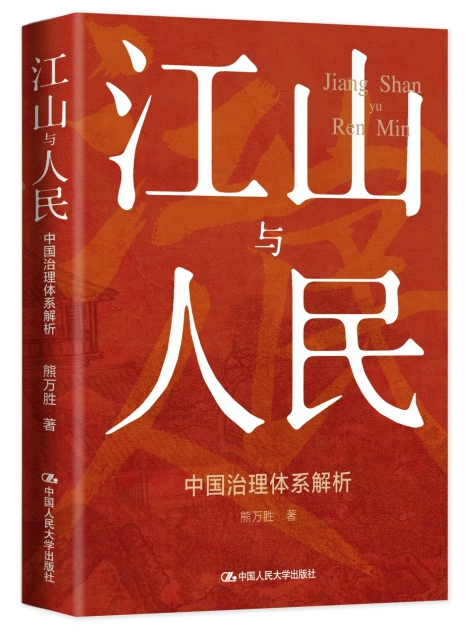
《江山与人民:中国治理体系解析》(订购)
熊万胜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年9月出版
精彩书摘
节选一
具象的社会
笔者想要提出的是另外一种理解中国社会特质的思路。这是一种关于中国社会如何被组织起来的研究,尤其是要在这个流行“脱钩”的时代,研究中国社会中的上下联结问题。这种研究是从一个人们都熟悉的经验事实开始的。
比如在中国的精准扶贫过程中,我们对于扶贫对象的了解是十分透彻的,从家庭地点、家庭人数、住房与周边环境、土地等资产、家庭的亲属关系网、邻里关系,到每个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身体状况、受教育程度、就业情况、实际收入等,几乎都要了解,虽然不一定都要记录在册,但要确保有人知道,因为所有这些对于精准扶贫的成效都有影响。
当国家如此了解群众的时候,群众就是具体的,或者说具象的。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依赖于和群众之间的人格化的日常联系。因此可以说,中国用这些日常联系替代了宏大的结构性互动,而替代的可行性来自独特的组织社会的方式。笔者把欧美的社会称为“抽象的社会”,而把采取这种依赖人格化的日常联系组织起来的社会称为“具象的社会”。
在如此巨大的中国社会中采取这种人格化的社会组织模式,必然要依靠一套复杂的结构,并依托独特的机制、丰富的资源和相应的文化才能实现。本书注重研究其中的结构,机制、资源和文化都作为理解这套结构的重要因素。这套结构可用一个现成的而且常见的词来表达,也就是“治理体系”。
对于治理体系,本书主要研究的是它整合社会尤其是联结上下的功能,研究以治理体系实现社会整合的条件和普遍性意义。
节选二
中国城市的反空间分异
在生活环境的治理中还有一个特殊的机制,这个机制具有典型的共享色彩。对于居住空间的安排,中国有一种有意识的空间混合的做法。
如果不加干涉,完全交给市场和社会去安排,人们居住的空间分布会和阶层或者其他社会结构统一起来,形成社会结构的空间化,这是“居住空间分异”概念涉及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有一种反空间分异的做法。这个做法的体现是,我们很少有大面积的别墅居住区,即使有别墅居住区,其中往往也有一些高层或多层房。这样会有三个层次的混合:(1)一个小区内可能是不同房型混合的;(2)居委会不一定按照小区来设置,会出现一居委会多小区或者一小区多居委会的情况;(3)街道是城市的重要社区单位,一条街上多种房型并存,不同阶层的人生活在同一个社区的情况是普遍的常态。
这未必是政府的有意安排,但肯定和政府的政策有关,可能是政府各种政策的一个复合性结果。比如和特定的房地产开发政策有关。政府会对容积率提出要求,限制低容积率,而开发商希望有更多的房子可以出售,就导致出现混合房型的小区。
而且,政府会明确地禁止发展太多的别墅居住区:一面开展拆迁工作,拆除农民自建房(这些房子可以说也是自建的“别墅”);一面建别墅出售给富人。这肯定存在价值观风险。更直接的理由是要保护耕地,减少对农民土地的征占。
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城市的市中心的房价高于郊区。在市中心开发高档商品房,只能是小规模的,因为动拆迁的成本太高,而且利益关系复杂,难以建成大社区。这也导致了同一居委会或街道内部的房子高低搭配。这种越是市中心社区房价越高的现象,与政府的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向市中心倾斜有关。结果是富有的人和穷邻居共享学校、医院、超市和街角的公园等。
节选三
如何搞好青少年的教化
青少年的教育问题近期受到决策层空前的重视,一系列的政策随之出台。如何为青少年减轻学习负担成为一个重点。减轻学习负担不是目的,他们能够成才才是目的。或者说,负担可以减,担当却不能减。从减负担不减担当的角度来看问题,仅仅减负是不够的。
青少年的负担不仅过重,而且结构不合理,即:学习负担太重,对于家庭、亲友和社区的负担太轻。这就好像是想要敲打出一只金碗,总在一边敲打只会把碗敲破,必须周遍地敲打才能敲打出一只可以载物的金碗。这个道理,一般的家长也懂,可是做不到。如果没有社会教化的支撑,私人的教化是很难成功的。
年轻人能不能成才、能不能结婚、结婚以后能不能生孩子,这在传统社会都是非常私人化的问题。传统的国家投入巨大的精力推行社会教化,制定出明确具体的行为规范,以千年为时间尺度,持续不断地向社会各界宣导。今天,这些问题的公共性已经非常明显,但是要搞好教化却不容易。
要搞好新时代的教化,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要在推进政治教化的同时,发展与政治教化相融合的生活教化。也就是以人的生活为中心来确定教化的内容,研究健康心理与良好生活方式的生成规律。第二,要科学地、长期地和谨慎地研究生活教化的内容,因为这是在教人如何过上幸福的人生,不能出差错。第三,要认真地研究教化的规律,总结既有教化的经验和教训。要实行有效的教化,必须把工作落到实处,认真研究它的规律。今天,我们在教化上的投入也很大,但效果不能令人满意,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充分消化吸收传统教化的有益经验。第四,要推动基层社会的组织建设。这也是宋代以来的经验。教化以组织为中介,只有在特定的组织中按照教化行动的人才可能得到激励,得到激励的行为才可能不断地重复和固化。
节选四
内需型经济与国家自主性
回过头来看,内需性经济形态一直是中国经济形态的主流。
中国作为一种大陆文明,一直依赖农耕经济。这是天然的内需性经济,与地中海地区和阿拉伯地区对商业的依赖迥然不同。这种自然而然的内需性经济体系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中国的物产确实丰饶,很少有物产是必须进口的,且有大量的物产可以出口。中国在最适合传统种植业发展的北纬30度附近拥有广袤而完整的国土,而在欧洲,这片区域被地中海所占据,是一片汪洋大海。在阿拉伯地区,这片区域又布满了荒漠。在传统时代,中国成为世界上天然的进出口贸易出超国。
另外,这种内需为主的经济形态也是王朝的自主选择。明朝作为对外部世界最有感觉的王朝之一,主动地选择了贸易上的闭关锁国,这种政策在清代得到延续。闭关锁国主要的用意不是通过降低外贸依存度来降低经济风险,而是历来的重农抑商政策的一个国际化版本。这是简化经济系统和社会结构的一种措施,通过降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尤其是要减少中间势力发育的空间。
晚清以来,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格局中被迫开放让中国社会承受了巨大的代价。革命后的中国在尝试了高度封闭的计划经济体系之后,证明仅靠自身的经济体系不足以富国强民,于是重新加入世界经济大循环,这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现在,我们被迫地也是顺其自然地回归到内需性经济模式中,此时我们是在开放的环境中依靠新业态,采取市场经济的体制来重建内需性经济体系。
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是更加依靠内需还是更加依靠外贸,对于治理模式是有深刻影响的。减少对外依赖有助于经济体系的安全。其中还有一个区分:国家自主性更强的国家如果同时也是内需性经济体系,它的国家自主性会得到进一步的增强,这样的国家与体系化的治理模式是相适应的。
美国、日本和欧盟虽然对外贸的依存度低,但是它们依然通过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优越位置赚钱,如此一来,资本体系和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就会出现分离,其效果和外贸依存度高的国家是类似的。在发展中国家的内需性经济中,国家不仅可以掌握经济命脉,还能独立地塑造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而不是把这个权力让渡给国际资本巨头。这样会形成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经合一关系,为更强的国家自主性创造条件,进而为体系化治理打下基础。
节选五
治理性团结
在福山看来,从社会性团结向政治性团结的发展是一种进步。一旦政治性团结依托的非人格性制度失败了,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的原则就会卷土重来,导致政治衰败。或者说,在国内政治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原则性和灵活性之间基本是不可调和的关系,不能把法治变成外交谈判。
福山非常强调制度化对于政治发展的意义,他所定义的政治衰败的两种形式都体现在反制度化上:一种是制度脱离实际,一种是家族制卷土重来。他不能设想有一种混合的状态可以让原则性和灵活性更好地结合起来,让非人格性的制度和人格化的联结能够统一起来,而这恰恰是中国的治理体系正在做的事情。对于制度化的强调并不是福山的独创,而是政治学的一般看法。而中国的治理体系对于主流的政治发展理论是一个挑战。
中国的治理体系能够包容人格性的因素,使一种高度现代化的国家制度建立在人的具体性上,形成一个可以“通人”的国家。这种人格化的因素不仅在面对百姓的时候起作用,在正式组织内部也会起作用,因为一个人总是同时具有一般性和具体性。中国的治理体系就是在这种张力下运行的。
如果人格性的因素太多,上下级之间和干群之间就会形成封建性的庇护关系;如果人格性的因素太少,部门之间和干部之间的沟通协调就会出问题,干群之间的人格化联系也会生疏。因此,有的时候对一般性强调得多一些,有的时候对良好的人际关系强调得多一些。
目前的趋势是:对干部的一般性角色强调得越来越多,同时,对于干群之间的人格化联系的衰微又试图挽救。结果,中国的治理体系总是处于一种既有制度性又有人格性的状态。中国的治理体系通过体系化的联结机制将社会的各方主体都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种十分不同的社会团结形式。
我们可以将这种通过体系化的联结机制形成的社会团结形式称为“治理性团结”,以与社会性团结和政治性团结相并列。
以上内容节选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江山与人民:中国治理体系解析》。
相关内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江山与人民:中国治理体系解析》出版,曹锦清、潘维、贺雪峰力荐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