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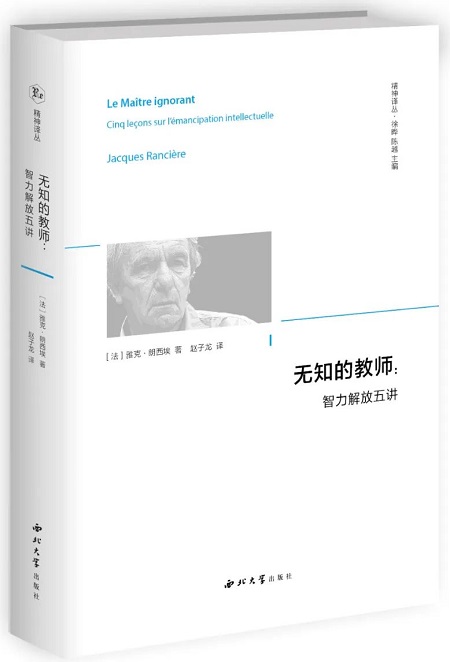
《无知的教师:智力解放五讲》(订购)
雅克·朗西埃 著
赵子龙 译
西北大学出版社
偶然与意志
受讲解人长成讲解人,一切周而复始。作为教员的雅科托本来也在其中,但一次偶然,将一个事实带到了他面前。而他一直认为,一切推理都要基于事实、服从事实。不过,我们不能因此把他看作唯物主义者。相反,就像提出散步足够证实何为运动的笛卡尔,或者像同时代的保皇派和信教者曼恩•德•比朗,他也认为,来自那活跃的、能够省察自身活动的精神中的各种事实,要比任何实质的物更为可靠。
雅科托正是这样来看的:发生了的事实是,那些学生不靠他做任何讲解,自己学会了法语读写。他没有向他们传授自己的学问,没有向他们讲解那些法语的词根和词形变化。他也没有像当时某些教育改革家那样效仿《爱弥尔》中的家庭教师,让学生误入歧途再加以指导,或是巧设路障迫使学生学会如何自行跨越。雅科托让学生们只依靠自己,让他们只能凭借费奈隆的文字,一版甚至并非教科书的逐行译本,还有他们想学法语的意志。他只告诉学生们去穿越一片无路可寻的森林。这个要求让他完全无法投入自己的智力,即教师充当中介的智力,无法用它去联结文字印迹中的智力和学徒的智力。而这样一来,他也消除了那空设的距离,即钝化教育的原则。
这时,一切都只能发生在三者的智力之间:费奈隆,他曾意愿将法语作某种用途;翻译者,他曾意愿译出一版荷兰语的对应;学生们,他们意愿学习法语。而这里似乎也不需要其他的智力了。雅科托之前没有意识到,但让学生们、跟学生们一道发现:所有的句子,以及写出句子的所有智力,本来都只有一种。
所谓理解,始终不过是翻译,是给出一篇文字的对应,而毫不直呈其后的理性。书页背后并没有什么,没有更深层次要求其他智力、那讲解人的智力来做什么;这里也不要求教师的语言、语言之语言,因为人不是要用那种字句才能讲出某篇文字的字句中的理性。这些荷兰学生出示了证据:他们用来评议《帖雷马科》的资源,只有这本书里的词。
所以说,仅凭费奈隆的字句,人就足以理解他的字句、讲出自己对他的理解。学习和理解,是用两种方式来形容同样的翻译活动。如果说文字之中有什么,那不过是作者的自我表达的意志,也就是翻译的意志。学生们通过学习费奈隆的书理解了一门语言,靠的不仅是比照两页对开内容的行为操练。
这里的关键,不是人靠天分就能切换两栏内容,而是人有能力用别人的词讲出自己所想。学生们跟费奈隆学到了这些,是因为作家费奈隆所做的本来就是一种翻译者的活动:他为了把政治教诲翻译成传说故事,用他那个世纪的法语转译了荷马的希腊语、维吉尔的拉丁语,以及成百篇童话故事和广博史书中那纯朴或精妙的语言。他在这两重翻译中所用的智力与那些学生们相同,因为后者也运用了这种智力,借他书中的字句讲述了他们自己对这本书的看法。而且,这种智力不仅让学生们学会了《帖雷马科》的法语,也曾经让他们学会了母语:他们用它去观察和记忆、复述和检验,去将要认识的联系到已经认识的,去做然后省察自己所做。他们像在不该去时出发了,像孩子一样走上前去,盲目探索,去做猜谜。
而问题正在于此:这样一来,我们岂不是需要推翻人们对智力价值公认的秩序?猜谜这种不受尊重的方法,难道就是人的智力取得本身力量的真正运动?而摈弃这种方法的人,不就是只想把知性的世界一分为二?那些方法论者反对这种基于偶然的不良方法,主张靠理性去行进,但他们是为早已认定的事情作证。
他们已经设定了一个幼小动物在探索中跌跌撞撞,因为他还看不清世界,而他们正好去教他认清这个世界。然而人的幼子首先是一个言说的存在。当孩子将听到的词复述出来,当荷兰的学生们“迷失”在《帖雷马科》里,他们都不是在偶然中前行。他们的努力、他们的探索都是为了走向这里:有人向他们发出一段言说,而他们想辨认并回应它,他们这样做,并非作为学生或学者,而是作为人;他们像要回应一个来对自己谈话的人,而非一个来对自己进行考试的人:这里的名义是平等。
事实正是如此:学生们是靠自己学习,不需要教师做讲解。
而且发生过一次的事总有可能再发生。尽管对于作为教员的雅科托,这个发现或许推翻了他的原则,但他作为人,更想了解人的多种可能性。他的父亲本来是屠户,后去经营他外祖父的木匠生意,而外祖父将他送去中学读书。雅科托曾担任修辞学教员,随后在1792年响应动员而入伍。他由战友选为炮兵上尉,作为炮手表现突出。1793年,这位通晓拉丁语的学者去火药司担任化学教官,对工人进行速成培训,送他们到领土的各个角落去施展富克鲁瓦的各种发现。同样是通过富克鲁瓦,他结识了沃克兰,而后者本是农家子弟,曾经瞒着雇主自学化学。
后来雅科托来到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见到了临时委员会依据心智活力与爱国精神两条标准选拔出的年轻学生。他见证了他们成为出色的数学人才,但这不是靠蒙日和拉格朗日为他们讲解数学,而是靠数学家们在他们面前的演练。雅科托显然在管理校内行政期间有所收获,得到了数学家的技能,后在第戎大学得以发挥。同样,他在所教的古代语言课上加入希伯来语,因此后来写了一篇《漫谈希伯来语语法》。不知为何,他认为这门语言很有前景。他最后收获一项技能,本非所愿却义不容辞地出任了民众的代言人。
总之他知道,众多个人的意志和国家面临的危难可以催生未有的新能力,因为某些迫切状况需要废弃基于讲解的逐步进展。他认为,国家的需要可以造成这种例外状态,而孩子探索世时、学者和发明家开辟独特路径时,他们的迫切需要如出一辙。
偶然的方法已经体现在孩童、学者、革新者的经验里,但在荷兰学生的成功实践下又现出了第二层秘密。这种平等的方法,首先是一种源于意志的方法。只要人有这样的意愿,以自身的渴求为动力或受形势所迫,他就可以自己学习,不需要教师做讲解。
使人解放的教师
在雅科托的实验中,他对学生们的指示就是这样的迫使。而它收效甚巨,不仅是对学生而言,也对这位教师而言。学生们不靠教师做讲解而学习,但并非完全不靠教师。他们之前不知道的东西,现在他们知道了,所以雅科托仍然教了他们些什么。而他没有向学生传授自己的学问,所以学生所学的,并不是教师的学问。
雅科托是教师,就在于他的指令将学生们限制在一个循环里,让他们靠自己走出去,同时他不投入自己的智力,只让学生们的智力去对抗书中的智力。这样就拆开了教师讲解人所合并的两项功能,即学者的功能和教师的功能。同时,这样也拆开了学习活动所涉及的两项机能,即智力与意志,让它们相对彼此形成自由的关系。教师和学生之间成立了一种纯粹的意志对意志的关系:教师的支配,造成了学生的智力与书的智力之间完全自由的联系。而书的智力,就是那共通之物,让教师和学生形成了平等的知性关联。这件装置,可以厘清教育活动中混杂的各范畴,并确切定义讲解人所做的钝化。
所谓钝化,就是让某个智力从属于另一个智力。人,尤其是儿童,有时难免需要教师,因为他的意志还无力将他带上自己的道路并引导自我。这种从属关系可以单纯地存在于意志对意志间。而这种从属关系一旦将一个智力缚于另一个智力,就造成了钝化。
在教和学的活动中,存在两个意志、两个智力。它们的重合就是钝化。在雅科托所设的实验中,学生系于一个意志即雅科托的意志,并系于一个智力即书的智力,而这两者完全区别开来。我们所说的解放,就是指人认识到并保持这两层关系的不同,就是一个人在他的智力只服从自身、不论他的意志是否服从另一个意志时的活动。
因此,这场教学实验切断了诸种教育学的逻辑。教育者们的实践本来建立于学问与无知的对立。他们之间的差别,仅在于他们选用不同方式让无知者得到学问:这些方法或困难或轻松,或传统或现代,或被动或主动,收效各有不同。依此看来,人们或许可以先作比较,认为雅科托的学生的高效优于传统方法的低效。
但事实上,我们根本不用这样去比较。将不同方法对比,就是承认教学活动的各种目的具有最基本的一致:将教师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但雅科托本来就无所传授,他也没有采用任何方法。其中的方法纯粹是学生的方法。而且法语学得是快是慢,这是无足轻重的。我们要比较的,不是各种方法,而是两种智力的用法、两种知性秩序的观念。那高效之路,并不是某种更佳教育法的道路。
它是另一种路,是自由之路。这条路,雅科托在共和二年参军时、在生产火药时、在创办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时,都曾付诸实验:这条自由之路,可以应对他在紧要时刻的急需,而它也是信任之路,是去相信任何人的知性能力。在教学所建立的无知与学问的对立关系中,我们需要看到在钝化与解放之间更为根本的哲学关系。这里涉及的关键词不止两个,而有四个。这四项决定因素的不同组合,决定了学习活动由谁主持:或是解放的教师,或是钝化的教师;或是有知的教师,或是无知的教师。
最后的一种,应该最难得到认可。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一个有知者不想讲解自己的学问,但怎么能接受一个无知者成为另一个无知者的学问来源?雅科托的实验本身也不够明晰,因为他毕竟有法语教员的资历。
不过,实验至少证明了教师没有用自己的知识去让学生学习,这说明教师可以去教自身知识之外的内容,去教自己所不知的内容。于是雅科托设法进行多种实验,有意地复制那源于偶然的单次成果。
他着手去教两个他不具相关技能的科目:绘画与钢琴。法律专业的学生们本想请他接任系里的空缺教席,但鲁汶大学校方已经有些看不惯这名古怪的外教,因为学生们因他而不去听各门主讲课,在晚上挤在一间小教室里,在两支蜡烛的微弱光亮下,听他讲道:“我必须教给你们的事情就是,我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教给你们。”学校主管考查后表示,雅科托没有任何名义担任这个教席。但恰好,雅科托正想要在实验中发现名义和实际活动之间的偏差,所以他没有用法语去讲授法律课,而是教学生们用荷兰语作辩护。尽管雅科托始终不懂荷兰语,但学生们的辩护大有长进。
力量的循环
雅科托似乎从实验中得到了足够的启示:人可以去教自己所不知的,这仅仅需要他解放学生,也就是迫使学生运用自己的智力。教师要做的,就是将一个智力限制在一个任意的循环里,让它只有靠自己才能走出去。要解放一个无知者,只要并且只有先解放自己,这就是意识到人的心智的真正力量。无知者能靠自己学到教师所不知的,只要教师相信他能做到、并迫使他实现他的能力:这里有一个力量的循环。而无力的循环与此相对,它将学生缚于旧方法中的讲解人(此后我们就叫他旧教师)。而这两种势力各有特点。
无力的循环总是已经存在,它是社会人群的本来路径,因为他们已经耳濡目染了无知与学问的明显区别。而力量的循环若要有效,只能靠推广。不过它的出现,就像一种自我重复、一种不经之谈。富有学识的教师,怎么会理解他可以把自己不知之事教得像自己所知的一样好?他不会承认他的知性力量因此增加了,只会认为他的学问贬值了。而另一方面,无知者难以相信他可以靠自己学习,更难去相信他可以教育另一个无知者。那些被智力群体排斥在外的人,本身已经听从了排斥他们的定论。总之,解放的循环必须被开启。
矛盾正在于此。我们略作思考就会发现,雅科托所提出的“方法”正是所有方法中最古老的,因为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某个人需要获取某种知识而又没有办法得到讲解,这种方法就不断得到检验。世界上没有谁不曾只靠自己学习过,同时没有教师作讲解。
我们可以把这种学习方式叫作“普遍教育法”,并这样肯定它:“自从世界起始以来,普遍教育法就真正存在,共存于各种基于讲解的方法。这种教育法,靠它自身,真正地培养了所有伟大的人。”但奇怪的是:“任何人在生活中都有千百次这种经验,然而从来没有谁想到去告诉别人:我不用讲解就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认为你也能像我这样做。……我和世上的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去用它教育别人。”而对每个人半睡半醒的智力,我们只需要说的是:“做自己的事”,继续去做你所做的事,去“学习事实、模仿它、认识你自己,这是自然的路径”。你只需要去有序地重复那偶然的方法,靠它测定你的力量。人类心智的所有活动中运作的是同样的智力。
但这里需要迈出最难的一步。每个人都应需采用这种方法,但都不愿承认它,不愿应对它所蕴含的知性革命。是社会的循环和事物的秩序让人们无法承认它的本质:它是每个人真正的学习方法,可以让每个人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我们要敢于承认它,敢于让它的力量接受开放的检验。不然,那无力的方法和旧教师就会和事物的秩序一样存在下去。
谁先来开始?那个时代不乏各种人,出于好意地关心民众教育:守护秩序的人想要教化民众,改掉他们的粗暴脾性,而革命者想让民众意识到自身权利;进步论者想通过教育,填平阶级间的鸿沟;实业家则期待通过教育,让民间最优秀的智力去推动社会发展。所有这些良好意愿,都遇到一个障碍:平民之众并没有什么时间、更没有什么钱去得到这些收获。
还有人尝试更易行的方案,根据不同案例,去推广最基本的教育,认为这样才能有效地扶助劳动人民。进步论者和企业家都推崇的一种方法,是互助教育法。它是在一个大型场地内召集一大批学徒,分成小班,让每班进步最快的人负责管理,担任班长。这样,教师的指示与课程就经过班长的中介,散播给所有需要教育的民众。这番景象让进步论支持者很满意:这样就让学问从顶峰一直传到最低微的众多智力之间。随后,幸福和自由也将下传给他们。
对于雅科托,这种进步却像套上缰绳。他说这是更完善的马术。他所期望的互助教育,是另一种情况:每个无知者都可以去做另一个无知者的教师,将他的知性力量揭示给他自己。
更确切地讲,雅科托关心的并不是如何教育民众:那些人所教育的人,只是打起旗号招来的新兵,是必须能够理解指示的下属,是他们所想统治的民众,而这种统治,当然是用进步的方式,不再假借神权,而仅依据人们能力的层级。
但雅科托所关心的,是解放,即所有人都能建立作为人的尊严、认识自身的知性能力并决定其用处。而那些“教育”推行者相信,教育是真正自由的必备条件。于是他们赋予自己教育民众的义务,却又争执不下应该给予哪种教育。而雅科托并不去想教育者该给民众带来怎样的自由,相反,他从中看到一种新式的钝化。不解放地教,就造成钝化。而解放者不会考虑被解放者该学什么。他可以学到任何想学的,也可能学不到什么。但他知道他可以学习,因为一切的人类技艺产品中运作着同一种智力:一个人总能够理解另一个人的言说。
雅科托的印刷商有一个迟钝的儿子,屡教无果,已让家人绝望。雅科托教他学会希伯来语,后来,这个孩子成了一个优秀的平版印刷工。他学了希伯来语,当然从来不会用到,但这让他知道了那些更有天分、更受教育的智力始终不知的事:希伯来语不会难如天书。
因此我们就清楚了:雅科托不是提出一种教育民众的方法而是要向穷人宣告一种恩惠:他们可以做到任何人能做到的事。宣告,就已经足够。雅科托决定全心投入此事。他宣称,人可以去教己所不知,而一家之父,即使贫穷而无知,但他只要解放自己,就可以教育他的孩子,不需任何教师讲解人的帮助。他指出了如何去实行这种普遍教育法:先学某件事,再将它联系到其余一切,并依从这条原则:所有人都有同等的智力。
在鲁汶、在布鲁塞尔、在海牙,人们为之震动;有人从巴黎、从里昂坐马车来参访;有人从英格兰、从普鲁士来见证新闻;人们把它传到了圣彼得堡、传到了新奥尔良。它的声音一直传播到里约热内卢。一场论战持续了数个年头,让知识共和国的根基为之震颤。
所有这些,都是源于一个有心智的人、知名的学者、美德的父亲成了一个痴妄之人,只因他不懂荷兰语。
本文摘自西北大学出版社《无知的教师:智力解放五讲》。
来源:西北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