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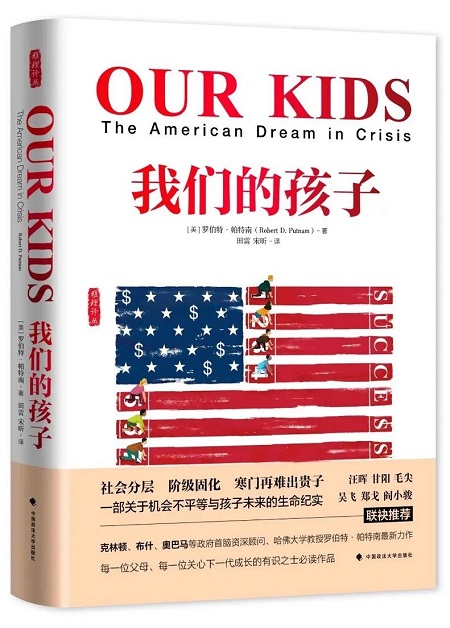
《我们的孩子》(订购)
[美] 罗伯特·D.帕特南 著
田雷、宋昕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学校:你的同学是谁,这很重要(二)
姑且不论孩子自己的家庭背景,如果把孩子送到身边同学来自上层阶级家庭的学校,孩子就能有更优秀的学业表现。在整个发达世界,这种“近朱者赤”的模式看起来是普适的。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以严谨的数据证明了这一不容置否的现实,他在自己开创性的研究中就写道:“不论学生自己的社会背景如何,最大程度上决定学生成就的学校因素是学生群体的社会组成,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学校因素。”上述一般性的命题,不仅适用于在校考试分数、毕业、大学入学这类学术成绩,而且即便我们维持学生自己的家庭背景和在校成绩这一变量不变,同学的社会构成也会影响到学生在成年后的经济收入。
在富人学校读书,穷孩子就能取得更好的成绩,这一现象被加里·奥菲尔德(Gary Orfield)和苏珊·伊顿(Susan Eaton)称为“教育研究中的铁律”。事实上,已有很多研究显示,学生在高中时的学业表现与其同学家庭背景之间表现出很强的正相关,其程度要高于与其自己家庭背景的相关性。
让我们做如下的思维试验:假设索菲亚(“生性聪慧”,小小年纪就喜欢读字典)幸运地转入了特洛伊高中;与此同时,伊莎贝拉却不幸地转入了圣安娜高中。一旦两个女孩互换学校,她们各自的学业成绩很难不受影响。不要忘记,克莱拉和里卡多之所以从洛杉矶的旧居搬到了富勒顿,恰恰就是因为预见到了这一幕。但是,为什么同学的社会经济背景如此重要?为什么学生群体的阶级构成会对一个学校的学生产生如此强有力的影响呢?
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百姓,相当一部分人首先想到的答案就是:学校的财力。也就是说,学校的预算主要取自于本地的财产税,所以富人区的学校就可以承担起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教师、行政管理者、课程项目和校舍设施。但其实不然,学校财力并非美国阶级鸿沟不断扩张的主要推手。例如,大多数研究者现已发现,学校财政(包括学生人头开支、教师薪酬)并非预判学校质量的主要指标。不仅如此,过去三十年以来,虽然阶级差距渐成两极分化,但在美国许多州内,地方财产税收在公立学校的预算中占据的比例越来越小,这部分要归因于这些州的司法判决,根据相关的判例,一州之内各学区之间的政府开支必须保证平等。
至于薪酬,同等条件下,富人区学校的教师只是略高于普通学校,但这一状况也可以告诉我们,年资更深的老师之所以会逃离那些以穷学生、少数族裔学生为主的学校,往往并非出于金钱的原因。而且,在那些穷孩子更多的学校里,师生比例这一指标如果有不同,通常也是会更高一些。在这一方面,表格4-1通过对特洛伊和圣安娜两所中学的对比,实际上准确地反映出了全国范围内的模式:不同学校之间学生成绩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就这一结果而言,政府配置的资源因素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当然,假如穷孩子的学校可以开得出更高的薪水,雇用到更多、更好的老师,那么这也不失为一种缩小阶级差距的好方法。但问题是,这类学校的教师和管理人员通常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学生视纪律为无物、不会讲英语、学习基础太差,以及学生从校外带进来的各种问题,无一不在圣安娜中学上演着。由于问题实在是积重难返,所以如果真的要拉平孩子们的竞争场域,则政府现有的财政投资绝对是不够的。但归根到底,我们现在确实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穷人学校和富人学校之间的成绩分化要归因于公共资源分配的偏差。
由是观之,更合理的解释是学生这个群体从校外带入学校内的种种资源和习气:家庭对学习的鼓励、“课外活动”的私人捐赠,这些积极因素可以造就良好的氛围;反之,犯罪、吸毒和社会混乱,这些消极因素也会导致学习环境的恶化。读罢前文对特洛伊和圣安娜两所学校的对比,首先映入眼帘的也正是上述种种因素吧。你的同学是谁?你和哪些人一起上学?这是大问题。
首先,学生如果来自于富裕、高知的家庭,则他们也会把父母作为资源带入所就读的学校。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可以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则越有可能亲身参与到孩子的学校事务。我们前面的故事完美地阐释了这一现实。“一周下来,我们对孩子们的督促也许超过了我父母在高中四年对我们的督促,”本德镇的厄尔曾如是说;无论在新泽西,还是在亚特兰大,西蒙娜从来都是家庭教师协会的负责人;克莱拉不仅亲自走进了孩子的课堂,还结识了学校办公室的行政人员。当然,那些经济拮据的父母同样也想要参与孩子的学校事务,但他们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我们的故事中,束缚他们的因素包括工作职责(比如居住在亚特兰大的斯特芬妮)、文化观念(比如在圣安娜的罗拉的外祖父),或者自身的受教育程度(比如本德镇的乔)。大多数情况下,父母参与之所以出现阶级分化,主要原因并不是贫穷家长没有主观意愿,而要归因于经济和文化的制约,当然罗拉的外祖父确实也指出,近年来经济状况一般或困难的父母确实变得更漠然。无论如何,较之于低收入地区的学校,富人区的学校总是存在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学生家长更大程度的参与和支持。
这一现实会造成一连串的后果。许多研究已经显示,父母参与,小到检查家庭作业,大到参加家庭教师协会的会面,的确会有助于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培养人际交往的能力,同时可以大大降低孩子酗酒或沾染毒品的概率。教育学学者安妮·亨德森(Anne Henderson)和南希·柏拉(Nancy Berla)在对此类研究进行文献综述时曾写道:“当父母投身于学校事务时,孩子的在校表现会更上一层楼,而他们就读的学校也能有更好的发展。”
当然,要从相关性推演到确定的因果关联,这一步殊非易事。那些经常造访学校的父母,往往也就是那些为摇篮里的孩子读书的父母。这样看来,起作用的到底是什么?是在孩子们上学后参与学校事务,还是为幼年的子女在睡前读书?抑或说,其中的因果链条也有可能是反过来的:学生的在校表现为因,家长的参与才是果?(既然知道老师对自己的孩子会赞誉有加,那么造访学校当然就是一件快乐的事,何乐而不为呢?)没有可由研究者控制的实验,有关因果性的问题实在难有定论,但即便如此,大多数研究者目前都相信,父母参与学校事务有助于孩子在校的学习表现,对出身社会经济下层的青少年来说,关联尤其显著。
其次,有钱人家的孩子还能把家长的财富带到学校。我们都知道,上流社会学校的筹款能力是中下阶层学校望尘莫及的,因此同样是“校外捐赠基金”这一预算,两类学校不可同日而语。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见,有了这笔资金,特洛伊高中就可以开办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远非圣安娜中学能及。更有甚者,在纽约市曼哈顿的上西区,多家公立学校的家长教师协会每年可以筹款100万美元,用以支持学校的各种活动,这些学校因此被称为“公立中的私学”;而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希尔斯伯勒,家长筹款基金会每年都能拿出345万美元,这数目已经占据了学校预算总盘子的17%。迄今为止,我们尚且没有记录家长筹款模式的全国性数据,但随处可见的个案已经令人触目惊心。
不仅如此,上流社会的父母还要求学校开设在学术上更严格的课程体系,这当然又会培养出更优秀的学生,不仅高中退学率微乎其微,入读大学的学生人数也越来越多。图4-1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对美国大部分公立高中的普查。在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以家长的经济收入为基本指标,区分出排在一头一尾的两类学校:前一类是富家子弟为主的高中,它们提供的大学预科课程的平均门数为12门,而后一类则是穷孩子扎堆儿的高中,它们的大学预科课程仅为4门。于是我们又一次看到,圣安娜和特洛伊两所中学的对立反映出整个美国的撕裂:特洛伊高中的所有孩子都是书呆子,克莱拉这样告诉我们;而当我们同索菲亚谈及圣安娜的学习环境时,她唯有报以冷笑:“学习氛围是神马?”
再次,同辈压力,特别是同学之间的压力,也是促成优异学业表现的重要推手。同辈压力通常在一个人15岁到18岁时达到最高点。研究表明,这种压力一方面表现为“近朱者赤”,好的榜样可以激励青少年的学习成绩、兴趣和志愿;但另一方面也有“近墨者黑”的效应,坏的示范也会导致青少年吸毒、旷课、抑郁以及行为不端,甚至养成不健康的消费观。因为同辈人之间会传递社会规范、教育理念,甚至是学习技巧,所以只要进入了特洛伊这样的中学,同学彼此之间都会成为学习的催化剂。自强不息在青少年中间是可以相互感染的,反之,迷惘堕落也会相互传染。同辈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存在于学校之阶级结构和学生表现之间的关联。
如果这样说,那么有钱人家的孩子为何会有高标准和严要求呢?换言之,这最初的压力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伊莎贝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回答——父母。“我的父母并没有给我施加太大的压力,但很多同学却被家里予以厚望……我的同学们要是在考试中没有发挥好,那些可怜的孩子都不敢回家,因为他们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一顿训斥,父母会劈头问道:‘成绩单呢?拿来给我看看。这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次没考好?’”
学生家长大都是“虎妈”,在这样的学校里,同辈压力就主要表现为伊莎贝拉及其同学所体验的“压力”和“竞争”;相应地,父母寄托在孩子身上的期待在学校内也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学生因此都有力争上游的动力。相反,若是在圣安娜这样的学校,即便一个学生在进入学校时满怀家长的期待,但也难以摆脱恶性的学习环境,往往满腔热情就被一下子浇灭了。
所以说,总体看来,那些成长在富裕家庭和社区的孩子,带到校园里的通常是正能量,会在同学之间营造出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反过来说,生活在贫民窟的穷孩子往往会在学校制造暴力和混乱,而这些负能量会危害到这些学校的所有学生。这就是我们在圣安娜中学看到的可悲局面,学生在课堂上一言不合就要动手,讲台上的老师也无能为力,能维持学校的秩序已属万幸。
本文节选自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我们的孩子》。
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