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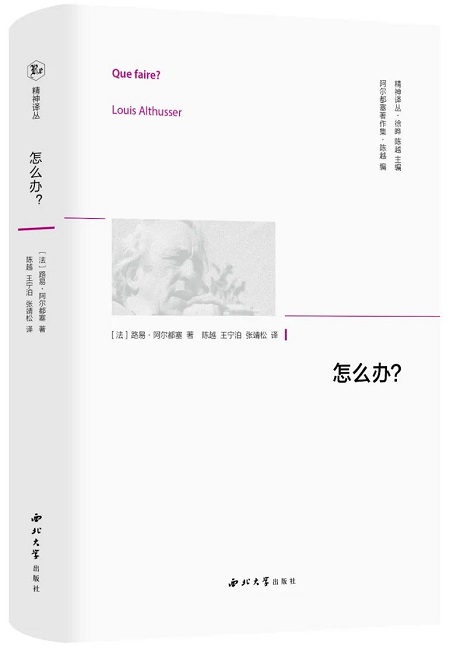
《怎么办?》(订购)
[法] 路易·阿尔都塞 著
陈越 王宁泊 张靖松 译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23年12月出版
通向“具体分析”的道路:
从《怎么办?》重新认识阿尔都塞
——《怎么办?》译后记(上)
文 | 陈越
《怎么办?》这部著作有一种难以说明的性质。最近十年,新的一批阿尔都塞遗稿经G.M.戈什加林(G.M.Goshgarian)先生整理编辑,由法国大学出版社(PUF)出版,迄今刊行6种,其中5部,均由编者本人或邀请其他学者撰写长篇介绍或序言,唯独本书,只有寥寥数语的“编者说明”——这一点未始与它的难以说明的性质无关。
一
本书写于1978年。1977年3月,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三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马德里会晤,正式打出“欧洲共产主义”的旗号,阿尔都塞从这种改弦易辙底下看到了“危机”的征兆。实际上,从1976年2月法共二十二大以来,甚至从这一年1月7日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接受电台采访时扬言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开始,法共的新路线就已昭然若揭,阿尔都塞对这一路线的批评也就一发而不可收。
1976年4月23日,他在法共组织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图书周”活动上,趁介绍自己新书《立场》的机会,首次对法共领导层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发难,发言稿至今保存在他的档案里。7月6日,他在巴塞罗那大学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讲演。12月16日,他又在索邦大学发表关于法共二十二大的讲演,其文稿便是1977年5月在马斯佩罗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二十二大》。整整一年后的1978年5月,他在马斯佩罗出版了第二个小册子《不能在共产党内继续下去的事情》——这是同年4月24—27日在《世界报》上连载并引起轰动的一篇长文(出版时加上了序言),对法共的政治路线、组织和意识形态作了全方位的批评。
阿尔都塞批评法共领导层默默改变战略:在将新战略强加于党的同时,为了隐藏矛盾,不向“战士们”(法共对党员的称呼)公开解释战略转变的深层理由,使他们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无法向身边的群众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的战略转变只会导致失败,而“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列宁语),更是一种虚弱的表现。他批评法共的结构和运行模式复制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军事机器的结构与运行模式,成为实行统治的等级性实体;正是这个机器导致党在关键问题上的沉默,使党内民主让位于领导层的实用主义和权威主义。他批评法共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建立在“战士们”对党的信任之上,另一方面又对这种信任盘剥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法共内部消失了,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抛弃了“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意识形态和理论被简化为维持某种统一的工具,最终损害了党在政治实践中与群众的联系。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要让党“走出堡垒”(一个来自马基雅维利的比喻),到群众中去,关注人民群众的需要和首创精神。他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带回到生活中,深入批评并改革党的内部组织和运行模式,在对法国社会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工人阶级和民众力量建立联盟的路线和政策。
这篇文章的发表与《怎么办?》的写作是在同一年,它的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后者,尤其是其中未完成的部分。不过,随着《黑母牛:想象的访谈(二十二大的缺憾)》文稿在近年整理出版,我们得知,从1976年4月到1978年5月,阿尔都塞在两年间陆续发表的上述言论与文字,都只是他在1976年的某个时刻就已经完成的这个长篇文稿的冰山一角。《二十二大》和《不能在共产党内继续下去的事情》这两个政论小册子是阿尔都塞生前在法国出版的最后两本书。但现在我们得知,《黑母牛》,这部从写作到面世相隔40年的长篇著作,才构成了他的政论写作的顶点。
然而,正如戈什加林指出的那样,阿尔都塞在政论写作中思考的主题,尤其是关于阶级专政的主题,也以更严格的理论形式出现在他同一时期的哲学写作中——从1976年的《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到1978年的《局限中的马克思》,而后者更是他“对国家和阶级统治问题进行反思的顶点”。现在我们同样得知,从1976年到1978年,除了《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局限中的马克思》这两个长篇外还写出了《哲学的改造》《论马克思与弗洛伊德》《马基雅维利的孤独》和《写给非哲学家的哲学入门》(又一个长篇)等文本的阿尔都塞,也达到了他的哲学写作的顶点。
《怎么办?》作为这一时期的第五个长篇,就在阿尔都塞的哲学写作与政论写作之间,尤其是在两者的顶点之间,占据着某个位置。想要说明这部著作的性质,就要说明这个位置的特点。
二
在《黑母牛》中,阿尔都塞以充分的论证表明,他对法共新路线的批评并非出于单纯的政治理念之争。他把“二十二大的缺憾”归结为领导层没有把党的路线或战略的制定建立在“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之上,并一再强调列宁这个著名提法的“生死攸关的必要性”:
如果不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如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就不是共产党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斗争,以至于不能自称革命者。这意味着我们将投入盲目的斗争,而这种斗争不会通向革命的胜利。
一切都取决于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但在第一时间阅读这部手稿后,艾蒂安·巴利巴尔提出:因为作者是以普通基层党员的身份虚构了一份“自我访谈”来谈论党的决策,所以不得不“把自己放在‘假设知道’的位置上”,这使他难以避免一些弱点,以至于“鼓吹具体分析却未提供具体分析”。两年后,似乎是为了回应巴利巴尔的批评,“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成为《怎么办?》这部新手稿的真正主题。不过,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应追寻“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在阿尔都塞著作中留下的线索。
实际上,在我们目前讨论的时期(1976—1978年)之前,这个提法在他的文本中很少出现。在《矛盾与过度决定》(1962年,收入《保卫马克思》)、《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1967年)、《列宁和哲学》(1968年)、《列宁在黑格尔面前》(1969年)和《帝国主义论稿》(1973年,收入《历史论集》)这些集中论述列宁的文本中,这个提法根本没有出现。
在1965年出版的《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里,各有一处出现了这个提法,但都属于侧面提及。一处是在《关于唯物辩证法》(1963年)里论述“条件”概念,另一处是在“《资本论》的对象”这一部分论述历史理论的概念及其对象。两处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这些概念都“不是经验概念,不是对存在着的东西的确认”,而是“建立在对象本质自身基础上的理论概念——一个总是已经被给予的复杂整体”。因此,两处也带有同样的目标,即对关于“具体”的“经验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
尽管“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在《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中很少出现,但我们知道,在这些著作中并不缺少关于“局势”(“形势”“目前时刻”“最薄弱环节”等)“分析”的论述,尤其是以列宁的分析为典范;并不缺少关于在这种分析中“以实践状态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述。同样,在这些著作中也不缺少对“具体”在“理论实践”中的理论生产特性的强调,特别是将这个“具体”代入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公式中去讨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使用了、大概也是强用了马克思的一小段文本”,“从中得出直观和表象是被马克思当作抽象来看待的结论”,从而论述了一个类似于劳动过程的“认识过程”或“理论实践进程”:用理论工具(“一般性乙”)对理论原料(“一般性甲”)进行加工,从而生产出理论产品(“一般性丙”,即马克思所谓“思想总体―思想具体”);论述了这个“思想具体”作为“复杂整体”(马克思所谓“许多规定的综合”)的理论特性;论述了“思想具体”与“实在具体”的不同:由于实在具体“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马克思语),因而在思维行程中“必须从抽象出发”,达到思想具体;论述了实为“抽象”的经验主义伪“具体”所带有的“意识形态神话”……这些论述都属于由《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所塑造并为人们所熟悉的“阿尔都塞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之所以很少出现在由这些论述构成的理论框架中,只是因为它在那里早已有了一个自明的位置,以至于我们凭借一种理论的内部逻辑,甚至一些词语的关联,就可以先天地为它指定这个位置呢?这种危险是存在的。不久后,阿尔都塞自己便把这种危险命名为他的“理论主义倾向(tendance théoriciste)”。这种倾向的顶点就是把哲学定义为“理论实践的理论”,把它从与政治实践的关系中剥离出来,使“理论实践”构成一个自足的循环。于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便会不言自明地出现(或隐藏)在这个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论实践进程”的终点。
然而,如果打破这个循环,用“关于阶级斗争规律的科学”去认识哲学,就像阿尔都塞在对“理论主义倾向”的“自我批评”中所做的那样,把哲学重新定义为“理论中的阶级斗争”,从而向理论揭示出它有一个叫作实践的外部,以及这个外部对于它的优先性,那么,人们便会认识到:理论只是在与实践相结合的进程中,换言之,在对阻碍这种结合的无穷现实难题的克服中,才有资格被称为“理论实践”。于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就不再有一个单纯由“理论实践进程”所规定的自明的位置。它的位置将由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进程所规定,将受到这一进程中各种矛盾和关系的“过度决定”。
这是一个仍被阿尔都塞付诸沉默的位置,因为只要实践还没有张嘴说话,理论就不得不保持沉默。而对这种沉默的认识,就构成了阿尔都塞自我批评的开端。
三
1966年6月26日,在从《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出版后的一次精神危机中恢复过来,又经历了法共阿让特伊会议(1966年3月)的党内批评之后,阿尔都塞在高师召集了一次会议,作了题为《哲学的形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报告。事隔10年之后,巴利巴尔在就“具体分析”问题对《黑母牛》提出批评时,不知是否想到他曾亲耳聆听阿尔都塞在这个报告里说过的一段话:
我忘了谈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暂且称之为经验认识的问题。例如,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我既没有制订关于这个提法的理论,也没有给出这种理论的大致轮廓。我不是说我所写的东西妨碍我制订这样的理论,但是关于经验认识的理论的不在场,像所有不在场那样,甚至会在在场的东西即说过的东西内部,造成一种歪曲和移置的后果。对此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说:径直强调理论和理论实践的特性,这样会在写过的东西中导致一些(令人尴尬的)沉默,甚至一些含糊不清之处。
显然,“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这次出现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是它在阿尔都塞文本中第一次得到正面论述,但作为一个“不在场”的对象,又具有一种否定的(自我批评的)形式。阿尔都塞接着预告说,他“正试图写点东西来弥补这个空白”,据弗朗索瓦·马特龙所说,这大概指的是“他最终没有完成的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品(1966—1967年)”。直到1967年10月,当阿尔都塞在为《保卫马克思》外文版写的《致读者》中“以‘自我批评’的名义”指出书中存在的“一些沉默或半沉默”时,被他摆在首位的仍是这个尚未弥补的空白:
尽管我突显了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生死攸关的必要性,尽管我因此揭露了各种形式的经验主义,但我并没有探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难题,而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大概谈到了“理论实践”中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我还没有触及政治实践中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我再说得明确点。我没有考察这种结合的一般历史存在形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融合”。我没有考察这种“融合”的各种具体存在形式(各种阶级―工会斗争的组织、这些组织指导阶级斗争的政党手段和方法,等等)。我没有确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些具体存在形式中的功能、地位和角色: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何处以及怎样干预到政治实践的发展中,政治实践又在何处以及怎样干预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中。
这篇《致读者》与同年为《阅读〈资本论〉》意大利文版(后来也用于法文版和其他外文版)所写的另一篇更简略的《致读者》一道,公开承认了这两部著作中的“理论主义倾向”,通常被视为阿尔都塞自我批评的开端。不过,我们现在有理由把这个开端提前到1966年的《哲学的形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仅因为时隔近30年之久才得以出版的这个讲稿已经包含了《致读者》中自我批评的要点,而且——对于我们目前的讨论来说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明确地把“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引入自我批评的中心,从而有助于我们沿着这条隐藏在阿尔都塞文本中的线索,更深入地理解这一自我批评的构成和后果。进而,我们有理由把这个开端视为一个从1966年到1967年逐渐形成的“认识过程”(借用阿尔都塞自己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先前著作中的“沉默或半沉默”的认识逐渐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逐渐被“加工成概念”(马克思语)。当然,这个作为开端的认识过程只是一个更大的认识过程——自我批评过程——本身的一部分。
实际上,1966—1967年(延伸到1968年2月的《列宁和哲学》)是阿尔都塞在其写作生涯中堪与1976—1978年相比拟的另一个高产期。这两个高产期长久以来并不为人所知,只是随着其间绝大多数文稿在作者身后整理出版,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但它们表现出来的惊人爆发力与阿尔都塞自我批评的关系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相比起来,第一个时期更容易被1965年耀眼的光辉所遮蔽。他在这两年里写出的诸如《话语理论笔记三则》《论“社会契约”:错位种种》《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论费尔巴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任务》《人道主义之争》《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哲学笔记》等中、长篇文本,以及包括《哲学的形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内的一批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与政治、艺术、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和中国“文革”的文章,都带有某种过渡、尝试、规划和游移不定的特征,反映着这个自我批评的开端作为一个认识过程的紧张、亢奋、广度和深度。
我们目前仅限于沿着“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线索,指出一篇题为《论理论劳动:困难与资源》的文章在这个自我批评开端上的重要性。这篇几乎被人遗忘的文章写于1966年12月,发表于次年3—4月号《思想》杂志。与同年所写的另外几篇文章一样,它并未摆脱“理论主义倾向”,所以被阿尔都塞本人称为“蹩脚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把“经验概念”从“具体”或“具体分析”中断然排除出去的做法,这篇文章在坚持与经验主义划清界限的前提下,通过对“经验概念”的重新“加工”,承认了它在理论生产实践中应有的位置:
……经验概念给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概念增添了某种本质性的东西:恰恰是对具体对象的(严格意义上的)存在的规定……它们的确表达了一种绝对的要求,即任何具体认识都不能没有观察、经验,因而还有它们所提供的材料(这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依据“事实”进行的巨量经验研究,与所有伟大的工人运动领袖在“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任何时候都必须进行的具体调查研究相一致的方面),但同时,它们又不能简化为直接经验调查所提供的纯材料。
不同于在《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中仅仅强调“具体”的“理论概念”特性,阿尔都塞在这篇文章中把马克思关于“具体”所说的“许多规定的综合”明确定义为“认识的两类要素(或规定)的正确结合―汇合”,即理论概念与经验概念的结合。理论概念是关于抽象―形式对象(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形态”“阶级斗争”等)的认识。它们并不为我们提供关于具体对象的具体认识,但对于这种具体认识的生产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经验概念关乎实在―具体对象的独特性的规定(如1917年俄国或1966年法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阶级斗争的“形势”或“具体情况”),但它们并不是现实的纯粹给定物,不是对现实的单纯描摹或直接阅读,而是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的结果,包含了若干层次或程度的理论加工。换言之,阿尔都塞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重新定义为:经验所提供的素材和原料经由理论概念的干预或加工而被转化为经验概念的过程,而“‘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则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加工劳动的例证”。
“一切理论话语存在的终极理由都是关于特殊的实在具体对象的‘具体’认识。”这种具体认识作为理论概念与经验概念的结合,并不是两个彼此外在的东西的结合,而是“与被加工了的经验概念相结合的、必要的(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概念的综合”。“具体”需要理论来把握,但理论通向“具体”的道路也需要经验概念来开辟。就像马克思说剩余价值在现实生产中得到“实现”那样,经验概念也在关于具体对象的具体认识的生产中“实现”了理论概念(这种实现,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当然不是那种黑格尔式的“幻觉”——理念在实在具体中神秘的、思辨的“实现”)。
把关乎实在―具体对象的经验概念放到认识过程的结果或理论劳动的实现的位置上,意味着在理论自身中“确保实践对于理论的优先性”,意味着阿尔都塞在对“理论主义倾向”的自我批评中,向“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发出的召唤。
来源:西北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