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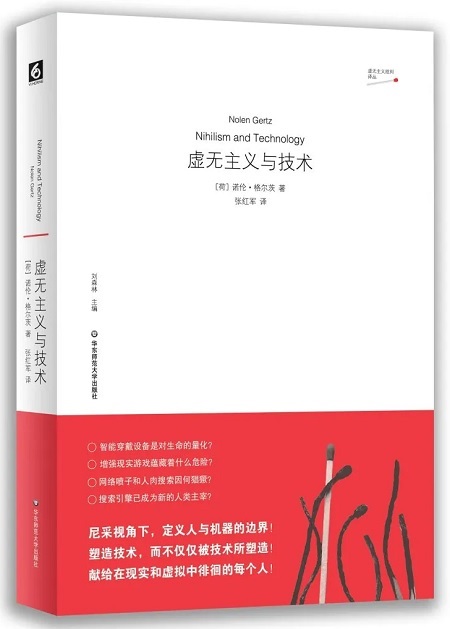
《虚无主义与技术》(订购)
[荷] 诺伦·格尔茨 著
张红军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6月出版
技术催眠是我用以描述我们越来越转向技术手段进行自我催眠这一现象的名词。这种对我们的人性的逃避、对我们的脆弱的逃避、对我们的有限性的逃避,今天仍然与我们同在,并且与尼采的预言相一致,只是相较于尼采时代变得更加严重而已。今天我们也许不太感兴趣佛教的精神层面或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层面,但仍然对自我催眠非常感兴趣,并且赋予自己大量的技术手段来让自己入眠,以达到今天我们可能描述为拖沓(procrastination)或更常见的“发呆”(zoning out)状态。
利用技术来达到发呆状态的想法可能与看电视最有关。电视最初作为一种奢侈品可能旨在娱乐观众、传播信息,最重要的是向观众宣传产品,但现在已经稳步发展成一件普遍存在的家具,我们打开它并且让它在那里开着,就像一盏灯那样,我们可能使用也可能不使用。
一觉醒来,打开电视,一片除了寂静和你的思想以外一无所有的空间,立刻被声音、某些东西或任何东西所占据。关掉电视,离开。回来,重新打开电视。在这期间,你还可以在公交车、火车、飞机、商场、广告牌、电脑、手机甚至手表上看电视。
这个世界充满了屏幕。从尼采式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发展。屏幕占据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空间、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感受。也许令人震惊的是,我们虽然已经意识到了盯着屏幕看的僵尸效应,但还是会继续花几个小时一直盯着屏幕。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嘲笑电视是“笨蛋匣子”和“白痴盒子”,嘲笑电视观众是“沙发土豆”,但这并没有阻止我们到处放置屏幕,尽可能多地盯着它们看。事实上,固定播出的当地晚间新闻节目通常是关于看电视对我们有害的故事,而这种讽刺并没有让我们关掉电视。
如果有什么要说的话,那就是我们之所以会喜欢屏幕,恰好是因为它们的僵尸效应。我们筋疲力尽——无论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孩子,还是我们的政治领袖——因此,我们认为对着屏幕发呆几小时是我们应得的东西,它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特权。换句话说,我们知道看电视就是逃避现实,而这正是我们喜欢它的原因。
我们知道技术可以催眠我们,而我们认为这种催眠不仅令人愉快还很正当,这一点对于理解技术催眠设备、网站和应用程序的激增来说很重要。我们完全有能力——由于技术的多稳态性——将几乎任何技术变成技术催眠的工具,不管它是否有意被这样使用。然而,由于技术催眠并不是我们羞于承认的一种追求,所以设计师们可以将技术催眠视为其创造物的一种特征,而不是缺陷。
“网飞与放松”(Netflix and chill)一开始是一种委婉的说法,但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梗。网飞公司最初并没有把自己作为一种约会工具来推销,但当这个梗走红后,网飞充分利用了这一新获得的成功,把这个梗变成了一场营销运动。对强调潜在用户的网飞公司来说,重要的不再是其光盘出租库的大小,而是流媒体服务的算法能力,后者可以发现你想看什么,继续为你提供这样的服务,并且尽可能少地干预用户,这样你就可以“放松”了。
于是,“刷剧”(binge watching)现象就诞生了。再一次地,就像在“白痴盒子”前的“沙发土豆”,这个描述听起来很消极。不间断的流媒体电视,一集接一集,一小时接一小时,这让人想起“酗酒”(binge drinking),一种老式的自我催眠,它会导致呕吐、昏迷和死亡。当然,如果有人批评另一个人是沙发土豆时,这种批评隐含或明确的建议是,他应该出去走走,见见人,说说话,或者去酒吧。于是,这种批评关心的并不是一个人正在进行自我催眠,而是一个人在进行错误的自我催眠,他应该让他的自我催眠更具社交性些。
这种不是对发呆而是对纯粹的发呆的批评,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流媒体服务和刷剧会变得如此流行。再一次地,屏幕无处不在。由于屏幕的普遍存在,我们可以在一个屏幕上观看流媒体服务,同时又在另一个屏幕上发布对我们正在观看的内容的推特评论。看电视不再是一种孤独的逃避现实的消遣,因为流媒体服务和社交媒体一起把发呆变成了一种社交性的参与活动。
这里人们可能会说,如果看电视已经成为一种社交性的参与活动,那么它就不应该被视为发呆、技术催眠或虚无主义,而是生活中有意义的一部分。当然,人们也可以这样谈论佛教。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重要的都不是人们是否从该活动中获得了意义,而是该活动是否可以被用作一种逃避现实的形式。
的确,对尼采来说,自我催眠之所以是虚无主义的,正因为我们从逃避现实中获得了意义。我们从追求涅槃和网飞刷剧中发现的意义,指出了我们贬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重新授予另一个世界价值的能力,我们创造的这个虚构的世界,让我们不再必须成为我们所是。
本文节选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虚无主义与技术》。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