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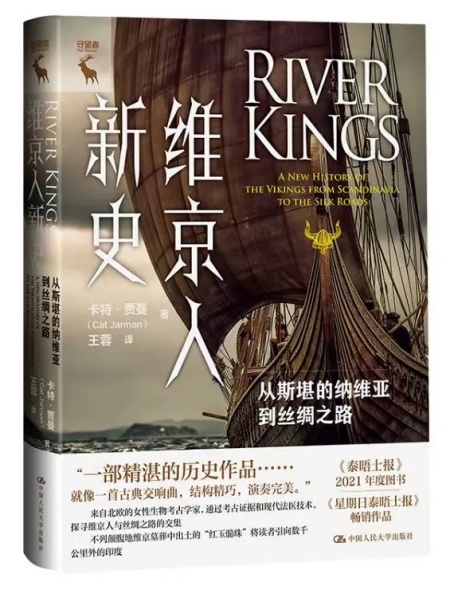
《维京人新史:从斯堪的纳维亚到丝绸之路》(订购)
作者:卡特·贾曼(Cat Jarman)
译者:王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同位素分析这一现代法学技术,已经成为考古学中,追溯人的地缘背景所用的一种主要方法,通过这一技术,能够让研究者直接研究尸骨生前经历的各个方面,甚至是独有境遇。在《维京人新史:从斯堪的纳维亚到丝绸之路》第一章《托尔之锤:骨》中,考古学家卡特·贾曼向我们描述了她是如何通过同位素技术去追溯、还原维京尸骨的经历。
《维京人新史:从斯堪的纳维亚到丝绸之路》
——托尔之锤:骨(节选)
2012年我第一次访问牛津的那天,马丁·比德尔向我介绍了所谓的雷普顿勇士———也称为墓葬511号墓主(简称“G511号”)。他的遗骸被仔细地放在三个米色纸盒里,整齐地堆放在办公室一角。小一些的里面装着他的头骨,另外两个大一些的长方形盒里装着其余遗骸。我见过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盒子,每个里面都装着从墓葬挖掘出来要存放在博物馆的尸骨。我读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G511号的报告,了解了有关他伤势的一切情况。通常情况下,外伤痕迹难以捕捉。刀切开皮肉时,强力已失,余下的力仅能在骨表层留下细小划痕。因此,尽管对受害者而言是可怕的致命伤,但骨头往往完好无损,因而我们无法了解死因。但这具遗骸的伤势显而易见。我从盒里拿起左股骨,可以看到斧砍穿臀部留下的深口。斧刃切入角度清晰可见,可怕的结果也可想而知。
这个标签上写着大写字母“V”的男人一直被认为是典型的维京人:高大强壮,金发蓝眼(虽然这些详细情况几年后才能知道)。在他身侧陪葬了一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剑,脖子上戴着托尔之锤银吊坠。这些能让人联想到他与维京世界联系的物品立即引起了挖掘者的注意。许多人都认为锤是传统维京勇士的基本象征。埋葬他的人还在他身边放了其他物品,大概是为后世之用,有一把钥匙、两把铁刀、一些衣服的搭扣和纽扣。托尔之锤另一侧是一颗色彩明亮的玻璃珠。两腿间的长方体软土块可能是木盒里的全部遗存了。里面是具寒鸦骨,大概象征着神奥丁的两只渡鸦福金和穆宁。骨盆旁放了一根野猪獠牙。
之后,将骸骨挖出清理,发现G511号曾受过许多可怕的致命伤。头骨有多处伤口,从伤痕可以看出他可能死时戴着头盔,眼窝处也有割痕。椎骨有多处割痕,与切除内脏伤口一致,也就是说他的内脏被摘除了。最严重的伤是左股处的斜切深口,由斧贯穿髋关节和股骨砍下。在这一过程中的某个瞬间,有人认为可能砍掉了他的生殖器,阉割了他。野猪獠牙放在两腿间,可作为替代,确保逝者完整地抵达奥丁的殿堂瓦尔哈拉。在这里,倒下的勇士到夜晚可享盛宴,那勇士必须是完整的。
或许有些传奇,但无论如何这处墓葬具有勇士的所有标志3,且G511号的墓是整个英格兰唯一一处妥善挖掘的维京勇士墓,因而意义重大。虽然历史文献表明,这样的勇士葬身于此的有数百甚至上千人,但没有哪处骸骨是完整的。许多有关这处墓葬的信息表明墓主的地位高,甚至可能是一位维京大军的首领。他的墓正好在曾是整个麦西亚王朝国王埋葬地的陵墓旁,这表明埋葬他的人想维护他(或者说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正统权力。
为完成博士课题,我再次研究雷普顿的维京人。G511号和雷普顿逝者这个新研究的关键部分是从一些尸骨取样,以便用一种最新的法学技术———同位素分析来尽我所能地了解他们是谁,又来自何方。在考古学中,同位素分析已成为追溯人的地缘背景所用的一种主要方法。传统方法是通过鉴别陪葬品的来源来确定,陪葬品即与尸体一同埋葬的物品,当然前提是得有陪葬品。但这一方法有明显缺陷。其一,用物品陪葬不一定是普遍做法,所以留给我们能重构逝者生前生活的痕迹就非常少。且就算真有陪葬品,与逝者一同埋葬的物品比如一柄维京剑或是一颗红玉髓珠也可能是经贸易交换得来的,分别经最后的所有者之手抵达埋葬地。我们找到的墓葬在许多方面尚有无法确定之处,我们无法了解这些物品是逝者的还是送葬者放在这里的赠物。这些物品可能无法反映多少逝者的生前经历,如一位考古学家所言:“逝者无法自葬。
其二,同位素分析能让我们直接研究尸骨来发现逝者生前经历的各个方面。虽然DNA也能做到这一点,但DNA主要提供人的遗传标记而非独有境遇。假设我死后葬在英格兰西南,骸骨的DNA分析能发现斯堪的纳维亚血统,或许能有一些线索证明我的迁移史。但在我孩子的骨骼中也能找到同样的基因,而他却在英国出生长大。也就是说,DNA分析无法区分第一代移民与其后代。
即便如此,DNA也可能让我们看到更大的图景:我们如何分布在全世界,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如何迁徙;还能让我们知道亲属关系,帮我们找到失踪多年的表亲,或发现疾病隐患。如你所想,在雷普顿墓葬的情况中,我感兴趣的是我们能否证明这些逝者是从斯堪的纳维亚迁徙到此的维京人。
正如此言,我们吃了什么,什么就会变成我们的一部分。你在读这本书时,你的身体就在消化上一顿饭,吸收所有可用来制造新细胞、新血液和新皮肤的成分。自你开始读这本书,你的全身都在变化。现在甚至骨骼也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新骨骼沉积取代旧骨骼碎片,以保持韧性和构造。这一原理几乎解释了你身体的所有部位,只有一个例外:你的牙釉质。牙釉质一旦在儿时形成就不会改变,甚至足够坚固,可以在土里恶劣的环境下完整保存数千年。因此,牙齿是生物考古学家最好的朋友。
因为所有组织在形成过程中会不断地从你的饮食中汲取营养,所吸收的物质痕迹也能告诉我们你吃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实现我的目标:弄清楚你在哪里吃了它。儿童时期你的牙齿基于你吃的食物和饮用的水而形成,而这些食物和水又携带着其生产环境中特有的标记或变化。比如,植物的大部分营养来自生长的土壤,这些土壤特征的形成基于潜在的地质环境。如此一来,也就是说,在德比郡种的小麦做的面包与在丹麦种的小麦做的面包,其化学特征会有细微差异。
一种检测此种差异的方法要借助一种叫锶的元素,这种元素自然存在于几乎所有事物中。锶有几种同位素,即同一种元素的不同形式。其中一种与另一种的比值在不同的地质类型中是不同的,因而在不同的土壤中也是如此。锶通过食物链传递时,这一比值保持不变,比如从土壤到小麦到面包再到维京人肚子里。且锶的这一比值一旦成为儿童新形成的牙釉质的一部分,就将会伴随他余生甚至直到逝世之后。如此再看那位雷普顿勇士,应该可以弄清楚他是否真的是入侵的维京人还是在当地长大的。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身份问题是复杂的,尽管这些方法有极高的可信度,但这并非仅靠科学就能解答的问题。即便同位素数据很明确地表明某人是在斯堪的纳维亚长大,可这并不代表他们就是“维京人”。实际上,没有科学方法可最终确定这样一个明确的身份。同样,看似来自本地也不能自然而然就表明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我们的身份错综复杂,且在我们的一生中不断变化调整。我是考古学者、科学研究者、作者,也是母亲和移民。但除了我的移民身份,其他身份都无法在我的骨骼中体现。因此,不论如何解释这些科学结果,我们必须要谨慎,要总是在尽可能多的不同来源的证据下考虑分析。毕竟这些新技术为我们研究墓主生前经历提供了机会,而在几年前我们也只能是想想。
虽然这些方法听起来简单,但要花费数月在实验室工作才能得到所有需要的数据,还要再花几个月的时间将这些数据整理成电子表格、数据库、关系表和比较地图。但G511号的锶数据相对容易解释:他一定不是在雷普顿或是附近长大的。牙齿上的信息表明他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很可能是丹麦,恰好完全与考古记录吻合。但同位素分析中的另一个结果也较为明显,即他身旁葬的那个人的数据。G511号并非单独埋葬的,与旁边更年轻的G295号埋在一处。虽然实际上尸体是错开时间埋的,更年轻的那位是在G511号埋葬后不久葬在这里的。两座墓由矩形石头连接,还有个碎裂的盎格鲁撒克逊精致雕塑,这也表明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这样的双墓穴在维京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很常见。有时夫妻合葬,有时同性合葬,几乎同性合葬的都是男性。后者这样的情况中,没人能确认两者的关系。
同位素数据可以额外说明的是,从同位素角度而言更年轻的这位男子与这位勇士成长的地方几乎一样。他同样受了重伤,很可能死在战争中。但他的墓中没有G511号中那样的贵重陪葬品,仅有一把刀。似乎这两人来自同一个地方,很可能是丹麦。新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揭开了两人逝世的一些信息。死于873年至886年,这使得两人甚至更可能与维京大军相关。有人认为这是一位首领与其武器守护者,甚至认为更年轻的男子是有意被杀死来陪伴他的主人。几年后,他们埋在一处的原因被揭开。
在与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遗传学家拉尔斯·费伦施密茨博士的合作中,我们想试图从雷普顿样本中提取出古代DNA。目的是找到更多证据确定这些人有斯堪的纳维亚血统,同时研究任何可能的家族关系,尤其是这位勇士与其同伴间的联系。十多年前,其他遗传学家也曾试图这么做,但没成功。当时能用的方法不太可能区分开骨中原始DNA与此前挖掘、清理和检查的所有人的DNA外污染。到2016年,技术进步到不仅能获取未污染的DNA,也能分别研究母系与父系血统及常染色体DNA,即继承自父母的独特染色体组合。拉尔斯及其同事发现这两人在父系血统有直接一级的家族关系,这意味着两人可能是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或者父子。考虑年龄差距,后者更有可能。此外,他们还发现G511号的眼睛颜色最有可能是蓝色,头发颜色最有可能是金色。如此,G511号的确符合高大金发维京人的传统形象。或许也有例外特征,遗传学数据还告诉我们他最有可能是光头。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