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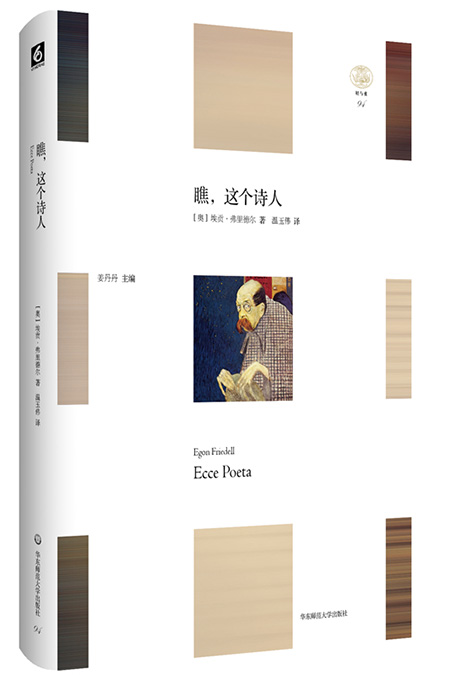
《瞧,这个诗人》(订购)
作者:[奥]埃贡·弗里德尔
温玉伟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从哲学、文化批判的立场出发,对现代以及现代性进行了深入剖析和反思,可谓现代“人的灵魂与精神状态评述”。
在书中,作者埃贡·弗里德尔首先探讨了诗人的本质,尤其是澄清了现代诗人的身位问题。他将诗人纳入哲人-立法者之列,认为即便在现代,诗人仍然是“人类范式”,是道德伦理的倡导者、实践者、推行者,乃至世界的变革者。
诗人何以被如此推崇?寻根究底,这与现代文化的持续混乱息息相关。在此意义上,本书也是一部由小见大的现代文化史,借助诗人这根奇异的探针,探察现代人的普遍困境和需求,进而发掘现代文化的隐秘机理。
编辑推荐
本书是对尼采《瞧,这个人》的模仿和影射,接续了对现代性的精辟分析。
这是一部现代的文化史,是对灵魂和文化心理状态的分析,是对个体困境和需求及其满足方式的审视。
本书为散文体,强调语言的纯洁性,可读性强。
作者简介
埃贡·弗里德尔 (Egon Friedell,1878—1938),奥地利历史哲学家、戏剧家、小说家、宗教学家、翻译家,甚至还是神秘主义者。1904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作为哲人的诺瓦利斯》),离开所谓学术圈子之后,以作家、批评家、演员、记者等身份活跃在维也纳文人圈子中。留存后世的作品有《现代文化史》(三卷本,1927-1931;中译本《现代文化史》,王孝鱼译,商务印书馆,1936)、《古代文化史》(卷一,1936;卷二,1950)、《歌德——独幕剧》(1908)、《时光机漫游——科幻新奇小说》(1946)等。
译者简介
温玉伟,主要从事近代早期德语文学研究,目前已出版的译作有《论德意志文学及其他》(弗里德里希二世著,华夏出版社,2024)、《作为悲剧的世界史》(斯宾格勒著,商务印书馆,2022)、《驳马基雅维利》(弗里德里希二世著,华夏出版社,2022)、《施特劳斯学述》(考夫曼著,华夏出版社,2022)、《欧洲文学中的古代与现代——简论古今之争》(勒策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等。
精彩书摘
人类的盛装
总结起来,同样有三类诗人。一类是超人性的英雄和艺术的理想形象。他们很稀罕,仿佛是幸运的偶然。另一类是同样歌唱伟大事物但是自身不具备伟大性的诗人。然而,他们常常把握住任意一种正在搅动时代的普遍情感,比如爱国主义、爱情、友谊、虔敬。这类诗人就是解放战争中的爱国诗人,中世纪的宫廷抒情诗人,十八世纪的友谊抒情诗人,宗教改革时期的宗教抒情诗人。第三类就是我们称之为街头诗人的一类。
这些都是属人灵魂的不同盛装。第一类作品是人类伟大的珍品,它们永不过时,只会因为整个文化层被暴力推翻而让位,它们会一再地被拿出来,穿行诸多世纪描状着属人精神至高的光辉和至高的权力可能性。它们是阴沉的庆典活动或者燃烧的火光的装饰物,它们的观念随着时代而改变,就像王者的大氅和王冠的意义之观念会改变一样。不过,所有时代都一致认为,这些是永恒的伟大事物的标志。
第二类与第一类在形式上相似,不过也仅局限于此。它们是特定时代的面具,一旦时过境迁,它们也就不名一文了。它们只具有伟大的姿态,是表演王者的戏子的帷幕和装饰,它们对时代产生的强大影响就如真实的华服,当然,演员也可以达到这样的影响。不过,它们的影响只在一瞬间。一段时间之后,戏台会被拆掉,灯光会被熄灭,五光十色的东西会被扔进垃圾箱。有这么一些时代,它们只产生这类作品,它们有各色的盛装,但是没有一件真正属于自己。于是,人们习惯于把这些时代通通扫进垃圾堆。
最后,第三类似乎很少有,但是在实际中多得数不清。它们干脆就在看起来朴实无华的时代外衣上做针线活,而且只在这上面做。它们的作品制作出来既不是为了特别的节庆,也不是为了假面游行和展示,而是为了日常和眼下。因此,它们尤其具有工作装的特点,实用、结实,价格绝非高昂,人们可以随意地拿到并使用它们。它们处于最后的技艺完善化的高度,因为它们是时代的子嗣,适应于任何生活方式,任何工种,任何天气,任何场所。
简言之,第一类是盛装,第二类是演员化妆间的衣袍,第三类是真实的历史服饰,是服饰学中的衣物。它们在服饰的历史中也保留了自己永恒的地位。
为第三类诗人所特有的是,人们不会想象他们拿着瑶琴,甚至更不会想象他们头戴桂冠。他们与这些永恒的符号毫无关系。他们既不像第一类诗人那样给世人带来这类符号,也不像第二类诗人从古玩店租借它们。他们所服务的是没有瑶琴和桂冠的时刻。
我们随后要讨论的诗人就是一位街头诗人,倘若人们愿意,甚至可以说是从具有受人蔑视的次要意义上来讨论的。他走在大街上,这其实就是他所有的诗歌活动。他穿行于当下人的房间,穿行于他们的儿童房间,他们的餐厅,他们的卧室,他们的宴会厅、妓院,他们的乡间别墅和咖啡厅。他是真正的街头诗人和街头歌者,是眼下平凡生活的描述者和歌颂者。他没有穿着丝绒西装,没有打飘逸的领带,内心里面也没有。他戴着一副牛角夹鼻眼镜。
他捕捉到了他那个时代平凡的苦痛。只有通过讨论他的时代,我们才能更深入地讨论他。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