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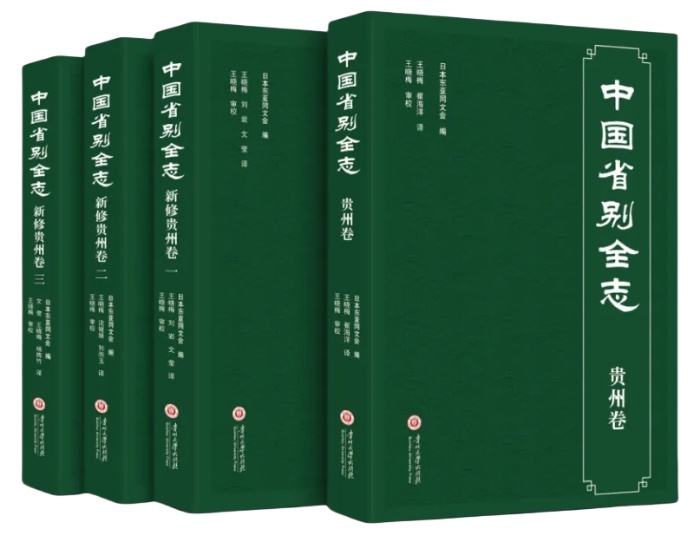
《中国省别全志》(订购)
《中国省别全志》是一部系统梳理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地理、文化、经济、社会等综合信息的权威性地方志丛书,服务于日本的对华侵略,为其与欧美列强争夺在华利益的斗争中提供学术和情报支撑。这套诞生于日本侵华机构之手、以精密“科学”调查为表、以服务殖民掠夺为里的志书,是中华民族伤痛历史的特殊见证,亦是埋藏着近代中国社会丰富实态史料的学术富矿。作为罕见的系统性省域史料,国内目前只有日文影印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线装书局)存世,由于语言壁垒的限制,很难为众多研究者充分利用。本书的翻译出版,将有力推动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史及贵州文化等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
序
(作者金勋: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乙巳暑月,惠风拂庭,草木葱茏,欣闻贵州大学王晓梅教授团队历经数年精心打磨的《中国省别全志》《新修中国省别全志》汉译本,即将由贵州大学出版社陆续付梓。这套由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的文献,既是近代日本对华调查的集大成之作,亦是研究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另类信史”。其汉译本的问世,如启重门,为学界提供一个观察近代中国的新视角,使我们得以从多元视角重审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实乃中国学术界一件可喜之事。
一
中国地方志传统源远流长,其雏形早在先秦时期便已孕育。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曾载:“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间接印证了早期方志“记山川、录旧事”的编纂传统。这一传统历经数千年演进,汉魏地记偏重风土物产的描摹,如《越绝书》《华阳国志》,以地域为纲,录一方之俗;隋唐图经则强调“图载疆域,经述政情”,以地图为骨、文字为肉,形成“图经合一”的体例;至宋代,方志体例趋于完备,如范成大《吴郡志》已涵盖沿革、风俗、城郭、水利等数十门类,奠定“横分门类、纵述沿革”的框架;明清时期,因朝廷大力倡导,方志修纂达至鼎盛,仅清代便修有六千余种,形成“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的完整体系,涵盖国家至地方、家族至个人的全方位记录,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然而,清末民初,内忧外患交织,中央权威式微,地方财力枯竭,这一延续两千余年的文化传统几近停滞。许多珍贵的地方史迹、社会风貌未及被笔墨定格便湮没于时代洪流,导致后世研究这一时期时,常陷资料匮乏之境。恰在此时,日本东亚同文会所编《中国省别全志》《新修中国省别全志》,以别样的面貌填补了这一空白,为我们留存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珍贵剪影。
二
19世纪末,日本推行“大陆政策”,对华情报收集成为其战略准备的核心环节。1898年,东亚同文会在东京成立,每年获外务省机密拨款,实为服务国策的半官半民机构;1901年,该会在上海设立东亚同文书院,将“实地调查”设为核心课业,成为实施对华调查的核心平台。
书院自1901年成立至1945年的近半个世纪间,培养了46届约4,600名学生。这些学生深入中国城乡腹地,踏出的调查路线逾700条,涵盖了20余省份,甚至延伸至东南亚与西伯利亚。正如近代日本政治家小川平吉在《中国省别全志》序言中所述:“诸生渡黄河、越阴山,西攀秦蜀峨眉之峰,南踏滇粤苗瑶之野,勇往直前,栉风沐雨,足迹遍及中国各省,调查报告书多达二十万页。”这些一手资料,构成了两套省别全志的编纂基础。
这套志书的编纂颇具特色,《中国省别全志》18卷,1917—1920年出版;《新修中国省别全志》9卷,1941—1946年出版。其体例既承中国传统方志框架,又融入近代科学方法,分总论(沿革、人口、气候等)、都市、贸易、交通、农林渔牧、工矿、商业金融、度量衡等八大类,辅以大量地图、统计表和照片,与中国传统方志的写意手法形成鲜明对比,构建起立体化的区域研究体系。这种编纂方式,既可见对中国方志学的借鉴,亦彰显其对近代科学方法的创新。
其史料价值,尤见于对社会变迁细节的精准记录。例如,对长江流域商业网络的记载,详至各码头货物吞吐量、商号资本额及交易习惯,弥补了同期中文文献的疏略。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不仅记录苗族、彝族的服饰、饮食,更触及部落组织与经济活动,为民族史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素材。据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所言,这些调查“在商业惯习、金融运作等方面的记录精度,远超同时期的官修方志”。
这套志书的连续性更显珍贵难得。1917年版对华北铁路沿线工商业的记载,与1941年版同一区域的战时经济状况对照,可清晰窥见抗日战争对中国经济格局的深刻影响;全面抗战爆发后,其对“经济统制”“清乡运动”“新民会”“亲日教育”的调查更为细致,为抗日战争史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
审视这套文献,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其编纂的侵略性本质,它始终服务于日本扩张战略。《新修中国省别全志》将调查重点放在西南、西北等未被占领地区,对云贵川三省矿产资源、交通要道的精密测绘,显然是为日本“南进”计划提供情报支撑,字里行间浸透着侵略者的野心。
然而,历史文献的客观性也使其超越了编纂者的主观意图。书中保留的大量原始数据,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的“硬证据”;其“实地调查+数据量化”的方法,将社会科学范式引入中国区域研究,为中国方志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参照。
三
长期以来,这套文献因语言壁垒,加之卷帙浩繁,国内学者难以充分利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推出的影印版虽解决了“可得性”问题,但不通晓日语的研究者与普通读者仍感障碍。贵州大学王晓梅教授团队的汉译工作,远非单纯语言的转换,更是一次系统性的学术再创造。
其一,实现了史料整理的完整性突破。译本首次全本汉译两套文献,工程艰巨可想而知。王晓梅教授曾坦言,原书“卷帙浩繁,原文为非通用语种之日语,没有足够的团队力量很难开展全译工作”。团队采用“分卷负责、集体审校”模式,将50册文献分为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六大组,每组由精通日语的学者牵头,历史学学者参与校订,确保译文的准确专业。内容处理上,团队坚持“存真与辨伪并重”。例如,对“猡猓”等歧视性民族称谓,统一改为规范表述;对“支那”“满洲”等殖民色彩词汇进行转述处理;对损害中国主权的表述,采“正文删除、脚注说明”之法,既维护国家主权,又留存文献原貌。
其二,构建了跨学科注释体系。原书大量专业术语与特殊表述,曾是阻碍读者理解的“拦路虎”。团队编制“译 +译者注”二层结构,注释涵盖历史背景、地理知识、专业术语解释等,使原始文献转化为易于利用的研究素材,极大提升了可读性与可用性。
其三,推动了编纂体例的现代转化。译本在保留原书结构的基础上,按现代学术规范调整。重排统计表并加以标注,规范章节标题,使其更契合现代阅读习惯与学术需求。
在文献整理技术上,面对50册文献中的大量模糊印刷与跨语种表述,团队与出版社结合现代文献处理技术与传统校勘方法,以高精度扫描和图像处理解决模糊问题,借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提高效率与准确性。团队“历经数轮研讨,反复推敲,几易其稿”,校勘笔记累积甚丰。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确保了译文的可靠性。在学术伦理与历史认知上,团队始终保持清醒,处理敏感内容坚守伦理,涉及国家主权立场坚定。对原文中有关领土主权的不当表述,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处理,既维护国家尊严,又保全文献的学术价值。
王晓梅教授团队的翻译,实为融合文献学、历史学、翻译学的跨学科工程。学者们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克服多重困难,奉献出了经得起检验的精品。
四
2025年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套译书的出版更显特殊的纪念意义。透过这些原始调查资料,我们可清晰窥见日本侵华的历史脉络。从1917年《中国省别全志》对华北矿产的调查,到1941年《新修中国省别全志》对西南交通的测绘,尽显其战略的长期性与周密性,为研究清末至民国时期日本对华政策提供了第一手证据。
同时,译书为当代国情调查提供了历史镜鉴。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虽服务于侵略,但其“实地调查+系统分析”的方法仍有可借鉴之处。今日中国更需精细化国情研究,这套文献的翻译出版,恰是对这种学术传统的探究与反思。
译书的学术价值惠及多学科领域,为中国近代史、方志学转型、边疆民族研究、中日关系史等领域的深入探索提供了新可能。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书中对各地商业网络的记载,为研究近代市场整合提供关键素材,可清晰窥见近代中国经济脉络与区域差异,为当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提供历史依据。在社会生活史方面,其对民间习俗的记录极具价值。书中详细描述的各地风俗、信仰、社会组织,为研究近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既有助于了解彼时社会风貌,亦为现代社会文化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在中国方志学现代化转型上,东亚同文书院调查将近代科学方法引入区域研究,其“问题导向—实地调查—数据分析—结论形成”的范式,对当代方志编纂具有启示意义。其系统性调查框架值得借鉴,可补当前部分地方志“ 条目简单罗列”之不足;其实证精神更值得学习,“逐日记录、逐月汇总、逐年对比”的方法,为当代方志“动态修纂”提供可行路径。在中日关系史领域,两套志书的编纂过程本身便是重要研究对象。比对1917年版与1941年版对同一地区的描述,可见日本对华认知的转变。早期尚留存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后期则充斥着殖民者的傲慢与野心,这种转变折射出侵华政策的演进。书中关于“中日贸易”“侨民状况”的记载,为研究民间层面中日关系提供新素材,与中文文献相互印证,有助于构建更为立体的中日关系史叙事体系。
五
近代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中国省别全志》与《新修中国省别全志》汉译本的出版,正是为学界提供了这样一套“新材料”。它不仅填补了清末民初区域研究的史料空白,更以独特编纂视角,促使我们反思历史研究的方法论。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特殊时刻,这套文献的翻译出版更具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铭记历史不仅是纪念胜利,更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既要警惕任何形式的侵略野心,也要重视国情调查的学术价值。贵州大学王晓梅教授团队以严谨态度完成这项艰巨工作,既为学界奉献了精品,更展现了当代学者的历史担当。
相信这套译本的出版传播,必将进一步推动近代中国史、中日关系史、方志学等领域的研究走向深入,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把握当下、开创未来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是为序。
来源:贵州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