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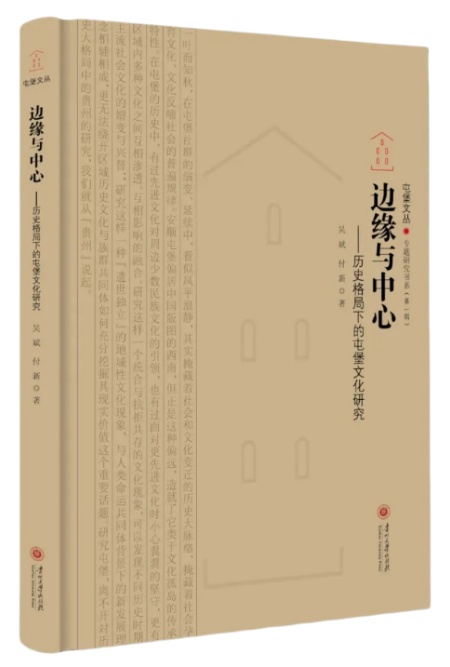
《边缘与中心——历史格局下的屯堡文化研究》(订购)
吴斌 付新 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边缘与中心——历史格局下的屯堡文化研究》以史料考证、现象分析、文本研究的方法,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屯堡文化,从屯堡社群的演变、延续中,挖掘整个历史变迁中的社会、文化传承的脉络,以及社会孕育文化、文化反哺社会的普遍规律,同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主流社会文化的嬗变与兴替。书中指出,作为一个尚存的文化共同体,屯堡人的贡献在于,他们在自身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巧妙而又忠实地实现了发源地文化与迁入地的环境有机结合,在坚持中又适时地发展了发源地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共同体。这个角度的研究,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和机制,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屯堡地戏传递的“身份”特征
(第七章 节选)
在贵州安顺屯堡地区众多独特的文化事象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地戏无疑。这是一种由演奏者头戴面具、身着彩裙,在锣鼓伴奏中舞蹈、打斗的戏剧表演。由于这种戏剧的表演场地并不在舞台上,而是在村寨空场或平地围场,因此被称为“地戏”,当地人也称之为“跳神”。
历史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地戏”的称谓是在《安平县志》——安平县即今安顺市平坝区,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以原“卢唐三寨及今金筑府地”置平坝卫,平坝之名由此而始,含有“地多平旷”之意。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裁平坝卫,设县,名安平县,隶于贵西道安顺府。《安平县志》成书于清道光七年(1827),由安平县知县刘祖宪主持编修,书中卷五有关于地戏的记载:“元宵,遍张鼓乐,灯火爆竹,扮演故事,有龙灯、狮子、花灯、地戏之乐。”巧合的是,屯堡文化的母源地江淮地区的历史记载中,在差不多的年代,也有“地戏”字样出现——清代范祖述所著的《杭俗遗风》中《时序类·太岁上山》有一段描述提及“地戏”,即:“立春前一日,杭府暨总捕、总理事、水利三厅;仁和、钱塘二县,着朝服,坐轿宪,全副执事,亲往庆春门外迎请勾芒之神。其神先期查取姓名年貌,或老或少,即将旧年神亭迎去,毁而新塑,彩画端整,仍供于亭。长约二尺许,头塑双髻,立而不坐。迎时,神亭之前有彩亭若干,供磁瓶于中,插富贵花及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等执事。大斑、鼓吹、台阁、地戏、秧歌等类,纸牛、活牛各一只,进城先往抚宪衙门报春,官即各回本署。神再行往各衙门毕,供于府大门外。”《杭俗遗风》应成书于清同治三年(1864)之后,钟敬文先生考证,《杭俗遗风》有范祖述之友林真作于同治三年六月的序。因此可以看到,在19世纪,中国西南的安顺屯堡和江南杭州都曾流行过这种名为“地戏”的娱乐活动。当然,这两种“地戏”虽同名,却未必为完全相同之事物。
屯堡来源于战争,发展于战争,这就决定了屯堡人必然是一个崇武尚义的群体。屯堡地戏的起源来历始终有较大争议。目前主流学界认为,地戏来源于军傩,是由“调北征南”后留屯黔中的明军将士带来的。高伦在《贵州地戏简史》中提到:“我们可以确认地戏就是傩礼中驱鬼仪式的傩戏演变而来的。它传入贵州的时间不会晚于明嘉靖,上限可推至宋时军傩的诞生和传播阶段。”军傩是傩戏的一种,对于军傩的记载,最早见诸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其中记载:“桂林傩队,自承平时,名闻京师,曰静江诸军傩。而所在坊巷村落,又自有百姓傩,严身之具甚饰,进退言语,咸有可观,视中州装,队仗似优也。推其所以然,盖桂人善制戏面,佳者一直万钱,他州贵之如此,宜其闻矣。”军傩原先流行于军队,带有一定练兵习武的性质,也带有祈神降福、振奋军威的作用,后来逐渐演变为民间傩戏的一种。军傩带有浓重的统治阶级的色彩,这决定了它只能表现忠君爱国之事,屯堡地戏作为军傩的衍生物,带有同样的特点。有别于其他剧种的题材多样,唱腔纷繁复杂,地戏的题材全部都是封建正统思想的内容,没有《西厢记》那种肝肠寸断的爱情叙说,也没有《水浒传》里的绿林义气,有的只是《三国演义》中关二爷的忠肝烈胆、《杨家将》的热血报国,地戏的唱腔也使用与这些忠烈题材相匹配的语调高昂的弋阳腔。
“弋阳腔”来自屯堡明军文化祖源地江淮地区。“安顺屯堡人的祖籍是弋阳腔流行的地域,屯堡人受到弋阳腔的影响,懂得弋阳腔的唱法特点,是极自然的事。联系起屯堡人所处环境来综合考究,安顺‘跳神戏之举’,当在明洪武十四年稍后至永乐年间这段时期发生。”范增如的这一观点,当算是这一观点的代表性言论。屯堡地戏与弋阳腔的演唱形式和风格一脉相承。弋阳腔在贵州的流传,据《南词引正》记载:“永乐间,云、贵二省皆作之。”而因明初朱元璋“调北征南”“屯田戍边”“调北填南”而来自浙江、江西、安徽、河南的将士以及百姓,把流传甚广的弋阳腔带到贵州也就顺理成章。由此可见,屯堡地戏和弋阳腔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
也有学者认为,地戏来源于军傩证据不足,更有甚者,认为“军傩”一说本身就存有疑惑,吴尔泰多年前就撰文认为,不仅屯堡地戏和“军傩”没有关系,且“军傩”本身是否存在都仍有疑问。他认为:“宋代以前的史料典籍或野史稗说中,都没出现过‘军傩’或相类的名称。如果历史上确有一个与‘乡人傩’‘宫廷傩’比肩而立的‘军傩’,这种缺漏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自从国家产生以后,军队就一直是国家和政权生存与发展的主要支柱之一,军队的活动往往决定国家和政权的兴亡更替。同样祭祀也是国之大典,是统治阶级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因此就决定了祭祀与军队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只要我们翻开中国古代史看一看,就会看到每有重大军事活动,必然伴随着祭祀活动这一有趣现象。或则祈求神佑将士无灾病,以利军旅征战,或则祷告神佑首战告捷,直捣黄龙,甚至以祭祀占卜来决定军事行动。所以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国之大事,乃戎与祀’便成了统治阶级立国的根本之一。有鉴于此,中国古代典籍和民间野史,对军队中的重要祭祀仪式和活动,无不记载详备,鲜有遗缺。傩祭是国家和民间的重大祭典,自中国历史有文字记载以来,历代都有记述,宋以前各代如然。民间野史稗说,乃至诗赋间,也记述得既丰且详。《论语》有孔子遇‘乡人傩’的记录,而‘国傩’‘大傩’(即宫廷傩)之叙,屡见于《吕氏春秋》《后汉书》及其他史书、方志中,至于如《荆楚岁时记》这类的笔记,对‘乡人傩’及‘宫廷傩’记述更是详尽备至,但翻遍这些文字资料,就是找不到‘军傩’一词。因此,我们有理由对此作出这样的判断,宋代以前,中国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一个相对独立于‘乡人傩’和‘宫廷傩’的‘军傩’。”
屯堡居民来源复杂,既有明初屯军后裔,又有随军而来的匠役、商人等,也有明朝时候陆续迁入贵州的犯官、流徙之徒以及中原、江淮等地因失去原有土地而不得不四处逃难的农民。这造成屯堡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吸收了多个时期、多个地域文化特征的独特文化事象,其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汉文化杂糅并蓄,甚至可能还掺入了某些少数民族的特殊礼俗。“屯堡人”不存在于中原、江淮或贵州其他地区,而仅存于安顺一地,这就明显说明,“屯堡人”和屯堡文化都是在特殊历史条件和特定人文环境中逐渐形成的,非一时一地之功。因此,很难说地戏是受固定的哪一个时期、哪一个地区的文化影响后产生并“传承至今”的,它也不太可能是某种单一来源的文化传承,反而更像是由不同的移民群体陆续带来的,由不同的祭祀、娱乐形式拼接而成的,它是现在所谓“屯堡人”这一族群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见证,也是屯堡居民在漫长的600余年中,自我精神世界发端、发展的外在映射。贵州省民俗文化学者顾朴光教授在其《安顺地戏纵横谈》中曾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屯堡人,就没有地戏;反之,没有地戏,屯堡人就会丧失它最具光彩的特征。”这一说法应该不无道理。
来源:贵州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