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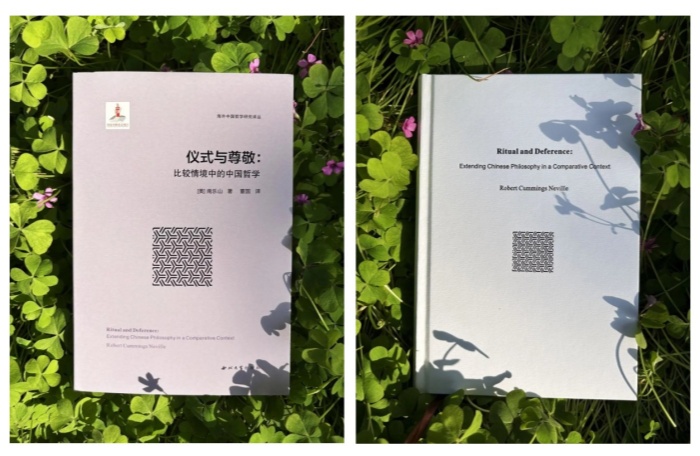
《仪式与尊敬:比较情境中的中国哲学》(订购)
[美]南乐山(Robert Cummings Neville)著
董国 译
西北大学出版社
前 言
此书为有志于中西比较哲学者而备。严格讲,我所受的正规教育,仅限于西方哲学、宗教与文化之内。故在福特汉姆大学,当托马斯·贝里介绍中国哲学(与印度哲学)时,我其实不太能理解自己对中国传统的热情。印度哲学及其他一些“非西方”传统哲学都曾让我颇感兴趣,但没有哪一个能像中国哲学那样让我如此着迷。比较哲学使我得以洞察自身在中国哲学中的特定学术志趣,如何与我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研究热忱贯通为一。
与大多数西方学者不同,我从未在哲学与宗教之间,做出某种无论是理智上令人满意的,还是实践上有所助益的区分。准确地说,我从未分开好学之士的哲学实践与宗教实践。故我把自己视为一个从中国、西方以及其他源泉,积极汲取养分的哲学家、神学家、哲学神学家、宗教哲学家,或宗教的哲学家。
因此,我的主要工作,乃建构一种哲学,能与我们时代的问题以及永恒问题密切相关。此种哲学,乃一或复杂、或成套之设想,对它的检验则包括:其是否连贯一致;是否适用于我们的世界,并能表现其中重要的事物;以及在推进关于何所为的全球性对话方面,是否富有成效。我为自己哲学中的各种观点提供丰富的论据,但我极少会断言自己的假设绝对正确,而他人的假设皆为谬误。相反,我在做出自己假设的时候,通常提醒大家其他哲学所忽视的一些观点,而这种忽视,其实易于纠正。本书各章节共同呈现了对中国哲学的部分解读,且常常将其与其他传统之哲学进行明确比较,旨在为更广泛的世界哲学对话贡献一己之力。
在写作中,我是一个有建设性与系统性的哲学家(尽管我自己的体系没太多直接表达在这本书里),而非一个汉学家。操英语写中国哲学者,大多数是汉学家,他们会看到这些章节在展现汉学的严谨规范和研究视角方面的不足。而我希望他们看到的优点是某种特殊的洞见——将中国传统作为一门活生生的哲学来钻研。《波士顿儒学》的反响,鼓励我表明自己的立场:儒学的研究者与践行者。如若我说,在我们的时代,儒学的诸多有趣发展路径中,有一种是我的哲学——还望读者忽略我的傲慢。虽然我和儒家传统一样强调伦理、修身和社会哲学,但在形而上学问题上,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我构建的形而上学体系,其中许多术语和问题都衍生自西方哲学。尽管如此,它仍然给予儒家形而上学的基本主题以当代阐释,如过程、有机联系、价值的普遍性、内在与相对超验原则的连续性,以及“形而上学对于美好生活实践的必要性”这一核心信念。系统思维是为了深化实践,使其更加关注世界上真正重要的事情。所有这些主题都是柏拉图式的,也是儒家式的,且都与基督教神学内的某些传统相一致。因此,我承认自己既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基督徒,也是一个儒者。在现代意义上,我也是实用主义的继承者和扩展者。
一些学者深切关注“成员归属”问题,即一个人是否真正全心全意致力于自己的传统。在中国哲学中,这种关注则表现为儒家“真传”之争。例如,朱熹在编辑(儒家)经典时,就把荀子从宗谱中剔除;最近牟宗三则提出,王阳明而非朱熹,才是孟子传统的真正传人。西方哲学有无数的柏拉图学派,不只有古代柏拉图主义、中世纪柏拉图主义,还有新柏拉图主义。当然,基督教内部也满是分裂。许多基督徒认为,救赎取决于一个人是否属于他们的特定教派,而非其他教派,当然更不能属于非基督教团体。对于关心成员学派归属的思想家来说,一个人同时成为儒者、柏拉图主义者和基督教徒,似乎不太可能。
我不太关注此种成员归属问题。对于那些被推崇适用于当代生活的每一种思想来源,我们应有所侧重,而不是全盘接受。鉴于不同类型基督徒之间的各种矛盾,甚至极端矛盾,只有一些是可以肯定的。我对柏拉图主义的特殊理解,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流行解读,大不相同(他们认为柏拉图是一个二元论者,相信某种存在与形式分离的独立实体)。与几个关系亲密的儒学同事相比,如杜维明、成中英和刘述先,我的议题来自古代儒学,特别是荀子对孔子的解读,而他们的议题则是新儒学的延伸。在这一点上,我和安乐哲、郝大维一致,尽管在其他问题上我们也有分歧。关键在于,一种建设性的哲学积极地从对其思想来源进行精挑细选的解读中汲取养分。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哲学辩护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对话,即讨论为什么有些思想脉络可以肯定,而另一些则需要抑制。
本书诸章节,原初皆为应邀之演讲或论文,源自特定的场合或计划。尽管已经进行了编辑、交叉引用和消除重复的工作使其保持一致,但不同的风格,仍反映了其不同的来源。作为独立呈现之作,其易读性,在我那些通常严肃枯燥的专题论文中,比较少见。第一章始于2005 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大夏讲坛”,原名为《当代儒学思想的扩展形态》,原作被翻译为中文,我听说在中国互联网上流传广泛。本章作为全书引言,认为儒家传统在形而上学、宇宙论、对人性和经验的理解以及社会理论等方面,都有值得发展的主题。而为了使儒家成为(哲学)对话的重要参与者,这些主题则应以与更大范围的哲学讨论相联系的方式加以重述。
第二章源于2005年2月在韩国首尔的会议上的演讲稿《儒家价值观的当代意义》,主题是“从混乱走向有序”,并以中文、英文、韩文发表在《栗谷研究学报》上。其基本主题为,在全球多元文化的语境中,生活中的基本价值观存在争议,而儒家价值观则可以被重新表述,以表达“美好生活”的观念。儒家的主要贡献在于其仪式 理论,即人们如何能就关于美好生活的根本差异,进行协商。
第三章则扩展了第二章关于荀子仪式理论的论述,并认为查尔斯·皮尔士的语用符号学理论,非常适合将仪式理论引入当前的讨论中。其后,本章根据荀子的观点,分析了仪式在形成欲望中的作用,以及欲望在形成如“美好生活”这类伟大文明价值中的作用。诸欲之争,以及在仪式中融合的心物之力,共同构成了一种内在的自我观念。这样的自我,在压力下充满了爆炸性的矛盾。与孟子相对简单的理想主义相比,它与后来弗洛伊德和尼采的思想更有亲缘性。
第四章将重点放在道家伦理上,并间或与儒家进行比较。形而上学往往是儒家思想中假定的一个子主题,而在道家哲学中,自然观及其基本特征,则是其伦理学的直接与重要来源。本章探讨了道家《道德经》和王弼的形而上学。
第五章和第六章论述了中国哲学在当代的接受和运用情况。第五章从相关翻译作品到研究者,分类考察中国哲学在英语世界的影响。第六章,其初稿以《中西方哲学中的方法论、实践和学科》的标题发表于由牟博主编的《通向智慧的两条道路?》,此篇论文详细讨论了基于中国模式的哲学实践意味着什么。
第七章扩展了第一章中关于形而上学的讨论。首先,尽管存在康德式的反驳,但是形而上学,实有其正当需要;其次,中国和西方都需要使其形而上学思想适应新的科学世界。此章阐明了关于此二者的一些想法,并指出了相应的发展方向。
赫伯特·芬格莱特,是西方最早一批认真对待儒学的、受过训练的哲学家之一,他所著的《孔子:即凡而圣》提出了一个经典论证,即以人道(仁)与仪式(礼)的双重主题进入儒学核心,这在当代哲学中是可行的。本书在多个地方讨论了他这一论证。第八章提出西方关于人道和仪式的问题——他们如何看待无意识的动机和价值?此章发展了弗洛伊德的解读和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总的来说,这些儒家价值观(以及许多其他中国思想中的价值观)需要去除单纯作为文化传播的“第一纯真” ,并通过怀疑大师的思想重新进行思考。这一章延续了现代儒家内部性理论的发展。
本书有三章集中探讨了比较问题,第九章是其中之一。本章源自为纪念已故秦家懿教授的会议而做的主题演讲,主要讨论了儒教与基督教关系问题。秦教授或许是我们当中研究这两种宗教传统之间持续的历史关联的最杰出学者了。罗马天主教神学家汉斯·昆与她有过合作,那次会议上他也发表了主题演讲。此章重点是今日两种传统如何相互增益,这对实践二者的人来说,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这个论辩关乎现实政治,旨在提出一种“儒耶合璧”的替代性方案,以对抗美国政府与基地组织所共持的先发制人的战争逻辑。
第十章处理的问题是,依中西传统,对终极者的设想是以位格性的还是非位格性的方式。我认为每一个传统都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导致它可以同时处理位格性和非位格性的描述。
第十一章专门讨论比较问题。首先讨论的是比较神学问题,其中对终极者的关注,最为重要且挥之不去的元问题是一个思想家是否需要归属多个传统,才能对其进行比较;比较神学与宗教实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继而,本章区分了比较哲学的两种范式(此范式划分亦适用于比较神学):一是描述性或客观主义比较,二是规范主义比较。后者试图在相互比较的传统中厘定何为真知与价值。最终,本书主张超越单纯比较(即便是规范性比较),迈向综合哲学之境。综合哲学具有建构性特质,故该论证对我自身的研究计划至关重要,亦期冀能激励当代学人将中国哲学视为重要思想资源。
第十二章总结了前面各章的主题,将其视为将来在与其他传统的关系中发展儒家传统的任务。
如我这般突破正规教育学科藩篱的思想者,其学术惠泽之浩瀚难计,诚可谓数不胜数。感谢所有的老师和学生,书中涉及的亲密朋友,以及那些不曾谋面,但直接从事汉学研究,以使我的工作成为可能的作者。我向年轻一代学者致敬,他们在整个受教育过程中,一直为比较工作做准备,这对我们这一代的学者来说,几乎不可能。我尤其要感谢波士顿大学的同事白诗朗,十五年间,我们共事于该校神学院管理层,但更深层的协作在于共同开创一种融汇中西的智识生活。我们携手推动波士顿儒学之“查尔斯河南岸学派”(杜维明领导之“北岸学派”则重孟子而轻荀子)的构建。多年前,当白诗朗担任加拿大联合教会跨信仰事务专员一职时,他便向我证明:人可同时恪守道德操守与胜任体制职务。此双重可能性,恰是吾等心向往之的儒家士大夫理想之必需。谨以此书敬献于他。
来源:西北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