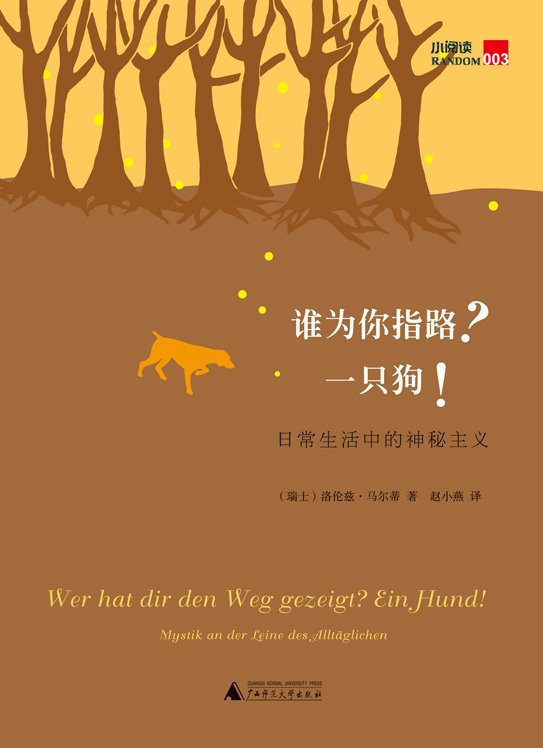
启程
怎么恰恰是只狗!——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用一只狗来命名自己的作品。这是一本关于神秘主义的书。但狗并不是这本书中的主人公,它只是一个次要角色。它在其中一个章节中出现了三次,而后又消失了。它并没什么特别,而这也正是它的特别之处。
狗代表了许多我每天都会遇到的事物,这些事物看上去如此熟悉,以至于我对它们几乎无所察觉。而“熟悉”是一种标签,仅此而已。被我贴上标签的东西,我很少去注视它们——我是说认出它们。它们无法引起我的兴趣。
但标签却遮蔽了事物最重要的本质。把标签拿开,我可能会有惊奇的发现。看上去如此熟悉的东西甚至变得有些陌生。原来我只是没有仔细去注视。我观察的时间越长,越深入,发现的就越多。再没有什么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我不禁感到惊奇,而惊奇正是通往神秘主义的一扇重要的大门,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
神秘主义,它是这样一种感觉:一切我通过感官所感受到的东西都蕴含着神秘。我无法说清那是什么,但却能感受到它。它是一种隐匿的终极真相,包含和渗透了一切事物,让世界充满生机;就像艾辛多夫(Eichendorff)那首著名的诗所写的,它是沉睡于所有事物中的一首歌谣;它是存在于所有一切的宏大关联。
神秘主义与一首诗、一支歌一样,你永远也无法解释它。在分析者的解剖刀下,它会变得支离破碎。
但你可以追寻它的味道。
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个。在七十次外出散步的途中,我将日常经验与来自神秘主义哲学的心得相联系。这书中的“散步”既是字面意义上的,也是一种比喻:思想也在漫步。每走一步,世界就变得有些不一样。
一条田野上的小路在讲述着故事;一棵树在庄严布道;鹅卵石变成了闪闪发亮的钻石;一条公路成为人生幸福的试金石。
漫步在一座城市的喧嚣中,是一堂冥想的功课;一扇窗让人认识了自我;轻轻飘落到繁忙都市中的雨滴,赐人以信念和希望。
在路上我和另外一些人相遇:一位挡住我去路的年老妇人,教给慌忙的赶路人如何观看的艺术;一位理发师在主持一场仪式;一位神学家在制作一张花园长凳;一位宗教改革家在驱赶麻雀。
路上还出现了很多动物:透过一头牛的眼镜,宇宙直视着散步者;一只讨厌的苍蝇原来竟是大自然的神奇杰作,而一只口渴的狗成为启迪人类心智的老师。
在劳作的小径上,工作的压力和时间的紧迫在威胁着灵魂的安宁。对此,一位年老的僧人知道如何给出建议。甚至一台发出轰鸣的吸尘器,只要你给它取一个合适的名字,它也能教你学会安静。
最后,乘火车的旅行让旅行者明白了,时间具有怎样的相对性,而生活则很少遵循时刻表上的安排。
这七十次的外出散步终止于一处边界。一次不愉快的相遇引人深思,带来领悟。老子飘然离去。在所有的相遇中,都能感觉到一缕无拘无束的自由气息。
散步活动与一种轻盈相联系。这种轻盈让人可以用轻松自在的方式思考那些严肃的问题,它消除了不安和紧张,开启了新的视野。
德文中的“散步”(spazieren)一词来自意大利语spaziare,意为“舒展”。散步创造空间,它拓展人的思维,以及心灵。
而最后,催人上路的,往往是对辽远的渴望。
第一章真理就在脚下
世界上有一条路,除了你,谁都不能走。
这条路通向何方?
不要问,去走吧!——弗里德里希•尼采
走,只是走
散步,在现今这个人人疲于奔命的社会中,是一件奢侈甚至近于放肆的事情。谁在闲逛,就证明他或她有时间自由支配自己的双腿。其实,散步的人很少想证明什么,他们只想随便走走。走,不过是因为有了行走的愿望。
没有预先设定的步伐,方向和速度都可能随时改变。与此同时绕道而行也被欣然接受,有时这正是人们想要的。笔直的道路未必总是最好的选择。
行走的人,避开了高速公路上沉思者的洪流,那些只想快速高效从A到B的人,将世界视为流动的快速消逝的背景。缓慢地行走,邀请你停下来,观赏、沉思和冥想。
行走的人并不比别人拥有更多的时间,但是他们有别于其他人的行走,使他们不像他人那样,在时间面前疲于奔命。他们摆脱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们给自己自由。他们不必节约时间,也无惧时间的流逝。没有什么能束缚他们,也没有什么能驱赶他们。他们在自由的时间里行走。一步一步,加速走向当下的幸福。
行走是音乐。莫扎特深谙此道,当他想要作曲时,他就去散步。然后音符就这样飞向他,回到家后他就把在路上听到的音符记录下来。
行走意味着:离别和新的开始。每一步都是离开一个地方找寻另一个新的目标。而新的目标一旦被找到,就又要被放弃。没有什么是静止的,一切都在改变,一切都在过去。行走和过去不是理论,而是可以触及、可以经历的真实。行走是生命中的图画和象征。
许多顿悟的思想家都曾徒步走在路上,这与缺少交通工具并无关系。他们的游历就是他们理论的一部分。佛陀抛弃了双亲皇宫里舒适的生活,转向居无定所的漫游。亚伯拉罕追随他听到的召唤声,不理会他的旅途将去往何方。摩西与以色列的民众经过数十年长途跋涉穿越了沙漠。就连耶稣也没有固定的居所,他的家就是巴勒斯坦尘土飞扬的道路。
对于他们的继任者,如此频繁的流动性往往是种苛求。游历的智慧被紧锁在围墙高筑的教学楼内,围墙提供了保护和安全感,隔绝了批评家和敌人的攻击。漫游者开放的思想随着岁月的流逝所剩无几,却从不曾消逝。它继续活在传统主义者的心中,并被发扬光大。
一条路的存在是以人们的行走为前提,否则它将荒草丛生,不复存在。行走的人在跟随前人脚步的同时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足迹又引导着后来的人。行走连接起了步行路上的古人和来者。路,是穿越时间空间伟大运动的一部分。它运动在一条河流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有它自己律动的节奏。
路,接受所有想踏上它的人。它不问来者的姓名、出身和职业。它让所有的人行走。也许,它也会对步行者或徒步的女人低吟几句波斯神秘主义者鲁米(Rumi)的诗:
来吧,来吧,不论你是谁。
漫游的人,追寻的人,全都没关系。原诗为:惊奇的人,崇拜者,离去的爱人。
这不是绝望的旅队。
来吧,即使你已经打破了自己的誓言,一千次。
来吧,再一次,来吧。
田间小路上的哲学家
道路会讲故事。就连公路、小巷和人行道也会讲故事。但最美的故事却是由田间小路来讲述的。它自己就是一个传奇。许多的足迹被深埋于此。它保护自己不被盖上沥青的大衣。它敞开胸怀,像接纳踏上它的人们一样,接纳狂风暴雨。
田间小路低声轻语,为了听到它的吟唱,人们必须聚精会神地行走。它阐述了生命的变迁:从费力的上坡到轻松的下坡;从笔直的、一览无余的一段路到被转弯遮蔽的路途;从冬天的萧瑟到夏天的丰富;从春天的苏醒到秋天的枯萎;从不被持续变化的外界环境影响的宁静,到高度纷繁的世界中简单的小幸福。
这些深深影响了一位哲学家。这位哲学家是19世纪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马丁•海德格尔。他在其主要作品中,提出了对受死亡限制的时间里存在的思考。这本书中的语言是那样特殊和神秘,以至于只有很少人能理解他的意思。
与此相反,海德格尔将一本小的著作献给了一条普通的田间小路:这本小书有着一种简单朴素之美,这是对“朴素的不竭动力”唯一的赞扬,是哲学家在田间小道的发现。谁置这种朴素于不顾,就是放弃了很多。
海德格尔常常徒步走在路上。行走对他来说是一种沉思练习。当他迷失在存在与时间的谜题中时,田间小道为他提供了避难所。
在田间小路上,海德格尔的思想随着脚下的步伐慢慢延展。他用笔来耕耘,而相比于此,一个农夫的脚步是在清晨走往收割的路上。与土地的联系理清了思绪。从容不迫的步伐带来的规律性使人沉静。
哲学家默默地走在路上。他觉得自己融入了行走路上的风景。而这风景又与他的思想产生了共鸣。在行走中,他体会到了一种广袤。这广袤不被山丘和森林所限制,“所有围绕在田间小道成长中事物的广袤,都献给了世界”。
海德格尔在弗莱堡一间孤独的农舍里几乎度过了他的一生。事实上他从未真正出游过。他只是通过散步来认识世界。从平凡中发现了伟大短暂中的存在,时间里的永恒。
无论是第一朵吐露了新生命幸福的鲜花,还是夏日清晨高飞的云雀,抑或是雾霾笼罩的山丘——海德格尔总是在不断倾听田间小路对他的轻吟。这些轻吟鼓舞了他的信心。如同哲学家用他独特的语言所写的,他对一切“充满喜悦”。而这深邃的喜悦对他而言,是一扇通向永恒的大门。
那么今天呢?
许多小路被沥青覆盖或者扩建成公路。田间小路的轻吟逐渐消失在噪音里,它沉静的力量也渐渐削弱了。海德格尔曾经预言和担忧过,人们会因此而“心不在焉,迷失方向”。
但是那些古老的,蜿蜒交织在一起的小路,与它们的故事依旧存在。只是需要人们花些时间去寻找,去倾听。然后它会突然又在耳畔响起,那些独特的低吟声,那些带来希望和喜悦的声音。
树木是最好的传道士
当我被俗事烦扰的时候,我喜欢逃往林中。树林提供给了人们保护和包容。它们就像是一座座教堂,人们轻轻走进去,沉默不语。暮色将至,空气潮湿。树木巍峨而庄严地挺立着,见证着逝去的岁月。当外界的喧嚣被屏蔽,在树荫遮掩的半明半暗中,林中的漫游者似乎碰触到了永恒的真谛。
对于宇宙论者布莱恩•斯威姆来说,森林是圣地:“当你踏入森林,在学会向包围着你的无限空间战栗之前,你将永远不能离开这里。自我,在走进森林后,将很快不存在,因为你将会是全新的;你会携带森林的气息。”
这话听上去充满了希望。虽然我从未在林中迷失自我,并且不论我离开的时候是不是有了新生,我总是敢于怀疑。但是每一次我确实有了一些不同。在我踏入森林的时候,面对的那些庄严古老的树木似乎只成了背景,它们变得不再重要,甚至有一刻我已经忘记了它们。这宁静和黑暗创造了一种安全的氛围。能在这里,是多么美妙。
很多树木十年来都生长在同一个地方。从白天到夜晚,从夏天到冬天。在这个总是躁动不安的世界里,它们带来了宁静,令人愉悦。
尽管它们有着坚强的耐力,大多数的树木却并不僵硬,否则他们将会被狂风吹断。相反,它们用一定的柔韧性保护自己。它们随着四季的交替改变自己,如同生命的进程。但这种改变缓慢而无声无息。并且在经历了所有的改变后它们依旧保持自我。
树木是个人主义者。每棵树只代表自己,每一棵看上去都与众不同。同时每棵树都与它生长的环境有着深层的交流:它的根为它提供了土壤中的水和养料,树叶为它交换氧气、二氧化碳和水蒸气,阳光带给它生长必需的能量。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之间建立了高度的独立性和对周围环境的坦诚的联系。这一点,人类只能学习。
树根深埋在地下,为树木提供了支持和稳固性,使它能够生长。树枝伸向天空,承载着树叶和果实。这是向上的,向着光明的运动;同时也是向下的,向着黑暗地下的运动。所有的生长总是包含了衰败和死亡:每逢秋天来临,树木聚敛能量,树叶凋零。然而每次死亡却也预示着新生命的来临:深秋的时候,树木孕育着新的芽苞,到了春天就生长成树叶。
如同田间小道,树也会讲故事。这是夏天的幸福与冬天的寒冷,春风的温柔与秋风的狂暴的故事;是受伤及愈合,危害与希望的故事。“对我而言,树木总是最令人信服的传道士,”赫尔曼•黑塞宣布,“谁对它们倾诉,谁知道去倾听它们,就能获取真理。”真理在黑塞看来就是每棵树为了实现自己生长的法则都有自己的形态,“用显著的唯一性去表现永恒”。
树木的传道不用语言。它们只是静静站在那里,忠告着,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当我离开树林,也许,我已经不同于之前踏进林中的我了。我的身上有了某种改变,即使连我自己也不清楚,这变化是什么以及我该如何承认这种变化。树林保守了这个秘密。
云往何处去
步,可以在任何天气进行。晴朗的天气,万里无云,到处充满阳光,吸引了许多人去户外。在雷雨、下雪、刮风的天气散步的人通常独行在路上。大多数时候天气不好也不坏,有太阳也有云,有时还有云带来的雨。
作为步行者,人们必须准备好相应的装备。因此就有了天气预报。在最近几年,天气预报变得越来越详细。从前媒体满足于对今明两天天气的提示,如今它们提供给我们整个星期的天气预报。气象学家声称知道接下来的几天是什么天气。他们给世界一个印象,天气可以预知,天气预报是准确可靠的。这种安全感在我们这个不安全的时代当然是好事。
以前人们为了预知未来,去祭司那里。今天的祭司——收音机和电视机登堂入室,用两三分钟举行它们气象学的弥撒,然后预示上天的旨意。他们开朗热闹的聊天语气即便在最糟糕的预报中也能让人心平气和。就好像一切都再正常不过,即使几天来的天气总是阴冷多雨。
这些天气预报员有着能够治疗心灵的音质。他们知道,我们不喜欢坏天气;当气压下降的时候,他们好像在和我们一起承受痛苦。反之,在他们宣布高气压的时候,他们愉快得不能再愉快了。他们和我们同甘共苦,是多么好的灵魂陪伴者啊!
他们激发了人们的信心,即使他们频繁犯错。他们的预测让人觉得可靠,虽然人们不能总是指望他们。因为云总是我行我素,飘向它们想去的地方。
天气是一个混沌系统的最好例证,就算有一定的可靠性它也还是如此。因为有太多的因素参与其中,互相影响,这使得准确的预报在许多情况下变得尤为困难。
混沌系统的研究者对于他们的发言都很谨慎。他们讲究的是可能性、概率和偶然。
当然天气的大祭司们不允许用这些论证,毕竟人们是要求个安心。
在最恰当的时刻带一把雨伞。
即使有再英明的计划,出门的人也可能会被淋湿。就像意第绪语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Scholem Aleichem)讲述的一个精彩的悖论——它同时也是个有点混乱的故事:
两个男人走在路上,这时天上开始下雨。
一个带着伞,另一个没有。
“为什么你不打开你的伞?”没有伞的人问道。
“不管用。”另一个回答道,“伞上有洞。”
“那你为什么还带着它?”
“我以为不会下雨呢。”
不带拐杖上路
嗒、嗒、嗒,当我在路上听到这种噪声时,我知道,此时有人正拄着两只登山杖徒步跋涉。这项运动叫北欧式行走,在如今非常流行。总是有很多身体健康的男男女女,拄着双杖走在路上。
这让我联想到一个苏菲主义者苏菲主义:一种伊斯兰的泛神论神秘主义。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由一个老者讲述的,这位老人有一次摔断了腿,只能拄着双拐走路。当时他发现这两只拐杖真是有用极了,它们不仅能帮助他走路,还能让他扫清脚下的障碍物或者赶走咬人的野狗。没人的时候,他还能用一只拐杖偷偷去敲邻居树上的果子。
这位老人非常振奋,当他的腿痊愈了以后,他仍旧保留着这两根拐杖。后来他的妻子、孩子和孙子也都拄着拐杖走路。很快,这种新的走路方式在村子里流传开来,最后甚至遍及全国。渐渐地还出现了各种各样颜色和形状的拐杖,专业的拐杖学家也应运而生,他们教授他人如何使用拐杖走路。
很多年后的一天,一些人甩开了拐杖。他们发现,没有陌生的辅助工具,人们也一样能行走自如。但是没人相信他们。很多人嘲笑这些拐杖否定论者,还有一些人摆出侮辱的手势对他们破口大骂。最后这些叛变者被以捣乱正常秩序的罪名而关进了监狱。因为那么多人都坚信拐杖是人的一部分。
到这里故事就结束了。一个悲伤的结局。我不认为北欧式行走的影响只有这么大。其他类型的拐杖也引起了我很多深思:比如手机,几乎没有人能离得开它,没有它,什么事也办不了;汽车,这种带着四个轮子、不断排放噪音和废气的拐杖;或者互联网(什么?别告诉我你没有上过网)。
拐杖也是顽固的想法和一种偏见的意识形态,它取代了自由独立的思想形式。人们支持那些所谓的权威思想,只是为了不必独立思考。
苏菲主义者之所以讲这个故事,是因为他们热爱自由胜过其他一切。如同其他许多神秘主义者一样,他们不想受到任何人、任何事的束缚。他们行动自由并且不惧打破常规——当这些规定变成行动的镣铐时。“学校和寺院的塔应该被推倒在地,碾为齑粉,”苏菲主义宗师伊德里斯•沙阿(Idris Shah)解释并补充道,“直到信仰变成否定,否定变成信仰之前,没有真正的穆斯林。”
上面的话是一种挑衅,对于拐杖的追随者来说这有些骇人听闻的意味。他们看到自己赖以信仰的基础摇摇欲坠,而事实上在此被推翻的只是一种原教旨主义。
同时,苏菲主义者并没有断然拒绝拐杖。作为暂时的辅助工具,拐杖自有它的合理性。它们帮助腿上负伤的人迈出第一步。但是当这个人伤腿痊愈、能够独立行走的时候,他仍旧紧握双拐不放,这时他便付出了自由的代价,他一点一点地遗失了自己的独立性。
苏菲主义者也是这样理解所有的教条、形式、学院和权威的:这些都只是帮手,在合适的时间必须被再次抛弃。因为自由就是:用自己双脚独立行走。
嗒、嗒、嗒,前面又走来一个拄着双拐的步行者。我应该对他表示赞赏、嘲笑,还是同情呢?
什么都不是,我说了声“日安!”,然后低头继续走我的路。
来源:广西师大出版社2012.12.12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