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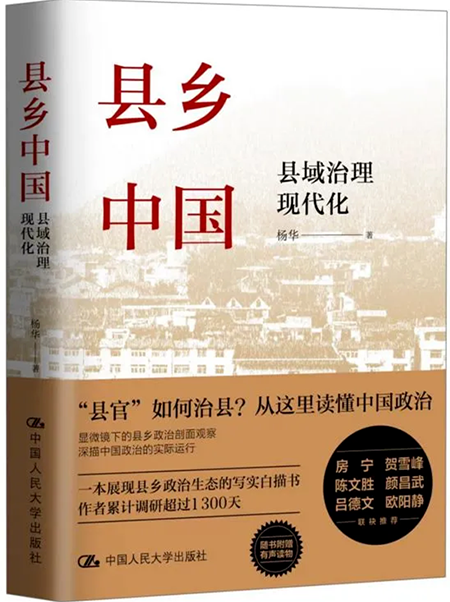
本文作者
杨华(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2021年8月末,我把一些县乡治理随笔依据县乡政策落地的主题汇编成一本约25万字的集子。贺雪峰老师看后认为很有出版价值,且应尽快出版,让我联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任晓霞老师。
任晓霞老师多年以前曾与我一同参加过在四川绵竹农村的集体调研。她毕业后,多年来一直从事编辑工作,与我们团队联系颇多。我跟任老师联系,和她提到有一本关于县乡治理的随笔集,想请她评估是否具备出版价值。起初我还担忧,因为这是随笔集而非专著,乍听之下里面可能有一些敏感内容,这或许会让她感到棘手。然而,她拿到集子没过几天就联系我,说这本集子很有出版价值,这使我对于这部集子的面世增添了信心。
《县乡中国》选题在出版社通过后,我们便展开了长时段合作。书稿整理阶段,任晓霞老师从编辑角度,就书稿的目录、可读性等提了一些建议,我们讨论达成了共识。后我花了一些时间对书稿进行修改与整理,再将其发送给她。书稿进入编校流程后,她和我就书稿的体例、文字、内容、书名、序言、宣传文案、推荐语等方面展开了频繁互动。
确定书名颇费周折,我传给她时暂名为《大国县治2:县乡体制》,不符合出版社的标准。任晓霞和我都拟定了十多个书名,两人反复商讨,都觉得不太满意。之后我的朋友提出了《县官与现管》这个书名,任晓霞觉得这个书名可作为主标题,但还需一个副标题来呈现书的主要内容。后来给出的意见是《县官与现管:县域治理现代化》。但又觉得“县官与现管”不很妥帖,人大社编辑团队和营销团队经过充分讨论,最终确定书名为《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这个书名虽平常却有独特之处:县乡既是中国社会的底色,也是中国基层治理的基础,用县乡中国作书名简洁明了,且富于想象空间。
书的宣传工作是琐碎而又漫长的。王海龙老师和任晓霞老师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营销团队,一起把《县乡中国》的宣传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度,使《县乡中国》在学界、政界和社会各界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鉴于《县乡中国》出版后市场反响良好,我便将编著的《县乡的孩子们》书稿交给了任晓霞老师。这本书是业内首部关于县乡教育的经验之作,主题关乎众多县乡孩子在起跑线上的公平问题,备受社会关注,且为纯经验作品,可读性颇强。《县乡的孩子们》问世后,虽未如《县乡中国》那般热销,但在学术领域有一定影响,我在多个教育学的学术论坛上听到发言人提及此书。
两本书的出版历程,宛如一场“学术马拉松”:从《县乡中国》框架的调整,至《县乡的孩子们》案例的补充,任晓霞老师一直同我携手同行。身为作者,我深知要将一部仅有粗略逻辑、由调研随笔汇编而成的书稿,打造成一部在读者眼中不杂乱、非随意堆砌且具备体系性与整体性的“专著”,会耗费编辑团队无数的心思与精力。任晓霞老师作为《县乡中国》的策划编辑,以近乎严苛的专业态度投入书稿的打磨工作,其修改意见常精准到标点符号。她逐句斟酌术语的准确性,甚至对田野调查里的细节反复查证。多少次她在凌晨发来微信询问书稿中表格数据的来源、案例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在《县乡的孩子们》里,她对“留守儿童”章节格外用心,使学术研究更富人文温度。人大社的团队,从封面设计到宣传策略,旨在让“好书走进读者内心”,“被更多人看见”,也促使我重新思考学术表达的公共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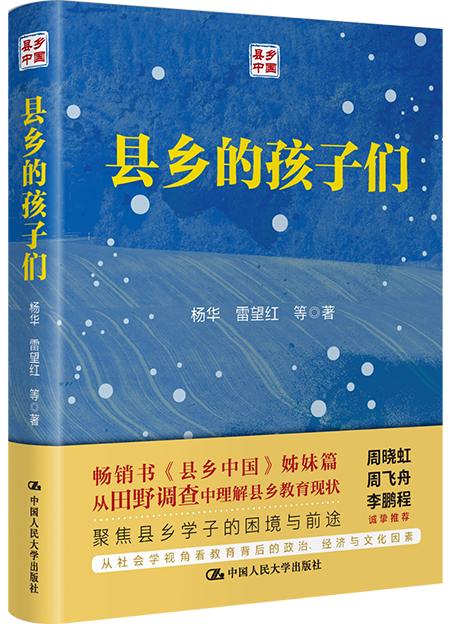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老师们,凭借专业和热忱,在大众与学界之间搭建桥梁,让曾经局囿于象牙塔的县域研究迈向公众视野。每一场推广、每一次校对,都是对思想的再度打磨与阐释。我时常思索,一本佳作的问世,从来不是作者一人的功绩,而是作者与出版人共同孕育的成果。正因为有这样的同行者,学术才得以步出书斋,与现实交流,与时代共鸣。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年代,能沉下心来雕琢一部真正有深度的学术作品实在难得。他们以专业为笔,以责任为墨,书写着出版人的使命。一部部厚重的著作,由此焕发活力,延展至课堂、田野以及公共讨论之中。这种幕后的辛勤劳作,或许不常为人所见,却一直支撑着思想的传播与知识的延续。他们的工作,是让思想穿透纸张,触及更广大的人群。每一场策划,每一次修改,都在默默彰显着出版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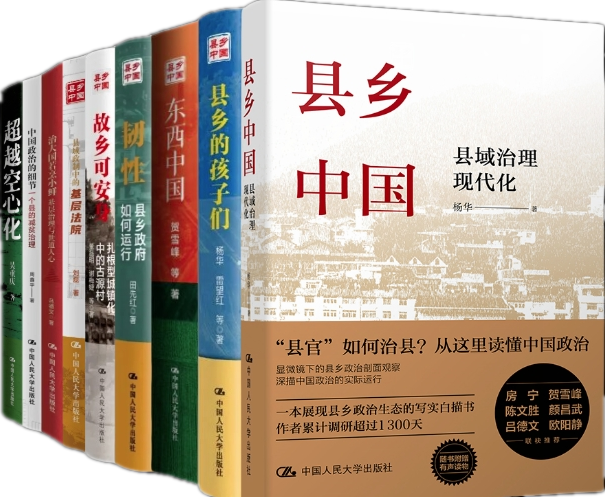
县乡中国书系
正值人大社70周年社庆之际,我想对人大社的老师们表达感谢:是你们让《县乡中国》从单本书延伸为“县乡中国书系”,把学术成果打造成图书精品,使其从书斋迈向公共领域,实现了学术的社会价值。期盼未来与你们继续同行,书写中国县乡的深刻变迁。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