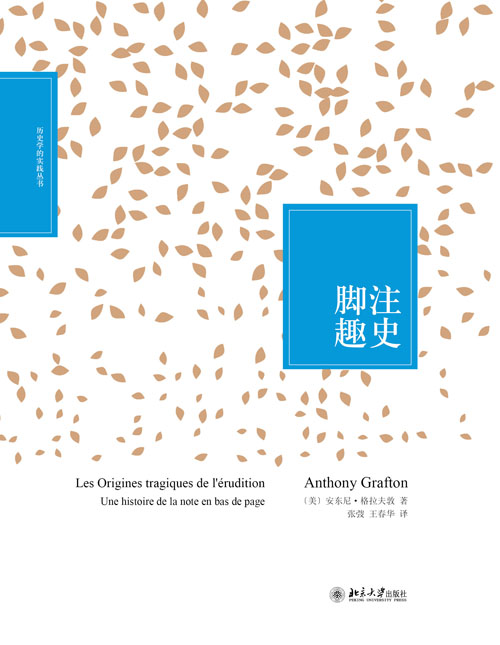
《脚注趣史》((美)安东尼·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是部很有意思的书,它在网络上被讨论了很久直至晚近才被译成出版,它研究的是脚注却使用了附于每章末尾的尾注。
此书作者说:“史学的脚注和传统的注疏在形式上类似”。这里所谓“形式”,应该就是指所谓注文置于同一页这个特点。我们去看中世纪留存下来的古籍手稿,比如10世纪的威尼斯《伊利亚特》会注残卷A本,正文会以大字誊抄在纸页的正中一侧,各家注疏文字则以略小的字体写在另一侧及上下部分。
段玉裁判断最初的注、疏都是另外成书的,后来的中国学者则喜欢夹注旁批,手写时可能也是写在页边的,经注合刊时就变成行间注,意义似乎在于使得注疏紧跟正文,但这样会妨碍阅读正文的进程。
过去的汉籍中相当于脚注的是作者自注,或以“按”或“案”来标识。西学东渐,我们在这“形式”上也学了人家,注疏和脚注都变得与正文脱离了。这“形式”上的变化也反映了“内涵”上的分别:注紧跟正文,有主观上遵从的态度;注与正文分离则是客观理性的表现。
西方古代学术中文献校理也是注疏家常做的事情,他们一开始就在怀疑荷马史诗哪几句是后人伪造的,哪几句顺序可能颠倒了,或是哪几个字可能写错了。这和强调“注不驳经,疏不破注”是不一样的,疑古态度较晚才在中国学界出现。而严格意义上的脚注的使用,明显是在近代中国才出现的。1980年代的中国,不少青年学者通篇无注或是引用未曾标注出处的文字,在辩护者口中,反成为思想解放、元气淋漓的表现。
著作家、学问家在脚注中节外生枝的评论和考证,除了体现对现实问题的关怀,也是新见解的萌生点、新思想的试验田,这可以减少正文的摇曳芜蔓,而又保证义理上的丰富和实证上的细致。而黑格尔、蒙森,则反对著作中填充庞大脚注,作者评论说,他们“隐匿了在文献方面的雄心,避免了在展示自己所汲取之学识这种费劲的事情上疲于奔命”。在启蒙运动末期,英国文士对于博学文体的讽刺与消遣,其实都是缘于脚注已经成为流行时尚这一事实。藏书的丰富、档案馆的繁荣,工业化时代产品说明书的详尽,都似乎使得博学丰富的脚注变成容易的流俗之事——更何况如今的数字时代、大数据时代,更将罗列繁复细致的考证根据推进到一个超乎想象的地步。
那么,脚注的趣史如何续写?或者说,思想学术书如何在今天发挥脚注曾有的人文风度?我们恰好可以从追求穷尽材料证据的方向上暂停脚步,注意一下脚注的论述文体,以及它与正文间在修辞效果上的呼应关系。本书作者在结语中说起现代历史学在叙事形式和史料、问题、方法之间寻求融贯的修辞学尝试:这是“类似于佩涅罗珀的编织艺术”。换言之,我们并不追求天衣无缝或者看似无懈可击的学术生产,而是把治学与著述看成是一门艺术创造,这关乎个人心智、品性与情怀,而不是一种制度或形式所可以匡范局限的。学术历史的魅力在于有人去做薪尽火传的事业,脚注应该提供这个帮助,而不是令人望而止。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