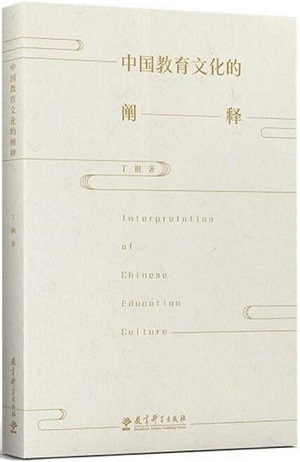
教育活动作为文化传递与创造的核心,本质上呈现为一种教育文化现象。教育文化研究是将教育作为深层的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教育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内在联系,强调教育活动的文化内涵和实践功用,并呈现教育文化实践的多元形态与丰富内涵。
对于中国教育文化的考察,首先必然涉及什么叫传统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无论中外都有着许多不同的阐释,但如果从共性的认识来看,有一点是比较一致的,这就是在广义上都肯定传统是指历史上形成的东西。我们讨论教育文化传统,也是从历史出发的。
我们关注教育文化传统的多元形态与丰富内涵,这对如何正确地评价教育文化传统的价值以及如何阐释它尤为重要。
人们往往习惯于把儒家教育与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等同起来,大多是依据中国自汉代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使儒家教育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正统教育的主流这种认识。的确,由于中国宗法社会的早熟,儒家所提倡的等级划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伦理构想,以及在这基础上形成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在中国教育文化传统中占据着主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实际上,孔子的教育思想不等同于孟、荀的教育思想,孟、荀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包含有对孔子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发展与改造,比如孔子重视礼乐教育而反对法制,而荀子在发展礼乐教育的基础上把礼法加以统一,提出了礼法并用的教育思想。到了汉代,汉儒更是吸收法家与道家的某些思想,对儒家教育思想进行了改造,形成了一个以儒家教育思想为主干、兼容诸家的教育体系。如果再往前追溯,早在汉代之前,不仅儒家主动吸取其他诸家的合理思想,而且像法家人物管仲、韩非等以及道家人物田骈等,都对儒家的教育思想加以汲取而使各自流派成为后世儒家发展的重要参照系。《吕氏春秋》庞杂的教育体系的形成,正是早期诸家争鸣融合的结果。因此,汉代虽说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但事实上此时的“儒术”已融百家为一体,已非孔子儒学的本来面貌。不仅孔子不等于儒家,即使是后来发展出来的程、朱、陆、王等这些被视为圣人的硕儒大师也不可能作为整个儒家的代表。柳宗元、刘禹锡、王夫之等被统治阶层加以排斥的非正统派人士,对中国教育文化传统的贡献亦是不容忽视的。
而且,儒家教育文化传统(已经整合起来的)本身也不能涵盖整个中国教育文化传统。因为除了儒家教育文化传统以外,中国还存在着墨、道、法等诸家的教育文化传统。例如,在魏晋南北朝时以自然主义教育为特征的道家教育文化传统,相对于正统的儒家教育文化传统,形成了重自然、轻名教的玄学教育思潮,这对中国教育文化传统的发展是具有重大影响的。
中国历史上还存在着佛教和道教这两个相对独立而各具特色的宗教。如果说,儒家教育非常重视政治与道德方面的教育,那么佛教教育则侧重于人的内心修养和思想的熏陶,注意对人的心理以及思维方面的训练,而道教教育则更注重养身修行的教化。佛教与道教的教育目的虽然是宗教本位的,但在具体的教育中又有一些合理的东西。从宗教平等的观念出发,佛教教育还十分注意在寺院教育中的师生平等关系,最突出的一点便是“问难”。佛教重视游学,游学者无论游学至何处,均可与当地讲师互相诘难,如确实才思过人,学问高于当地讲师,还可替代其讲师地位。而道教教育十分重视养身修行,注重“外丹”“内丹”,其教育又具有浓重的科技教育的色彩。道教养身修行炼“外丹”是需要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与技术的,而“内丹”实为一种气功养生术,其中关于吐纳导引、经络学说等的传授,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科技教育的特色。因此,对于佛教和道教的教育必须做细致深入的研究。这种包裹于宗教神学之中的教育文化传统也应当成为中国教育文化传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考虑中国教育文化传统时,关于多民族的教育文化传统也不容忽视。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少民族有着自己较为系统完整的文化与教育文化传统。我们不能也无法忽视这些教育文化传统的事实存在,它们也必然是中国教育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教育文化传统的形成,从外部来讲,与不同地区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宗教、语言等有关,从内部而言,又与其教育体制、办学目的、教学内容与方法等相联系。对于诸如此类的教育文化传统,如果我们缺乏深入细致的把握与研究,那么今日的教育变革以及民族教育的现代化,就将因教育文化传统资源的缺乏而失去实际意义。
进一步讲,人们对于教育文化传统的认知,往往集中于那些已经制度化、系统化和已见诸书面文献的思想观念,而忽视那些蕴藏于民间的风尚习俗之中的非制度化、非系统化的教育行为方式。比如说,社会的生活方式、礼仪的遵从、行为的模仿以及知识的口耳相传等。古人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这就明确道出了中国古代教育的两个任务或两个方面:建设国家和管理公务,要以教育为最优先、最重要的事情;而要教化人民、形成良好的风俗习惯,必须从教育入手。前者比较容易认识,后者则涉及如何在风尚习俗的教化中推进教育。民间教育文化、教育方式所体现出来的教育文化传统往往被忽略。这正需要我们对中国教育文化传统有全面而深层的把握。
今天我们要经常不断地讨论教育文化传统的问题,有着非常现实的思考,也即背景与动因: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教育文化传统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从发展的角度看,现代化是在传统的背景下起步的,并且在具有一定文化传统的社会中发展,所以现代化总是与一定的教育文化传统相关的。可以说,现代化既是现实的,同时又是一种积累、传递和发展。简言之,它是一种历史与现代的共存,并且指向未来。正如传统并非一成不变的,教育文化传统本身也经历着不断的选择、批判、改造,我们今天对于传统的选择、批判与改造本身也是在发展传统,从而构成了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从这一意义来看,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教育现代化建设恰恰是传统的延续。我们研究教育文化传统的目的也不仅仅是保存它,而是改造它、发展它,使其适应今天的需要,因为“过去的文化既不可一概否定,也不应一味地赞美。不论我们如何想唾弃它,而它也是同现代有着血肉的联系;另一方面,不论我们如何想赞美它,而它已经不能按照原来的样子复活”。这就需要我们对于中国教育文化进行理解与阐释。
谈到阐释,又必然涉及阐释的对象,这阐释的对象就是历史上影响至今的教育文化传统。我们要理解教育文化传统对今天的现实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作用与意义,就离不开对于教育文化传统的阐释。对于教育文化传统如何做出全面与真实的阐释,仍是我们今天反思传统与变革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教育文化传统不仅具有外在的时代根据,而且具有其内在的理论价值。这就是说,它不仅提供了某种特定时代的特定知识思想体系,而且提供了某种关于教育本质认识的智慧。这种智慧包含着对于教育的深刻洞见以及合乎人性发展的真理性认识,并且蕴藏着许多有待充分展开的合理因素。
譬如,中国教育有着重视道德教育的传统。这一传统具体通过对于仁义与礼法关系的不同理解而展开。就其道德知识结构而言,其中许多概念与观点属于过去的道德教育范畴,但是,就其所提供的教育智慧来说,古代教育家对于道德认知、情感与意志方面的培养经验,对道德修养与人格完善关系的处理,以及把道德教育看成使个体社会化的重要途径来促进社会与个人的发展等方面的智慧,常常值得再三回味与探究。
又如,“孝”作为传统的美德,在古代社会得到充分的强调而构成道德教育内容之一,其与家长制及崇尚先人经验的认知方式等是相关联的,而现代社会要使之成为道德教育的一个内容,就需让其建立在今日的家庭形态与关系以及社会道德认知的基础上。
再如,儒家有着重视仁智统一、强调理性自觉的教育文化传统,要求人基于道德而保持理性上的自觉与修养。即使在现代社会,我们也必须承认培养一种道德自觉仍然是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则,儒家所提倡的“慎独”“内省”等方法,这同现代教育所强调的自律是相联系的。
对教育文化的阐释并不在于探寻规律,而是要探求意义,即采用理解的方法,从内心的理解出发去把握历史中教育文化行动的意义。运用阐释的方法解读教育文化,就必然要投入理解,并体现为一种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关怀。
伽达默尔说,“在精神科学里,我们的各种形式历史流传物尽管都成了探究的对象,但同时在它们中真理也得到了表述”,“对历史流传物的经验在根本上超越了它们中可被探究的东西。这种对历史流传物的经验不仅在历史批判所确定的意义上是真实的或不真实的——而且它经常地居间传达我们必须一起参与其中去获取的真理”。文本的意义并不是由作者的意图所决定的,“本文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
本书中对中国教育文化的阐释,其实更在意读者能够从自己的理解中得到感悟、启发。于是,阅读便成为一个追问的过程,是一种由理解者参与的阐释过程,也是一种力图从文本中发现其背后之意义的过程。
如果作者与读者共同成为理解与意义的建构者,那么,本书的目的就算达成了。
文章内容节选自《中国教育文化的阐释》一书,教育科学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 (订购)
来源:教育科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