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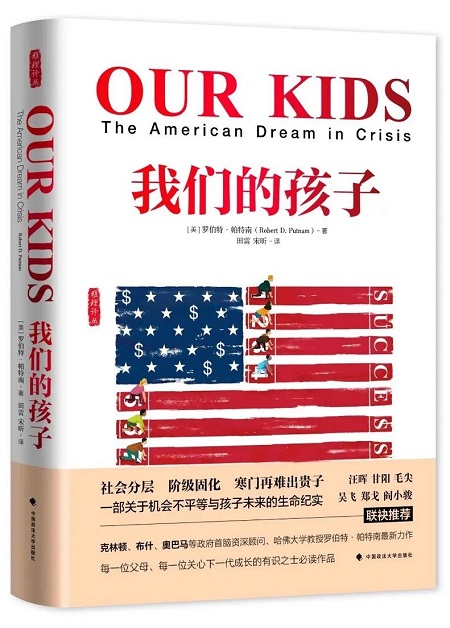
《我们的孩子》(订购)
[美] 罗伯特·D.帕特南 著
田雷、宋昕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学校:你的同学是谁,这很重要(一)
本章所探讨的核心问题如下:今日之美国,富孩子和穷孩子之间出现了与日俱增的阶级鸿沟,那么美国的学校到底是扩展了这种阶级对立,还是缩小了这种对立,抑或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伊莎贝拉和索菲亚有着完全不同的家庭出身,然后又读了完全不同的学校,那么学校教育到底是扩大还是缩小了他们当下存在的社会差距?说得更精确些,假设学校确实以某种方式牵涉到阶级分化,那么学校到底是阶级分化的成因(causes),还是仅仅为社会分化的场域(sites)?举目望去,关于当代美国学校教育的经验研究可谓汗牛充栋,那么这种类型的研究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学校到底是会固化,还是会缩小,抑或是加剧着美国社会的阶级差异,又是以哪些方式完成了前述的种种勾连?这些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但探究的过程也是发人深省的。
美国公立教育系统之创设,其出发点就是要给所有的孩子——无论他们的家庭出身——以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在过去的两百年中,公立教育系统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扩张和变革,每一次大转型都围绕着一种新的核心目标。
公立小学运动,发生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最终推动了免费公立初等教育的全民普及。霍利斯·曼(Horace Mann)是公立小学运动之父,这位美国历史上首位伟大的教育改革者曾经宣称:“教育,是推动人类生存状况平等的伟大手段,足以克服人在出身上的种种不平等。”
全面的中学教育运动,起始于1910年,终结于1940年,最终推动了公立中等教育的全民普及。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和劳伦斯·卡兹是研究这次变革的杰出学者,在她们看来,美国在20世纪之所以能够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兼得,公立中学教育的普及是其中源头性的推动力。
大学赠地运动,发轫于1862年至1890年间生效的《莫里尔法案》,其后又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所接续,整个运动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平民化奠定了基础。《莫里尔法案》的立法目的就经常被认为是“高等教育的民主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朝鲜战争结束后,政府为近八百万老兵提供了基本免费的高等教育,这些退伍军人在征召入伍前社会背景各异,此举也极大地扩展了进入大学读书的渠道。
上述公立教育运动的目标并不只是追求机会平等,举其要者,还包括发展国家的经济生产力和培育民主社会的公民。不仅如此,在民权运动之前的时代,这些教育改革虽然宣称奉行平等主义,但平等的羽翼却不庇护美国黑人。然而即便如此,若是得知当下的学校教育已经无力缩小学生的阶级差距,那么历史上的教育改革先贤无疑也会大失所望,而如果知悉学校实际上在扩大阶级差异,先贤们大概难免痛心疾首。
但从伊莎贝拉、罗拉和索菲亚的案例来看,她们的经验已然背弃了通过学校教育追求平等的愿望。那么,关于当今美国社会的阶级划分和学校教育之间的关系,现有的证据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呢?
让我们首先观察一下十二年义务教育系统内的学生分数。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肖恩·里尔登(Sean Reardon)曾完成过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一个结论: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孩子的数学和阅读考试成绩出现了越拉越大的阶级差距。事实上,里尔登的数据图表又是一个剪刀差的形状,在我们这本书中,各种数据指标一次又一次地呈现出阶级之间的剪刀差。里尔登精炼地概括了他的关键发现:“对比出生于2001年的孩子和出生于1976年(亦即25年前)的孩子,统计在两组孩子内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之间的成绩差距,则前者的数据要比后者高出大约30%到40%。”
大致上讲,富孩子和穷孩子之间的差距,对应着前者通常要比后者多接受数年的学校教育。不仅如此,一方面,存在于不同种族之间的族群差距一直以来都在缩小;但另一方面,这种阶级差距——即便是在每一种族内部——却持续扩大(我们此前也曾在其他指标上发现了相同的模型,比如非婚生子女的比例)。进入21世纪后,单是统计儿童的幼儿园入学率,阶级差距就已经比种族差距要高出2~3倍。
里尔登的研究发现已然令人心灰意冷,但更糟糕的是,他的具体研究只揭示了冰山之一角,与之相互呼应的还有大量有关儿童发育之阶级差距的研究,这里的发育不仅包括认知能力,还包括非认知性的情感能力指标。他的发现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他紧紧围绕着以考试成绩作为指标的学校学业,而学业则是人生道路上阶级差距的关键因素,比如大学毕业率、监禁率和成年后的收入,无一不和成绩有关联。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里尔登的分析还表明,学校教育自身并没有创造机会的阶级差距:早在孩子进入幼儿园时,机会差距就已经大到无可弥补,而根据他的研究,这种差距并没有随着孩子进入学校而发生显著的扩展。在检视了相关证据之后,詹姆斯·赫克曼这样写道:“如果我们观察18周岁的孩子,则其母亲的教育程度不同,孩子在认知能力的表现上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非常关键,因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人能上大学,而哪些人没有机会,但上述差距早在孩子6岁时就已经基本存在,换言之,在孩子上学之时,差距已经注定。我不否认美国的学校教育是不平等的,但无论是缩小还是加剧考试分数的差异,学校教育都只是配角。”
还有一些研究也强化了这种观点,即在加剧阶级之间的机会差距方面上,学校自身并不是主要动因。比如,有研究统计了小学学龄的儿童,即发现在孩子们离开学校的暑期,测试成绩的差距会加速扩展,而等到孩子们秋天返回课堂后,成绩差距就会稳定下来。换言之,在精英学校和底层学校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容否认的教育质量和资源的不平等,但只要我们还考虑到其他同学校无关的因素(诸如家庭结构、经济压力、父母参与甚至是看电视的时间),学校教育和资源本身就是相对微不足道的因素,在导致考试分数以及认知与社交技艺的阶级差距时,学校教育并非关键。
在本德镇、亚特兰大和橘子郡,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确实有学校老师主动对穷孩子伸出援手,拉平了竞争的场域。还记得乔在小学时的老师,曾牺牲她的午餐时间辅导乔读书;克莱拉和弗朗西斯科的老师也曾带着这对孪生姐弟参观迪斯尼,游览诺氏果园游乐场;凯拉的辅导员为她预约了牙医,支付了牙箍的费用,而图书馆的管理员则帮助她申请到了助学金;米歇尔也遇到了负责的老师,发现并帮助她克服了学习障碍;罗拉的一年级老师加西亚夫人,不仅“和善”,而且“风趣”;还有补习学校里“棒极了”的老师,帮助索菲亚完成了高中学业,还读了大学。当然还有悲凉的另一面,在圣安娜中学就没有老师愿意伸出援手,帮助穷孩子。
由是观之,似乎所有相关的研究——无论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都指向一个大方向:就美国社会日渐扩张的阶级鸿沟而言,学校教育没有过错,也不应负担责任,甚至学校反而可能是竞争平等化的推动者,若果真如此,教育改革的先贤们想必可以含笑于九泉了。但是——请注意,这是一个大写的“但是”——这绝非否认这一现实:在我们这个国家,富孩子上好学校,穷孩子上坏学校,两类学校之间存在着天差地别。如此看来,现实就同上述理念——即学校是无辜的旁观者,就美国当下愈发扩张的阶级鸿沟而言,学校既非主犯,甚至连帮凶都谈不上——产生了无法弥合的裂痕。通过对特洛伊和圣安娜中学的比较,基于阶级的教育隔离不容置否。而且学生身处其中潜移默化,影响力不可能不大:近来不断有定量研究发现,有钱人家的孩子上好学校,贫穷的同龄孩子上差学校,而在两类学校之间的学习成绩可谓天差地别。
那么,真相若果真如此,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最容易发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居住的贫富分隔。正如我们在克林顿港、本德镇、亚特兰大市或橘子郡所看到的,有钱的和没钱的美国人现在居住于相互隔离的邻里社区内,壁垒越来越森严。虽然并不是所有孩子都根据父母的居住地就近上学,但这确实是大多数孩子的选择。正是因此,我们可以说,过去30~40年间基于收入差距的居住分隔,已经将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分流到不同的学校。
但反讽的是,学校的教育质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日渐森严的居住隔离。原因很简单,当决定在何处购房时,大多数家长现在都看重周边学校的条件。即便是那些自身教育程度有限的家长,也同样如此,我们可别忘记亚特兰大的工人阶级母亲斯特芬妮。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当前都特别用心地为孩子挑选最优的学校,正如亚特兰大的西蒙娜和橘子郡的克莱拉,高知父母甚至是先择定学校,然后才举家搬入该学区。事实上,早在她们的孩子还未达到学龄时,西蒙娜和克莱拉就开始在学校之间货比三家,她们之所以选择现在的家,正是为了让孩子们可以就读于优秀的中学。
通常而言,上层阶级的父母消息通达,他们比中下阶级的父母更有渠道判断学校的教育质量,而且一旦做出判断,他们也更有能力去购买位于选定社区内的房子。布鲁金斯学会的乔纳森·罗斯威尔(Jonathan Rothwell)就发现,同样一栋房子,位置靠近重点公立中学就要比临近普通中学贵出不止20万美金。另有研究也发现,当家长们为位于好学区的房子竞价时,他们所竞取的是学区,这里生活着许许多多受过高等教育、高收入的家长,而不是学校,不是最好的教师素质、班级人数规模或单个学生的人均预算,这也就意味着,在父母看来,学生的家庭要比学校的投入更能决定学校的品质。(多年前,当我家搬到波士顿地区,要找一个有好学校的社区时,我太太运用了所谓的“牙箍检验法”——在一个地区内,到底有多少孩子戴牙箍?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指标,据此判断父母的收入以及关爱孩子的程度,也可以由此判断出学校的质量。)就是这样的过程,一方面让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幸运儿集中在一类学校内,如特洛伊高中;另一方面则让出生在穷人家的可怜孩子集中在另一类学校,如圣安娜高中。
“自主择校(school choice)”,允许家长跨越所居学区为子女选择学校,这一机制虽然一开始怀有美好的出发点,但对缩小阶级差距的效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从积极的方面看,确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进入他们父母所选择的学校,而不是所居学区的学校,目前这类自主择校生的比例大概在15%。但问题是,受困于信息不对称,家长经常无法作出明智的择校决策,不仅如此,孩子接送以及照管的问题也约束着家长的选择,这些问题在低收入家庭中间尤其普遍和严重。对于我们在本书重点关注的下层阶级的孩子来说,自主择校不太可能让他们的人生反败为胜。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并没有那种通情达理的父母可以帮助他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本文节选自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我们的孩子》。
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