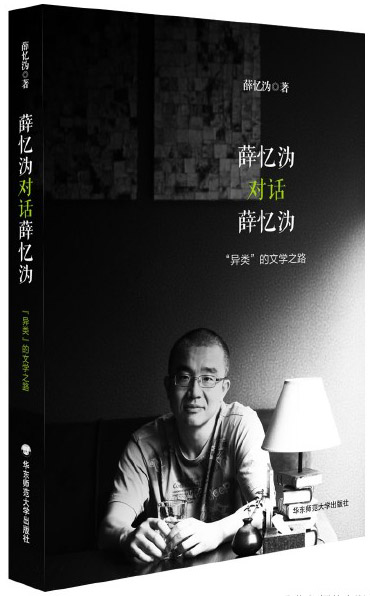
《薛忆沩对话薛忆沩—“异类”的文学之路》(订购),薛忆沩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版,39.80元。
《一个年代的副本》,薛忆沩著,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5月版,28.00元。
陈思旅 作家,北京
远离祖国,文学生命却得到惊人的激活—2002年移居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作家薛忆沩,近几年成为中国文坛“新锐的熟客”。2015年,他复制三年前的“疯狂”,据说又有五本书在国内同步出版,其中很值得关注的是访谈录《薛忆沩对话薛忆沩—“异类”的文学之路》。这部机警、风趣而精辟的“薛忆沩语录”,不仅铭刻着作者个人文学道路上的坐标,也见证了一代理想主义者的精神追求。
薛忆沩颇具传奇色彩,他从多年的寂寞低调,到近年的活跃见报,各种文学访谈在不同时期和地区引起很大反响。《薛忆沩对话薛忆沩》精选了作者十六年间“写”出来的31篇专访,是一部经过深思熟虑的“笔谈录”。薛忆沩在书名中将“对话”的主语、宾语都“兼并”成一个人,显然与首篇虚拟的访谈《薛忆沩采访薛忆沩》一脉相承,当时他对镜而坐,自问自答,此后与文化记者们的对话便被这个习惯“格式化”。薛忆沩借用这种蕴含“自传”元素的文字游戏,不断对自我、人生、文学、历史等重要命题展开追索和反思。
薛忆沩从小品学兼优、文理兼修,在信息封闭的特殊时代,他年仅11岁就通过内部渠道,“偷渡”进入西方哲学和文学的广阔天地。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青春期的叛逆,薛忆沩开始与“生活的逻辑”背道而驰:中学时别人都朝组织靠拢,他却急流勇退辞去“学生官”,向知识俯首称臣;他考上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却醉心于课外阅读和文学创作;他毕业后不肯服从工作分配,在大家依恋体制的八十年代中后期,却几番申请“失业”,崇尚“精神贵族”和文学“个体户”,埋头创作长篇小说;九十年代掀起经济浪潮,人们涌到深圳为了发财,他却为了自由自在,还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攻读热爱的冷门专业,成为语言学博士;当他如愿进入深圳大学执教,工作刚走上“正轨”,却毅然选择离开,以38岁的“高龄”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深造,几年后凭全优成绩获得英美文学硕士学位……他总是既谦卑又孤傲,抵御外界的诱惑和异化,维护写作的自主与纯粹。
薛忆沩独立于主流和传统的文学之路“注定”一波三折,当年的险阻与煎熬,如今被媒体津津乐道:1988年,薛忆沩“速成”第一部长篇小说《遗弃》,自费出版后受到知名学者的褒扬,但八年间的读者不足“十八罗汉”;他24岁“挥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一个影子的告别》,如同一个文学“幽灵”徘徊在出版界,24年后才登陆台湾的《新地文学》;他年纪轻轻就在权威的文学刊物崭露头角,1991年摘取台湾《联合报》文学奖,本来前景看好,不料文学的小舟遇上历史的暗礁,他的写作不得不搁浅,六年后才重新启程,靠《出租车司机》的“歪打正着”,创造了“遍地转载”的骄人业绩;《遗弃》也被学界考古发掘、修订再版,正当行情高涨,他又远渡重洋,创作因求学再度冻结。
移居海外反而使薛忆沩重新领悟到母语的魅力和潜力,文学创作在几年后空前爆发,他不断有触及“灵魂”的新作问世,还大规模地“重写”旧作,戏称这是“更年期”与“青春期”的较量。薛忆沩自我改造的结果,是“潮平两岸阔”—2006年,历时18载的小说集《流动的房间》宣告竣工;2009年,小说集《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成为“中篇小说金库”第一辑的压轴之作;2012年,他在大陆同步推出五本书:《遗弃》、《不肯离去的海豚》、《一个年代的副本》、《文学的祖国》、《与马可·波罗同行》,同时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被列入“世界华文作家精选集”丛书在台湾出版。此后《遗弃》《出租车司机》《首战告捷》《空巢》等几部小说相继登上深圳、广州等地的“十大好书榜”;他连续两年得到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提名,并连获“中国影响力图书奖”、“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林斤澜优秀短篇小说作家奖”。薛忆沩的文学长跑,终于赢得了集中的热烈回报。
于是薛忆沩被媒体誉为“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主要因其优异的先锋品格、跨学科的专业背景、体制外的生存方式,以及热爱数学和长跑等个人习惯,“异类”已经成了他的著名“商标”。薛忆沩对此却不大认同,坦言自己的文学是正宗,又过着单纯的作家生活,被编入“另册”似乎有些错位。但“抢修旧作”的异常行为、“篡改过去”的特异功能,还有在异乡写作、在故乡出版的“新常态”,又一再证明薛忆沩是“异类”,一个充满悖论的“异类”。所以访谈录的副标题沿用流行的称谓,既是对“异类”的强调,又是对“异类”的自嘲。
访谈录秉承了薛忆沩一贯的苛求,诗意与哲理的“含金量”严重超标,思想的表述和语言的修辞都有独特的风格,即便是只言片语,也要轮番耍上十八般“技艺”:隐喻、象征、悖论、双关、反讽……薛忆沩是位高冷“段子手”,把“脱口秀”变成了另一种创作,各个领域的术语在他笔下纷纷产生“诗学反应”,使简单的问答充满了复杂的张力,难以句摘和言传。
整理访谈的过程中,薛忆沩重新面对各种提问,也不断责问自己,而文学的“宿命”与“理想”,是他对所有疑问的答案,他说如果能够选择,他肯定还会选择悲天悯人的文学。薛忆沩应该是“上帝选中的作家”,他把人生当成写作的“祭品”,一意孤行地冒险,忍受各种考验和磨练,就为了兑现与文学的“神圣之约”。可见薛忆沩在“知天命”之年回顾自己的文学道路,并于2015年出版这部访谈录,有着几层特殊的意义— 这是他对“天命”的书面认证,对1975年以来“心许文学”的郑重纪念,也是对三十年创作生涯的中场检阅,更是为新的征程所作的“精神热身”。
《薛忆沩对话薛忆沩》虽是文学创作的“副产品”,却呈现了作者半世纪人生的“主干道”,读者从中既能体会他在辉煌之前的悲壮、风光之后的沧桑,也可以看到他神秘莫测的命运、超脱坚韧的个性,以及十几部“流动”的作品。相信新老朋友们、特别是文艺青年们,通过聆听薛忆沩的“心声”,将对生命多一份敬畏和清醒,对理想多一份虔诚和坚定。薛忆沩在蒙特利尔适得其所、平稳着陆,他那不可限量的文学前途,同样给我们带来了温暖和信心。
本文原载于《南方都市报》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