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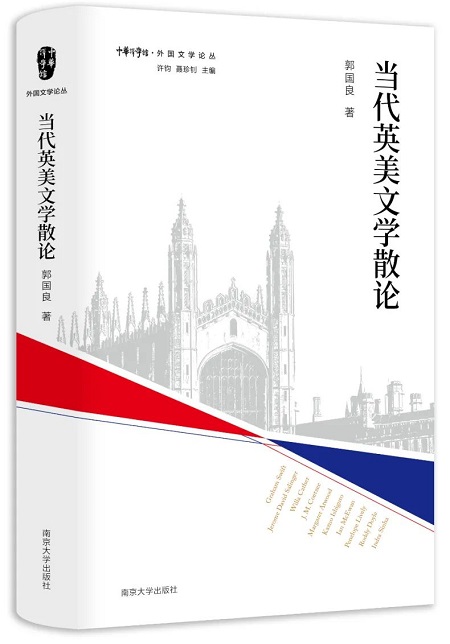
《当代英美文学散论》(订购)
郭国良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这部篇幅不大的小说细腻而深刻地描绘了十六岁少年霍尔顿被学校开除后的近三天中游荡纽约街头,历经艰难,独闯成人世界的心路历程,真实地反映了以他为典型代表的大多数美国50年代青年内心的惶惑、彷徨、闷燥、自艾的心态,勾勒出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年在堕入精神崩溃边缘中的一幅惊人心魄的图景。
霍尔顿是时代的替罪羊、受难者和牺牲品。他满怀抗争的热情,但又缺乏信心和勇气;他天性善良,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一定的正义感,但又失却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他探求生命的自由和意义,却又充满种种卑琐和恶习。他梦想站在又高又深的悬崖峭壁上,看护在旁边嬉戏的成千上万纯清、烂漫的孩子们,做个“麦田里的守望者”。他的这个“守望梦”,集中体现了他摆脱孤独、压抑、虚伪和庸碌而渴求关爱、向往超逸、呼唤真诚、实现自我价值和理想的迫切愿望。
霍尔顿生活在孤独寂寞的精神世界中,渴望得到人们的安慰和关怀。生性敏感的他对周围的人和事看不顺眼。他的思想感情与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成人世界,与结帮成伙的同学,与庸俗难耐的老师,与他浪迹曼哈顿时结识的各等陌生人格格不入。父母的冷漠使他痛苦,而平时表面上对他最好的老师的同性恋行为又使他丧魂失胆。他在旅馆里惨遭妓女等的暗算、欺凌和毒打,受了侮辱却又无处申冤,精神险些失常。他在酒馆里闷坐独酌,体验到了一种难言的疏离感和孤独感,陷入了不可名状的忧伤、抑郁和凄惘中,活脱脱一副落魄苦相,不啻彷徨歧路的飘零客。
他身穿晴雨风衣,头戴红色鸭舌帽,在纽约街头踽躅徘徊——这是他茕茕独立、孤寂无援的形象的生动写照。在他出走的三天里,他发自肺腑地喊出了“一霎时,我觉得寂寞极了。我真希望自己死了”。“我觉得那么寂寞,那么苦闷……”“……外面又是那么寂静,那么孤独,我真希望自己能回家去……”霍尔顿一次又一次的痛苦呐喊,充分表明了他已深陷孤独伶俜的困境中,也昭示着他寄希望于梦想。“守望梦”正是他欲摆脱困境的自然流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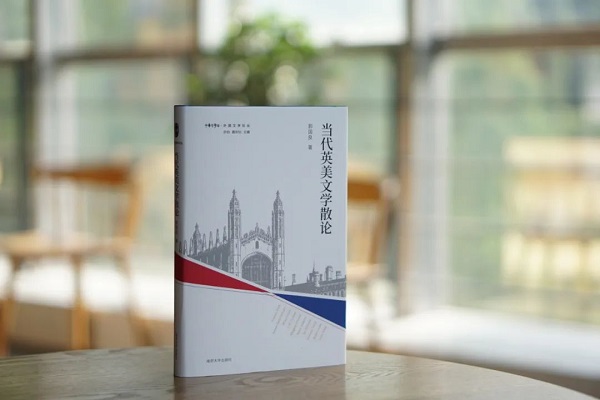
霍尔顿也生活在压抑中。他流离浪迹的三天,又是寻求超脱的三天,是他“守望梦”的一种折射。在学校里,他对一切——老师、同学、功课、足球等等,全都腻烦透了。他之所以不肯用功读书,原因之一就是无论是老师还是父母,逼迫他读书无非是“求学问,出人头地,将来买辆混账的凯迪拉克高级轿车”。在旅馆里,他看到的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有穿戴女装的男人,有相互喷水、喷酒的狗男女,他们寻欢作乐,忸怩作态,使他感到恶心和惊讶。他无聊至极,便来到夜总会厮混。回到旅馆后,心里更觉虚空和烦闷。他开始觉察个人与周围世界方枘圆凿的关系,开始与家庭、学校和社会豆剖瓜分。
横亘在他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是学会在现行的社会环境中得过且过,随遇而安;二是确立新的价值标准,自行其道。霍尔顿不愿随波逐流,过那种浑浑噩噩的日子,不愿拥抱物质充裕而精神匮乏的未来生活,因而无法与令人窒息的社会相妥协;但同时,他又缺少勇气和胆略,成了行动上的矮子。在朦胧的恐惧中,他惶惑地出逃,既试图摆脱心理的压力和强大的社会势力的威逼,又对远非他个人可以抗拒的社会势力做出某种反抗表示。自然而然地,精神压抑中的霍尔顿只有一头扎进了梦想之中。“守望梦”编织得可谓合时又合情。
霍尔顿又生活在伪君子当道的世界中,他企盼真诚和信义,“守望梦”表达了他企求逃脱这个被虚假所充斥的世界的强烈愿望。整部小说中,成人世界中没有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他们全都道貌岸然,母亲只知溺爱他但并不理解他,父亲打着主持公正的法律的幌子大肆营私,牧师装出神圣的腔调,令人作呕;校方自欺欺人,自我标榜,要把孩子们栽培成“有头脑的优秀年轻人”,而毕业生几乎全是势利鬼和马屁精;假模假样的安多里尼先生虽学识渊博却只会故弄玄虚,宣扬极端的利己主义信条:“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雄献身,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还有,霍尔顿眼中最假仁假义的校长看到开着汽车来接孩子的家长就立马跑上前去跟他们一一握手,交谈良久,竭尽巴结逢迎之能事,而对家境贫寒的家长就敷衍地只握一下手,其伪君子的嘴脸昭然若揭。
霍尔顿认识到,这个世界是业已丧失诚实和纯洁的堕落所在,世道不对头,生活无寄托,一切都是“假里假气”。他坚拒与虚假的家伙为伍,痛恨虚情假意的风尚。他想逃离现实,但他在这偌大的世界中找不到归宿,只有向往乌托邦式的西部:在一片单纯清静的森野上,盖间小木屋,找份平平常常的工作,娶个又聋又哑的美丽姑娘,俩人一辈子不言语,靠纸和笔交流信息、传达感情——他认定语言离间人们。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守望梦”其实也是他对虚伪成风的社会的反抗和对朴实、真诚的殷殷向往。
霍尔顿的“守望梦”,从根本上来说,追猎的是潜意识中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他本质上有一颗纯洁善良、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童心。告别童年时代不久,他就不安地意识到童贞受到威胁、理想受到玷污。他觉得自己被世界所淹没,难以听到自己的声音,难以留下自己的脚印。“每次穿过马路之后,你总是有一种像是失踪的感觉。”“我觉得自己会永远走啊,走啊,走下去,谁也看不见我。”失落感和受挫感从心中油然而生。
他渴望与人们交往,但又害怕与别人接触;他渴望得到人们的承认和关注,却用脏话秽语招耳壮威。他在生活中找不到出路,固然反映了他所置身其中的世界庸俗黑暗,显示了他很想遁迹世外,退隐到个人的小小天地里去,也表露了他又不甘沉沦,迫切希望自己能成为这个世界中一个有用的分子。在他踯躅纽约街头的这三天“天路历程”中,他上下求索,在绝望中探寻希望,在迷惘中追求人生的真谛。他不愿被无情的社会所消解和吞噬,期待找到同情、理解和关爱,在内心深处苦求理想、憧憬美好的未来。在他的“守望梦”中,他不让无辜的孩子们跌下悬崖而坠入“世故和腐蚀”的深渊,说明他心存奢望,想实现自我价值,想浪漫地追求想象中的英雄主义。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守望者身临崖顶,自己也已摇摇欲坠、岌岌可危。他穿梭于儿童与成人世界之间,经受着心理矛盾的煎熬和来自灵魂深处的凌厉拷问。他越想逃避现实,却越深地陷入了个人困境的泥潭。他越想挣脱世俗的樊篱,却越被卑琐庸怯所绊羁。霍尔顿寻求超脱、友爱和诚实的努力固然可贵可嘉,但它如空穴来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精神病院才是他三天漂泊后找到的栖所(学校和家已只成遥远的背景)。也许,这栖所是临时的,但他的“守望梦”却无疑是个难圆的“白日梦”。
本文节选自南京大学出版社《当代英美文学散论》。
来源:南京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