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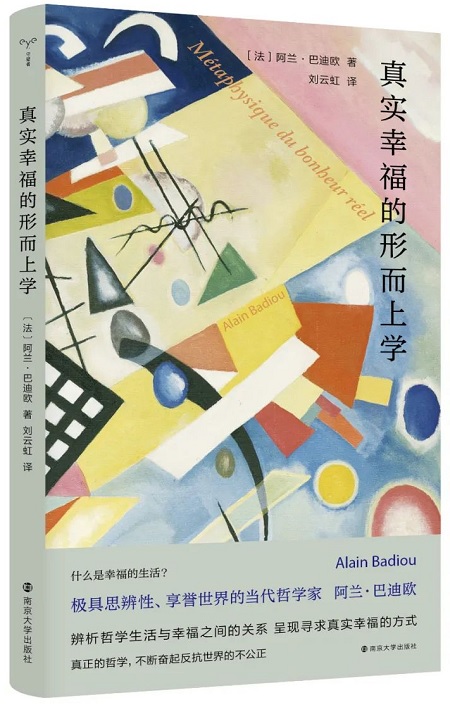
《真实幸福的形而上学》(订购)
[法]阿兰·巴迪欧 著
刘云虹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3年2月出版
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在这些条件下,哲学应承担起放慢思考、建立其专有时间的使命。在其当代倾向中,哲学竭尽全力追随世界的步伐。它被不连贯、分裂又快速的现代时间紧紧束缚。哲学的使命——只要它有能力做到——在于建立一种能赋予自身时间的时间,即一种思想,也就是一种赋予自己缓慢研究与构建之时间的时间。我认为,对一种专有时间的构建是人们能够要求当今哲学所具有的那种风格的指向性原则。在这一点上,最平常的经验来帮助我们:成为自己时间的主人,历来不就是幸福的一个条件?这难道不是主人们始终拒绝给予被统治的大众的吗?共产主义主张人类应摆脱雇佣劳动,后者不正因为是一种异质时间的暴力强加而总被表现为悲惨境况?工人的反抗难道不是经常质疑考勤和考勤机、监督员和劳动节奏吗?一切真实幸福都以时间的解放为前提。
在许多当代思潮,尤其是阐释学派,更特别是后现代潮流中,有一种对哲学话语碎片式布局的推崇或赞美。这种推崇主要扎根于尼采模式。我想,出于形势或时机,或只是因为世界将此强加给我们,必须为哲学重建一个连续性原则。碎片实际上是一种方式,通过它,哲学话语盲目地服从于世界本身的碎片化,并且通过它,以某种形式,哲学话语经由其碎片式分裂任由货币和商品抽象体现唯一的连续性原则。所以,哲学必须发展自身固有的缓慢,并恢复思想的连续性,即创建它的决断原则和连接它的理性时间。
现在让我们想一想:在这些条件本身之下是否有机会看到,显然处于危险中的哲学终于经受住我们开头所讲的挑战,终于能支撑它的欲望?哲学生病了,这毋庸置疑,它所遭受的打击始终与内在的困难相关。我认为——并且这将是我能提出的乐观主义理由——对这个在某种意义上不断表明自己比人们所说的病得更厉害的病人,对这个宣布自己即将死亡甚至已经死去的病人,对这个病人,当今世界——世界,至少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施加了一种模糊的压力,以打破其欲望,同时却悖论地要求其继续活下去。一如既往,世界的意义含混不清。流通、交际和安全的一般体系部分地被引向对哲学欲望的削弱。但反常地,它以矛盾的方式在其内部创造、组织一种要求,这一要求模糊地、似乎虚空地面向哲学的可能性。为何如此?
第一,信心不断增强,至少在力图处于思想自律中的人那里,信心是不断增强的,确信人文科学现在或将来都无法取代哲学,无论在其学科布局上,还是在其欲望的独特性质上。有段时间,广泛流传的一个观念、哲学终结主题的形式之一,就是一种由科学理想赋范的,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语言学、“科学”心理学甚至精神分析学归入其中的普遍人类学,将能够取代哲学:仍然是以某种方式在说,我们已经走到了哲学的终点。至于我,我相信现在所显现的是,人文科学作为统计平均值和一般格局的场所展开,它无法真正使在思想上探讨或涉及独特、独特性成为可能。而倘若人们仔细思考,决定的策源地恰恰总是在独特性中,并且任何真正的决定最终都是一种独特的决定。确切地说,不存在普遍决定,因为开启真理或让人进入真理的,或以某个固定点自我支撑的,都属于决定的范畴,也始终属于独特性的范畴。所以人们会说,如果当前有可能的话,理应提出一种独特性哲学,它能由此成为一种决断和打赌的哲学。
第二,实际上每个人都意识到了所有重大集体主体的破灭,同样,在这点上也是思想上的破灭。重要的并不是知晓这些主体是否曾经存在、正存在着或将要存在,而是这一事实:使理解集体主体成为可能的那些重大范畴,今天似乎已经饱和且无法真正激发思想,不论人类的历史进步类型的形象,还是被设想为客观现实的重大阶级主体,如无产阶级。这召唤每个人关注我所称的以自己名义决定和说话的必要性,甚至并尤其当涉及回应一种新真理的出现对每个人提出的要求时。但显然,甚至并尤其当问题是政治问题时,以自己名义决定和说话的必要性要求为了这一决定,必须有一个固定点、一个无条件原则以及一种支撑最初决定并使之普遍化的共有理念。必须每个人都能说这是对的,那是错的,或这是好的,那是坏的,以自己的名义,但也开放地与他人有机共享其话语。如果说因此要求我们建立一种独特性哲学,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样必须建立一种真理哲学。
第三,我们与集体主义、宗教、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激情的增长处于同一时代。这一增长与摧毁集体主体的重大理性格局截然相反。这些重大格局的动摇和坍塌、共产主义理念暂时却痛苦的缺席导致一种黑暗的淤泥重新升至表面,为明确逃避以自己名义表态或做决定,它将供替换的总体想象化(imaginarise),此外,它还试图根据划界限、排除和对抗的规约依赖于古老的主体,而后者的回归变得越来越具威胁性。从这方面来看,绝对肯定的是,哲学被要求给予它应以之支撑自身的固定点或无条件一种理性形象,同时被要求表明,并不因为集体历史命运先前的理性格局的背叛,人们就要放弃思想的理性坚定这一美德。因此,哲学也被要求能够提供一种更新的形象,一种与当今世界一致的理性的奠基性形象。
第四,我们所了解的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暗中意识到它是一个非常不可靠的世界。此外,存在一个悖论,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表现得似乎是最好的可能世界,而显然,其他任何一个曾在革命或解放范式下经历考验的世界都既罪恶,又摇摇欲坠。同时,尽管装作最好的可能世界,这却是一个知道自身非常脆弱的世界。这是一个被展现的世界。这完全不是一个建立于其存在的持久稳定性之上的世界。这是一个很少自知的世界,它依赖于过度抽象的法则,以避免暴露在它无法接受或迎接的事件灾难下。说到底,战争五十年来不间断地完全毁坏一些国家,并且越来越不怀好意地徘徊于“西方”利己主义的邻近区域。
世界的这种危险的脆弱性让它在流通和交际的普遍法则之外,随时提出无数奇怪的东西和各种分散的极端可怕之事。此外,这个世界最终可能在任意时刻,在这里或那里,或最终在各处都陷入暴力、战争或压迫,陷入一种非常令人震惊的对自身的盲视。从这两方面来看,我想哲学应有能力迎接或思考事件本身,并不完全是世界结构、其法则或稳固性的原则,而是事件、惊异、要求和不可靠如何得以在一种始终理性的格局中被思考。
这就是为什么,以某种与阐释学、分析和后现代的断裂为代价,我认为从这个世界的无限不可靠的内部所要求哲学的,是打赌有一种明确的、奠基性的哲学,它同时是独特性哲学、真理哲学、理性哲学和事件哲学。因而它也应提出人们所称的独特性、事件和真理的一个理性交点,作为哲学欲望的庇护或外壳。这个交点必须创造理性的一种新形象,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将独特性和事件联结于真理,这在古典传统中是一个悖论。如果当代哲学希望保护自身的欲望,希望以建设性的、普遍化的方式向全人类重述圣茹斯特(Saint·Just)的名言“幸福在欧洲是一种新观念”,那么它应着重探讨的正是这一悖论。
至于我,我曾试图表明,这个独特性、事件与真理的理性交点通过其自身构成一种可能的主体新学说。我反对主体同属于形而上学且必须被摧毁这一观念。我提出,只要主体恰恰被设想为独特性、事件与真理于其中理性联结的最大微分,人们便能够也应该向思想和世界提出一种新的主体形象,其根本准则在于:主体是独特的,因为总是某个事件在某种真理中构建主体。或者,主体既是一个可能的理性之所,也是人们所称的事件的真理点。最后,只有对于一个主体,只有当个人接受成为主体时,才有幸福。
我在此试图提出哲学事业的理由和计划,这些论点可以说只是其明确的对角线。
如果人们从如此构建的一种哲学来看待思想和世界,它说明主体的独特性在于由某个事件在某种真理中建立主体,那么人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形而上学已经坍塌或终结,但丝毫不能说形而上学的所有范畴都是过时的。仍旧从这样一种哲学出发,人们因此同样会说,形而上学诚然已经坍塌,但对形而上学的解构本身也已坍塌,并且世界需要一种奠基性的哲学主张,它建立在形而上学与形而上学批判的统治性形象的混合或共同废墟之上。
出于所有这些理由,我相信当今世界比哲学自身所认为的更加需要哲学。如果人们判断出当代哲学主要流派过于适应世界法则的话,那么这一切便不令人吃惊。我还相信,由于过于适应世界的法则,它们没有成功地告诉我们真正的生活能是怎样的。因此归根结底,对这些流派而言,这个世界本身所要求哲学的东西有一部分并不清晰。为使之变得清晰,必须在哲学本身有一种中断,即它就自身任务所说之话的中断。
准则可能是:打破终结。而打破终结意味着已做出一个决定。任何终结都不会自行终止,终结不会结束,终结是无止境的。为了停止终结、结束终结,就必须做出一个决定,而我尝试的正是在世界本身向哲学提出的要求里,给出这个决定的支点和有效元素。
我毫不否认,总之哲学生病了,考虑到计划的规模和支撑这一计划的困难,甚至它或许已濒临死亡。然而世界对它说,世界对这个垂死者说,在此不需要救星或奇迹——这至少是我的假设——世界对这个垂死者说:“站起来,往前走!”于是,在一种真正理念的指令下,往前走将带给我们幸福。
本文节选南京大学出版社《真实幸福的形而上学》。
相关信息
作者简介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1937— ),当代法国哲学家,曾任巴黎高师哲学教授,是当代世界与齐泽克、阿甘本等人齐名的左翼学者。曾师从阿尔都塞,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终结论进行了批判,以《存在与事件》一书开创了“事件哲学”。他的代表作还包括《主体理论》《世界的逻辑》《世纪》《哲学宣言》等。
内容简介
《真实幸福的形而上学》这本简短的小书旨在开启道路,以便哲学战略家能够对每个人说:“这足以让你信服,反对一切观点且为某些真理而思考,这远不是你所想象的徒劳无益的活动,而是通向真正生活的最短路径,当真正的生活存在时,它以一种无与伦比的幸福著称。”
来源:南京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