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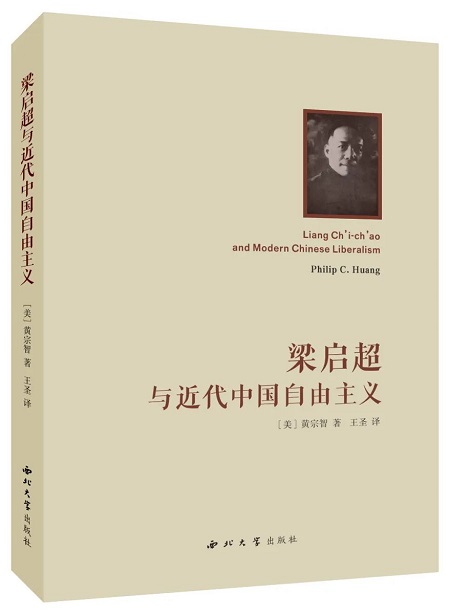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订购)
[美] 黄宗智 著
王圣 译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23年5月出版
后见之明告诉我们梁启超的自由主义计划的失败,但我们不应该忽视该计划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巨大吸引力。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10年代的近30年,自由主义理想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中占据了焦点。在19世纪90年代以寻求制度变革作为民族生存方法的改革者中,自由民主政府的理想赢得了第一批拥护者。在20世纪的前十年里,它继续受到改革者和革命者的拥护。康有为和孙中山在变革的方式上有激烈的分歧,但是他们对宪政和代议制政府的信仰是大同小异的。1911年辛亥革命刚刚结束时,中国选择通过宪法和议会手段来解决分裂的权力利益问题,自由主义运动的吸引力达到了顶峰。尽管随着议会政府被证明无法完成既定的任务,政党政治很快名誉扫地,“民主”仍然成为知识分子革命的战斗口号,并继续得到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拥护。到1920年,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已经不再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后来的中国政府仍然希望保持“民主政府”的形象。事实上,20多年来,中国很多人都在梦想着自由民主。
梁启超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最雄辩、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纲领的代言人。他的故事讲述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特征,以及它作为20世纪中国政治行动指南的优缺点。
梁的自由主义是儒家、明治日本和西方思想的混合体,所有这些都是根据他个人的喜好和关注重新加以阐释的思想。这不仅仅是对西方的移植——基于对他的“儒家传统”的理性拒绝和对西方价值观及其思想的简单拥护。因为在梁看来,中国和西方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整体,它们各自都是在其范围内的复杂的理智选择。在梁的头脑中,其持久性的儒家偏好认为人的道德和态度远比其他一切更重要,公羊思想在塑造他的思想上所起的作用,既表明构成梁的儒家传统的复杂思想的支配力,同时也显示其适应性。因为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并不是固定的量——它可能导向张之洞的改良主义方向,或章炳麟的激进主义革命方向,或刘师培的中国中心方向,或者许多其他方向,当然也可以导向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方向。梁对明治日本影响的接受和他对西方思想的选择性使用,都同样地证明了“西方影响”这一范畴的不足。事实上,从大范围的西方和明治日本的思想选择中,梁走出了自己的思想道路,同时根据自己的喜好对这些思想进行了重新诠释,就像他对儒家思想所做的那样。
构成他的自由主义的混合体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思想,在其中,不同的成分不断相互作用、相互改造。譬如,在19世纪90 年代早期,儒家公羊思想成为他理智中最忠诚拥护的对象,但他对“思想自由”的恪守使他很快拒绝了康有为的教条主义主张。在20世纪 10年代末及以后,他只把公羊学戒律当作一种手段,一种允许他以最大灵活性重新诠释儒家以适应他自己调和目的的方法。然而,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和五四知识革命者的极端主义倾向促使他重新强调了他所认为的儒家折中、融合的基本取向。他对他早期从社会达尔文主义中接受的国家和自我主张的信息,作了相当的限制。下面将讨论的其他变化,来自他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关切之间的相互拖拽,源于他的理想和可观察到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他的抱负与政治行动的紧急状态之间的强烈张力。
他的自由主义计划的核心是“新民”理念,这是一种融合了各种不同思想影响的理念——梁的儒家思想强调人的道德和态度高于一切;他对“思想自由”这一古典自由主义理想的依恋,由于他自身反复无常的理智气质,他很容易认同这一理想;一个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的假设,即自由民主将是追求国家力量最有效的途径;日本明治时期流行的一种思想,觉醒的国民将为自由民主和国力产生必要的社会能量;以及日本和西方关于古典自由主义的道德和价值观的各类著作。“新民”的基础是这样一种假设,即任何变革计划都必须经由人民的态度和价值观的现代化开始。梁特别呼吁一个自由的、民族主义的、积极的“新民”,他们还将拥有其他各种道德和态度上的属性,那些他认为是现代公民所必需的属性。按照他的理解,这样的公民不仅能保证自由民主政府的实现,而且能够确保一个强大的新中国的实现。
和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样,梁的行动方式也是新旧元素的混合。他为自己设想了两个不同的角色,分别以他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的黄克强和李去病为代表。李是一名理想主义的革命家,他要唤醒人民,领导人民进行一场自发的革命。黄是一位精明而务实的政治家——现代政党政治家和得君而治的儒家政治家的结合体。黄是一个试图在现有可能范围内改良中国而遵循权力游戏规则的人。1903年及以前,梁的自我观念主要是李去病。从1903年到1917年,他主要以黄克强的自我形象为导向。
这样一个自我认同的弱点在梁自己的经历中得到了最好的反映。即使他试图扮演李去病的角色,他也无法长久地避免这样一种认识——他的“新民”不可能一夜之间创造出来,充其量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而已。可见的现实使他相信,李去病的目标是不现实和不成熟的。
在梁看来,国家生存的迫切需要不是革命的毁灭,而是加强现有的中央政府。因此,他最终转向了黄克强的行动模式。他尽可能多地在国内号召新的国会力量,但他太现实了,不会把所有的希望仅仅寄托在这些力量上。他认识到掌握权力的人是那些控制军队的人,因此,他试图获得军事强人的信任,并设法通过说服和他可能施加给国会的压力来引导军事强人走向自由民主和现代化的道路。这些思想构成了他在1903年以后反对革命者,以及后来与袁世凯和段祺瑞合作的基础。他的努力为后来的一些自由民主人士提供了先例——仅举几个例子:1917年康有为与张勋的联盟、孙逸仙试图与南方军阀的合作,以及 1922年“第一流内阁”的实验。
但是,在共和国的强权政治舞台上,仅靠宪法力量和说服手段只能是一条薄弱无力的思路而已。到了20世纪20年代,像孙中山和毛泽东这样的人纷纷转向一种不同的权力和行动模式中——组织严密的政党、群众组织以及一个政党军队。20世纪20年代及以后,是国民党,更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意识形态和权力结合起来。他们要控制中国的命运。然而,梁却无法这样去思考。他的自由主义和儒家思想倾向于妥协和调和,以及他个人对思想自由的偏爱,使他不愿意考虑用教条的意识形态来思考。他退回他的自由主义—儒家的教育计划,去着手创造“新民”。他坚持“新民”可以通过教育逐步培养,而一旦得以实现,那么“新民”将以某种方式产生必要的权力,从而将他的理想转化为现实。
这是一个茫然的希望。到了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进程从中国思想界和政界的聚光灯下消失了。许多想要追随它的人转向了其他道路,或者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尽管如此,梁坚信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转变人们的态度和价值观开始,这一信念仍然深刻影响着后来的中国思想。20世纪20年代及以后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公民的正确的价值观和态度产生了不同的设想,而这一探究仍是为了寻求更有效地塑造“新民”的方法。
本文摘自西北大学出版社《梁启超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