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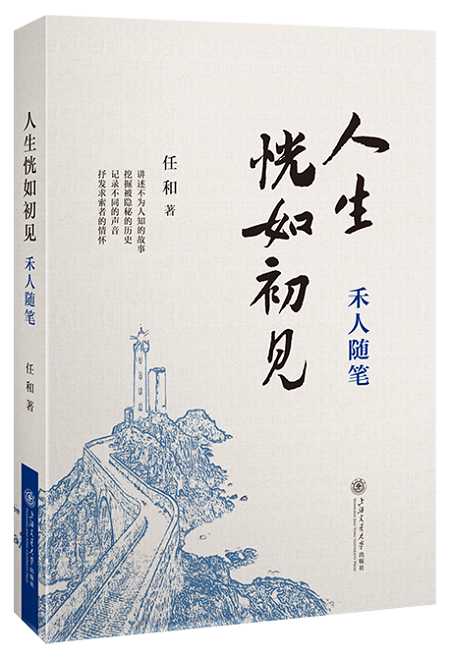
《人生恍如初见——禾人随笔》(订购)
任和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精彩文摘
北航、南航、西工大,是中国三所最著名的航空院校。也是中国飞机设计师的摇篮。我有幸与这三所学校结缘,成就自己的职业生涯。
上高中时,我有幸参加了校航模队,对飞机有了浓厚的兴趣。从全省的航模比赛归来,才知道飞机的理论有多深,制造有多难。从此,学习飞机制造成为我的人生梦想。考大学时,十个志愿中,头三个全是航空院校飞机设计和制造专业。我的高考成绩比全省一本录取分数高出许多分,已经满足中国任何大学的分数线,可我选择了北航。
拿到北航录取通知书后,我心情非常激动,无限憧憬。一个山里娃,将要来到首都北京,实现人生的许多第一次: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到首都北京,第一次进大学校园面对这么多优秀的学子,第一次真正在学业上感到竞争压力,第一次感到除了学习以外,还有更重要的社会活动,而我自己却像一只丑小鸭。到了大三,我对自己的原专业已经完全没有了兴趣。一个偶然的机会,学校院系调整,我向学校再三要求,成功地改换了专业。四年的时间,自己经历了脱胎换骨一般的洗礼。入校时的趾高气扬没有了,代之而来的是灰暗晦涩的心境。自己梦想的专业也与现实相去甚远,对北航母校充满复杂的情感。
80年代初国家的大学数量少,规模小,招生也少,录取率很低(5%)。毕业大学生是时代的骄子,上学不交学费,学校还给发生活费。毕业后工作也由国家统一分配。
80年代中期,我带着郁郁寡欢的心情来到西北边陲一个国防小镇——阎良飞机城,参与到国家某重点飞机型号的研制当中。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总是兴奋的。因为从此将不再依赖父母家人,可以独立生活了。
那时的飞机城,条件非常艰苦。然而投入到国家重特大项目当中,并逐步担当重要角色,其精神力量巨大。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使命感、兴奋感!活在其中,苦在其中,乐在其中。对外界发生的变化几乎浑然不觉。在那里,我生活工作了十年,拥有了家庭和孩子,建立了人际关系,期间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正当我踌躇满志之时,世界却在悄然发生着变化。90年代初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号召军转民。军工企业没有型号任务,资金严重不足,待遇跟不上来。人心浮动,下海成风。我当时决定趁年轻选择读书充电,以备后需。
历史大潮中,每个人都面临选择。任何决策都需要有勇气去面对。利用社会转型的阵痛期,选择良师,从事我喜爱的专业研究,扩展加深自己的知识,成为我当时的愿望。90年代初,我来到西北工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西工大成为我第二个母校。工作后二次脱产入校求学的三年,日子非常艰苦而清贫,但目标明确,精神很愉快。90年代中期,社会已进入了物欲横流的时代,我庆幸躲进了象牙塔,经受住了诱惑,忍住了寂寞,艰辛地跋涉了三年,出色地完成学业。西工大成为我又一个热爱并眷恋的母校,有我许多的良师益友。几年前,母校西工大特聘我为客座教授,我欣然接受。真想以某种方式回报母校,为母校的发展贡献一点应有的力量。
我没有在南航读过书。和南航结缘,是来到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工作以后。我负责国际合作,希望推动两校间的学生交换,后来是联合培养研究生,联合招收培养“2+2”本科生等等。南航聘我做访问教授,我就有了经常来南航的理由。自2006年起,我几乎每年都去。最长在那里讲学3个月。南航在三个航空院校当中,虽然是老三,但是发展非常快。南航人有灵活的头脑,认为现在中国要发展自己的大飞机。
国家把发展大飞机项目列为2006年至2030年间16个重特大技术专项之一,列为振兴中华民族的富国强民的项目。我得知后非常振奋。因为我一直在航空领域工作,发展民用大飞机是我的梦想。一个新技术、新型号出来,就像我的一个孩子出生一样兴奋。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给学生宣讲,它的性能和研制过程。偶尔看到一个新材料的出现,总想是否可以用到飞机上。听到哪次飞机失事,不自觉地开始进行事故分析和判断。我真希望自己也能投入到大飞机的研制当中,把自己半生的学识和经验贡献给自己的祖国,为我们民族自己的大飞机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
(写于2009年8月,墨尔本)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