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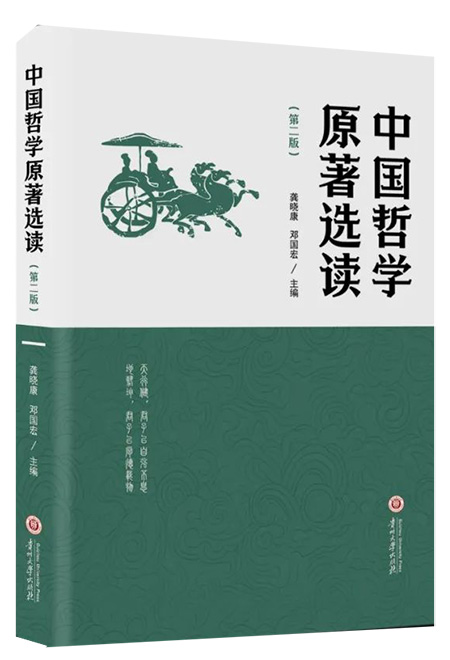
《中国哲学原著选读(第二版)》(订购)
主编:龚晓康 邓国宏
贵州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中国哲学经典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承载着中华民族最崇高的价值理念,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如何对中国哲学经典进行重新诠释,激活文本的意义而彰显其生命力,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了新时代哲学工作者的迫切任务。有鉴于此,龚晓康、邓国宏教授在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选取了中国哲学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文献,编写了《中国哲学原著选读(第二版)》一书,在注释的同时并对其观点进行了解读,目的在于方便青年学子和哲学爱好者研习。
主编简介
龚晓康,贵州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大学出版社副社长(主持工作),国际易学联合会常务理事、阳明文化转化运用研究省创新团队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阳明心学、佛教哲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空性与解构》《阳明学知识论问题研究》。出版专著多部,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哲学动态》等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邓国宏,贵州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哲学、先秦哲学(荀子哲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道统与学统视域下的宋元明清荀子学史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乾嘉时期的荀子学研究》。出版专著多部,在《道德与文明》《孔子研究》《哲学与文化》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导言(节选)
中国哲学虽然与西方哲学出于共同的“哲学原型”,但由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故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脉络。一般而言,中国哲学的发展可分为先秦哲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四个时期。
基于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中国哲学重视形上与形下的贯通。
《易传》有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然形上本体之“道”与形下现象之“器”并非截然二分者,而是“器在道中”“道在器中”,甚至“道即器”“器即道”。“生生之谓易”,中国哲学所言的“本体”,非是西方哲学所言的抽象概念,而是既“寂然不动”又“感而遂通”者。至宋明理学,则从体用的角度阐发之:形上之道作为本体,隐而不显;形下之器作为发用,显而不隐;形上与形下的贯通,是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本体与现象虽有隐显的差别,但其实只是同一个世界的不同面向。
第二,中国哲学重视大我与小我的区分。
《孟子》既言“万物皆备于我”,又言“大体”与“小体”,可见他区分了“大我”与“小我”。庄子也有类似的观点,其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此处之“我”即为“大我”;而“吾丧我”之“我”,则为“与物相刃相靡”之“小我”。大我与小我的区分,亦为宋明诸儒所重视。程颢喜言“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即是要人体证“大我”。王阳明明确提出“真己”与“躯壳的己”的区分,前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故为“大我”;后者“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故为“小我”。但是,“大我”与“小我”的区分并不意味着有两个不同的自我,而毋宁说同一自我具有不同的维度。所谓的成圣成贤,不过是破除小我的自私执着,以回归与物同体之大我。
第三,中国哲学重视性善与性恶的辨析。
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之说,启发了儒学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孟子即心而言性,“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心中即具有仁义礼智等向善的力量,故其主张“性善”。荀子所言之性,为人生而就具有的自然情性,“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放纵情性则有恶行的发生,“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荀子主张“性恶”。孟子之性善论,挺立了人之道德本体。荀子之性恶论,则看到了教化的力量。宋明诸儒则区分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前者出于理,为纯善无恶者,是人的先天道德本体;后者理与气杂,为有善有恶者,表明人需要道德的转化。
第四,中国哲学重视存理与去欲的工夫。
关于“理”,《说文解字》有云:“理,治玉也。顺玉之文而剖析之。”“理”为玉石自然之纹理,然需顺其纹理而剖析;前者表明“理”具有先天的性质,后者表明其呈现不离后天工夫。与“理”之自足性相反,“欲”则表示某种缺失性。《说文解字》有云:“欲,贪欲也。”欲望之义,就在于贪婪地攫取外物以满足小我。宋明理学家皆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即通过存养天理而灭除自私意欲。王阳明对理欲问题则有新的发明。一方面,他提出“理也者,心之条理也”,天理不过是本心天然的条理。另一方面,他认为七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七情若是顺于本心,则具有道德的动力;“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七情若是有执着,则沦为“人欲”。理、欲皆出于本心,两者并非有直接的对立。与理相对立者,乃是欲之执着,故王阳明认为存理灭欲之实质,在于去除欲望中的自私执着以复归本心的天然条理。
第五,中国哲学重视良知与知识的辩证。
孔子虽然强调“生而知之”,但“入太庙,每事问”,表明他也重视知识的习得。孟子主张人有不虑而知之“良知”,荀子则强调“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孟荀之论“知”,实有不同的维度,体现在宋儒那里,则是“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区分。王阳明以“德性之知”为良知,以“见闻”为知识,谓良知与知识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心之虚灵明觉即是本然之良知,其动而有意与物之间分离:一方面,“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以良知为本体;另一方面,“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物以良知为本原。故良知实为认知活动生成的源初场域。良知既为吾人先天之心体,不因后天之见闻而有,故能不滞碍于见闻。就见闻之知而言,其是以意与物的分离为前提,并在主客的交互运动中而形成。而意、物皆出于良知,故见闻“莫非良知之用”,而良知“亦不离于见闻”。王阳明承认知识具有客观的价值,但又认为知识需要良知的指引,故他持一种即知识而超越知识的中道知识论。
来源:贵州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