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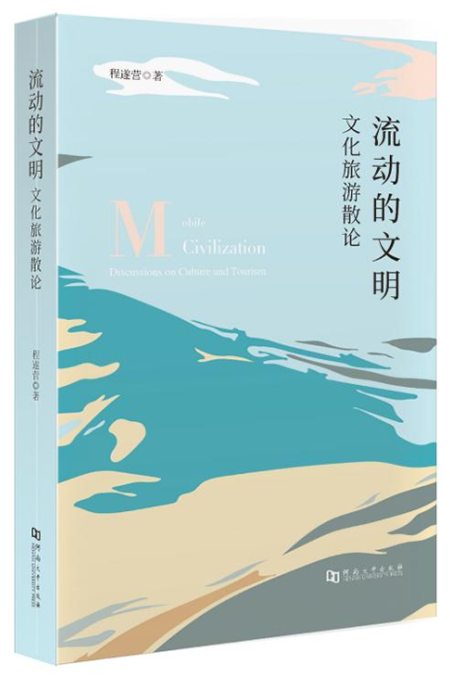
《流动的文明:文化旅游散论》(订购)
作者:程遂营
河南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水是生命之源,河流是水的常态,流动的河流哺育了两岸的生命;旅游是人的流动,文明在人的流动中传播、交融、成长。作者从求学到从教几乎都在与河流打交道,在不断的流动中体悟文化和旅游之道。
作者简介

程遂营,河南大学文化旅游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中原英才计划中原文化名家,享受河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省优秀教师,央视《百家讲坛》“六大古都”“黄河上的古都”“丝路上的古城”“长江边的名城”等系列节目主讲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研究”等项目10余项,在《光明日报》《旅游学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程遂营讲六大古都》《黄河上的古都》《丝绸之路上的古城》等学术专著10余部。曾赴欧洲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为华人、华侨宣讲中国文化。
精彩书摘
序言一
从小河到大河

“望京楼”十分醒目。据记载,这幢高楼是村里富豪孙永信的家族楼,最初建楼是为了防匪、防盗。原有两幢,后因年久失修拆掉一幢。而今有幸留下的这幢楼,高约17米,四层,墙体厚度达80厘米,用坚实的青砖砌成,雄浑古朴,俗称“简城高楼”。2021年,被列入河南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与悠久的历史相比,给幼小的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村旁流过的两条小河。一条河从村子的南面流过,另一条从村子的北、东绕过,两条河在村东南汇合,流向远方。小时候,不知道河流的名称,也不清楚源自哪里,流向哪里。后来,有了一些地理知识,才明白村南的那条河叫沙河,发源于鲁山县境内的伏牛山区;村北的那条河叫北汝河,两条河合流后仍称沙河或颍河,是淮河最大的支流。
在我的记忆里,沙河的水异常清澈,可见鱼虾。夏天的时候,我和小朋友们经常在小河里洗澡、嬉戏、摸鱼、捞虾。三面环水,村子的景色很优美;小河淤积形成的沙土地适宜花生、水蜜桃的种植,香甜的花生和硕大水蜜桃成为我童年为数不多的美食记忆。不过,由于没有桥梁,只有渡船摆渡,村子的对外交通极为不便。每年洪水季节,沙河还不断侵蚀村里的土地,使简城村每人只剩半亩左右的耕地。地少人多、无法靠种粮自给的窘境,迫使村里很多人不得不另谋生路。
我的家庭是典型的另谋生路型家庭!我的父母都不识字,是标准的文盲。但有幸的是,1958年,我父亲参加了沙河上游第一座蓄洪大坝—— 昭平台水库的建设。因为干活卖力,又有一手能做饭的技能,留在了昭平台水库,成为那里炊事班的一名员工。我的母亲则留在简城村,务农为业。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的概念,父母生养了我们姊妹六人。我排行老四,上有三个姐姐,算是男孩里的老大。照理来讲,因为父亲不在家乡,我的上面又是三个女孩,我这个男丁是需要扮演程家男劳力角色的,可我的体质偏偏不争气!据母亲回忆,出生的时候,我足有八斤重,但一生下来,就面临家庭经济困难,母亲和我整天只能吃红薯充饥。母亲没有奶水,我吃红薯整天拉肚子。一两岁时,我瘦得皮包骨头,差一点就饿死被扔掉了。后来,虽然勉强活了下来,但从童年长成青少年的我身材瘦弱,个头不高,根本不像父母期待的男劳力的模样!我记得,因为心疼母亲和姐姐们,我也曾经拉着装满红薯的车子,试图展示男子汉的气魄,结果呢!不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下坡时还差一点弄翻了车。大姐赶忙制止我说:“赶紧别拉了,你根本不是干重活的料!”
不能做撑起门户的男劳力,还能做什么?幸好,那时候村里的教育和学习氛围很不错,有小学、初中,老师们大多年轻,有朝气、有活力。逐渐地,我在学校里发现了自己的快乐和价值!
也许是大姐的话刺激了我,也许是真的喜欢学习,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当然,也成为最受老师宠爱的学生。每年春节前,当我把一张张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奖状带回家,母亲和姐姐们满心欢喜,然后用糨糊把它们整整齐齐贴在正堂的土墙上,到我初三毕业,已经贴了满满的一面墙。与此同时,因为父亲很少回家,农田里播种、施肥、收获等活计不得不由母亲、姐姐们扛起来。实在干不了的重活,只好央求左邻右舍和亲戚们帮忙。
当然,母亲和姐姐们再辛苦,也撑不起家里的门面。所以,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辛苦,也很艰难,母亲常常愁得偷偷掉眼泪。对于这种家庭窘境,我父亲也是心知肚明的。于是,随着我们兄弟姊妹逐渐成长,我的二姐、弟弟和妹妹先后到了父亲那里,在昭平台水库或在水库附近的鲁山县城谋了职业,减轻了家里的负担。
初中毕业后,我成为村里第一个考上舞阳县城一高的学生,三年的高中学习之后,我又相继成为村里第一个考上省外大学的学生、第一个硕士研究生、第一个博士生、第一个教授。
从大学到博士学习,我从家乡的小河走出来,与几条大河结下了不解的缘分。首先是大学时代的长江。高中毕业后,我来到了美丽的江城武汉,在华中师范大学(原华中师范学院,1985年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度过了难忘的四年时光。在此之前,我见到的最大河流就是家乡的沙河,而浩浩的长江的确给了我不小的震撼。我清楚地记得,1984年刚入学,我就从校园广播里听到了由胡宏伟作词、殷秀梅演唱的《长江之歌》:
你从雪山走来
春潮是你的风采
你向东海奔去
惊涛是你的气概
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
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
我们赞美长江
你是无穷的源泉
我们依恋长江
你有母亲的情怀
……
悠扬、婉转的歌声伴着满山飘香的桂花在桂子山上回荡,令我心旷神怡。而后我游览了武汉长江大桥、黄鹤楼,想象着大诗人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美妙意境,如痴如醉!
四年大学毕业后,我考取了哈尔滨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有同学开玩笑说,我从“火炉”一下子掉进了“冰城”。的确,这个弯子转得是有点大,连我自己也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今天想来,完全是拍脑门式的抉择。不过,美丽的松花江很快平复了我略显不安的心绪,太阳岛和煦的阳光也让我这个中原游子感觉到了冰城的温暖。在哈尔滨的三年,我第一次学会了滑冰,虽然老是跌跌撞撞;第一次坐了马拉的冰爬犁;第一次知道哈尔滨冰灯的冰块取自松花江;当然,也第一次感受到了室外彻骨的寒冷和室内温暖如春的强烈反差。研究生毕业时,我差一点留在大庆。因为那时候的大庆油田待遇很好,研究生可以直接分配一套两居室的房子,过年还有油、米等福利。不过,父母还是非常希望我回家乡工作。于是,1991年,我来到黄河岸边的河南大学,当了一名教师。
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北距黄河只有九公里之遥,不时地,我骑着单车独自或与一二朋友一起去黄河边溜达。多少次呆望着东流的黄河水,总是无法和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壮美诗句关联起来。当然,也无法想象,古代桀骜不驯的黄河水如何泛滥成灾,淹没开封城市和广大乡村。反倒是,浑浊而带有污染的黄河水,使我对数千年来“母亲河”背负的沉重负担感到些许的悲悯!
20世纪90年代,高校掀起了读博热潮,我也随波逐流,考取了南京大学,攻读中国古代史博士学位,这是又一次对长江的回归。南京长江大桥不同于武汉长江大桥,南京的中山陵也不同于武汉的黄鹤楼,但南京人对鸭血汤的钟爱却类似于武汉人对热干面的青睐。虽然在长江边学习,但博士毕业论文选题我还是选择了开封,撰写了《唐宋时期开封的生态环境》。所以,博士毕业后,我又回到了河南大学。
从沙河到长江,从松花江到黄河,从小河到大河,我似乎对老子“上善若水”的深刻意蕴逐渐有了更深的理解。的确,人间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好像水一样,宽厚、包容、谦卑、无私,“善利万物而不争”,就像慈爱的母亲,滋养万物。哺育了开封、武汉、南京的黄河、长江是这样,哺育了我的家乡简城村的沙河以及美丽冰城哈尔滨的松花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来源:河南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