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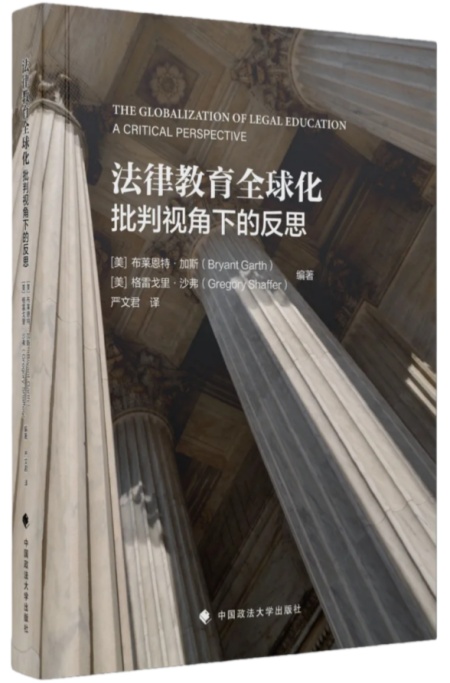
《法律教育全球化:批判视角下的反思》(订购)
作者:[美] 布莱恩特·加斯,[美] 格雷戈里·沙弗 编著
译者:严文君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原书编者:布莱恩特·加斯(Bryant Garth)、格雷戈里·沙弗(Gregory Shaffer)。本书结合了两个理论视角来探讨跨国法律秩序形成的过程。通过结合这两种理论视角,本书评估了驱动跨国法律“共识”形成的因素,即何为“良好的”与“现代的”法律教育,同时考察了法律职业内持久的国家竞争如何破坏这种“共识”的。这种发生在跨国和本土结构中的两种进程相互交织,影响了全球和地方的法律教育改革。
作者简介

布莱恩特·加斯(Bryant Garth)
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法学院杰出的法学荣誉退休教授,在法律职业、全球化和争端解决领域造诣深厚。他履历丰富,曾先后担任美国西南法学院、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法学院院长以及美国律师基金会主任。Garth教授的学术成果斐然,专注于法律职业、法律社会学和全球化研究。他与Yves Dezalay合著的两部书籍荣获法律与社会协会颁发的Herbert Jacobs奖。此外,他还担任《法律教育杂志》(the Journal of Legal Education)的联合编辑,参与 “After the J.D.” 项目,并主持法学院学生参与度调查咨询委员会。在众多学术期刊上,都能看到他发表的研究成果,他也经常在学术会议中担任重要角色,是法律教育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者。

格雷戈里·沙弗(Gregory Shaffer)
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Scott K. Ginsburg国际法教授,在国际法领域成就卓越。他曾担任美国国际法学会主席,是全球知名的法律与全球化专家,尤其擅长国际贸易法。沙弗教授学术成果丰硕,出版12部著作,发表超百篇文章和书籍章节,其研究常被引用。他的作品跨学科,涵盖跨国法律秩序、法律现实主义等多领域话题。《新兴大国与世界贸易体系:国际经济法的过去与未来》荣获国际研究协会奖项,还曾获约翰・杰克逊纪念奖。他获得多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奖,在多所知名院校担任访问学者,在约30个国家开展讲座。此外,他还活跃于多个学术期刊编辑和顾问委员会。
译者简介

严文君
外交学院国际法系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曾为2024年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2017年英国牛津大学沃夫森学院和2012年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的访问学者。现任中国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宇航学会航天政策与法律专委会委员、酒泉国际仲裁院仲裁员、《中国国际法学刊》编辑。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公法基本理论、国际争端解决、国际组织法、国际人道法和外空法。在SSCI和CSSCI等期刊中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主权债务违约的国家豁免问题研究》1部,参编2部。前后撰写11篇资政报告为有关部门采纳或批示,其中3篇得到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
中文版序言一
我的职业生涯处于全球化时代,一直在从事教学工作。我在美国授课,美国已成为全球法律教育的核心枢纽。在美国,我教导过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其中有许多来自中国的优秀学生。我也曾前往中国,在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讲学。而此刻,我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研究院撰写这篇序言,最近我在这里结识了来访的中国教授,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是领军人物,包括杨国华教授、叶斌博士和胡建国博士。由此可见,我的经历正是法律教育全球化的一个缩影。我在乔治城大学的学生严文君将本书翻译成了中文,我对此深表感激。
本书是我与布莱恩特·加斯(Bryant Garth)教授合作的成果,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他是一位重要的导师。本书融合了我们二人研究全球化与法律的不同方法:我关注跨国法律秩序的构建过程,而他则侧重法律职业的社会学研究。这次合作成果丰硕,希望本书的中文版也能让中国读者有所收获。我们十分感谢本书的重要撰稿人,他们从多个国家的视角探讨了法律教育的全球化。
在撰写和编辑本书的过程中,加斯教授和我都参与了与中国相关的研究项目。加斯教授与他的长期合作伙伴伊夫·德扎莱(Yves Dezalay)在《法律:再生产与革命:一部相互关联的历史》一书中涉及了中国相关内容,其中有关于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章节。我则与高亨利教授(Henry Gao)合作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探讨中国如何融入国际贸易和经济法律秩序,这也促使我撰写了《新兴大国与世界贸易体系:国际经济法的过去与未来》一书。
中国在法律和法律教育领域投入巨大。这些投入改变了中国的教育,在中国国内产生了重要影响。反过来,它们也让中国以及中国律师在全球跨国法律秩序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国学生持续出国留学,同时大量外国学生来到中国。这些国内和跨国的法律教育进程非常值得研究。本书为如何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范例。
格雷戈里·沙弗(Gregory Shaffer)
中文版序言二
格雷戈里·沙弗(Gregory Shaffer)和我感谢严文君将我们的《法律教育全球化:批判视角下的反思》一书翻译成中文,并促成其在中国出版。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引起中国法律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兴趣。这篇中文版序言将较为简短。沙弗教授和我在本书第一章撰写了一篇篇幅较长的引言,该引言旨在将书中各章节置于更宏观的历史、法律和社会科学框架之中。它概述了我们撰写本书想要达成的目标,我在此就不再重复其中内容。不过,我很高兴能写这篇简短的序言,专门向中国读者介绍本书。
本书名为“法律教育全球化”,然而或许令人惊讶的是,书中大部分章节探讨的是一种特定的法律全球化进程:即美国法学院法律教育模式的输出与输入,这些模式包括案例教学法、跨学科法律学术研究、诊所式法律教育,以及法学院与律师事务所之间的紧密联系。与此相关的是,许多追求“全球化”的法学院都在教授 “跨国” 法律,比如世界贸易组织(WTO)法、国际商法和国际商事仲裁法、全球环境法,以及包括国际刑法和国际人权法在内的国际法。法学院全球化运动中还涉及众多的跨国法庭,它们大多是冷战结束后设立的。随着冷战后美国实力和理念的兴起,这些跨国法庭和法律变得愈发重要。因此,本书的多个章节(尤其是第十二、十三、十四章)都对跨国法庭和法律展开了讨论。
本书副标题为 “批判视角下的反思”,因为我们旨在批判性地解释和理解,为何及如何在1990年后的时期,冷战后美国的霸权转化为一场全球法律教育改革运动。美国凭借其影响力推行符合本国利益的贸易、投资和经济政策并使之合法化。这一全球变革进程促进了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同时也使得大型律师事务所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自19世纪末以来,这些大型律师事务所与美国法学院,尤其是以哈佛大学法学院为代表的顶尖法学院密切合作,在美国的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过去三四十年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新一代法律专业学生都渴望进入大型跨国律师事务所或其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工作。因此,法律教育全球化与知名大型律师事务所和法学院的扩张紧密相连,实际上,这些法学院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进入这些律师事务所(当然也为其他跨国机构输送人才)。
然而,必须认识到,这种法律教育与实践的全球化既有全球层面的根源,也有本土层面的根源。例如,以亚洲学生为主的世界各地学生前往美国(以及澳大利亚、英国等其他国家)学习法律(以及商业、经济等相关学科),他们往往带着专业知识和法学学位回到本国,并将其投入当地律师事务所、法律学术研究以及法律教育的改革之中。与此同时,冷战后的美国终于能够利用福特基金会等长期以来的慈善投资,将美国的法律教育模式推广到国外。因此,法律教育全球化的结果并非源于美国法律教育与实践模式的优越性,而是特定时期美国全球霸权的体现。
这并不是说每个国家都在模仿美国,而且即便是所谓的模仿,也更多地带有本土特色而非全球共性。但世界上相当一部分国家在进行法律教育改革时,主要参照的还是美国法学院。对于见多识广的律师和学者而言,美国的做法似乎更“现代”,理应被传授、模仿并推广到全球,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尽管美国的霸权地位近来有所衰落,但这些模式的影响力依然强大。
数个世纪以来,与全球权力相关的类似现象一直在上演,无论是殖民统治、帝国霸权,还是没有正式殖民或帝国架构的霸权。罗马帝国就是欧洲的一个典型例子,它推动了法律职业的发展,这种发展从中世纪的博洛尼亚开始。罗马法律传统在欧洲大陆和英国演变后,通过欧洲的殖民主义和帝国势力传播到世界各地,即便在这些帝国衰落之后,其影响至今仍在各大洲延续。我们可以预见,未来全球权力的转移将影响法律或其他治理形式在全球和各国所发挥的作用,但以往全球强国的影响依然会存在。
全球权力关系的多变性意味着,我们这本书聚焦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美国的法律以及教育和实践中的法律模式尤为显著。此外,现代技术使得变革能够迅速发生。在当今这个动荡的时代,变革可能会再次迅速降临。
中国并非本书的主要关注点,但鉴于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书中必然在多处有所提及。许多章节探讨了中国的法律和法律教育发展情况,包括那些对中国及其他国家都产生影响的进程。其中有一章(第十章)聚焦于中国深圳一所新建的研究生法学院——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的创立。该学院旨在融合美国法律、中国法律和跨国法律,其毕业生主要在企业法务部门和律师事务所任职,以融入全球经济。这一章由该学院的前院长菲利普·麦克康纳赫(Philip J.McConnaughay)和副院长科琳·图米(Colleen B.Toomey)共同撰写。另一章(第十一章)关注纽约大学吸引本校法学院学生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海和巴黎的纽约大学校区留学的举措,但赴美留学的学生数量远超美国外出留学的学生数量。
第二章详细阐述了福特基金会是如何按照美国模式成为全球法律教育改革推动者的,该基金会在推动将诊所式教育纳入中国法律教育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章由罗恩·列维(Ron Levi)、罗妮特·迪诺维策(Ronit Dinovitzer)和王温迪(Wendy H.Wong)撰写。维罗妮卡·泰勒(Veronica L.Taylor)在第六章中也探讨了在全球化影响下,律师在特定时期如何更多地参与政策制定,其中也涉及中国的情况。澳大利亚的安西娅·罗伯茨(Anthea Roberts)撰写了第十四章,该章对比了多个国家国际法的教学方式和授课人员,指出在国际法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美国与中国的情况可能比与法国或俄罗斯更为相近,后两者在国际法领域相对封闭。这一章还将留学生流向与国际法的发展联系起来。最后一章由卡罗尔·西尔弗(Carole Silver)和斯维莎·巴拉克里什南(Swethaa S.Ballakrishnen)撰写,描绘了那些在本国接受法律教育后赴美攻读法学学位的学生的经历,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学生以及亚洲学生。该章探究了学生赴美留学的原因以及他们从这段经历中获得了什么,不同国家的学生情况可能有所不同。
因此,中国参与了法律教育全球化进程,当然,参与程度在不断变化,并且与中国国内的重大事件和主流观念密切相关。中国以及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在不同时期也曾借鉴其他国家的教育和学术实践,如德国(日本也借鉴了德国的经验)和苏联。本书还探讨了非洲(第三章,尤其是第四章的南非)、拉丁美洲(第七章,尤其是第八章的巴西 )以及包括印度(第五章)和不丹(第九章)等其他地区在法律教育全球化方面不同但又相关的经历。
直到1990年冷战结束后很久,才出现关于法律教育全球化的讨论。此前,大多数有关这一现象的文献都片面地推崇以美国为模板的现代化模式。我们从批判性和社会学角度进行的这项研究,旨在将那一时期和该模式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并结合不断变化的全球态势进行分析,尤其是1990年后美国霸权时期的情况。
布莱恩特·加斯(Bryant Garth)
译者序
我翻译这本书的机缘是2024年我在乔治城大学法学院访学时,选修了沙弗(Shaffer)教授的《跨国法》(Transnational law)这门课。沙弗教授对待国际法的态度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他经常会在课堂中引用和比较其他国家的国际法观点来讨论问题,旁征博引,丰富而多元。而作为一名教师,他又深谙教育之道。因此,在读到他这本《法律教育全球化:批判视角下的反思》时,我便十分有兴趣。我博士毕业后,从事法律教育已逾十载,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之余也时常会去思考法律教育的实质是什么,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法律人才,以及我国法律教育在世界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本书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一批杰出的美国法律教育者(其中不乏国际法学者)对美国自身以及全球法律教育的思考,而这些,对我们转换性地站在中国视角去思考同样的问题,是很有益的。
中美法律教育虽然有巨大的差异,但其背后的核心逻辑以及重要影响因素可能有相通之处。比如我们同样有着独特的法律教育环境、同样需要把法治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同样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法律人才、同样有着不可估量的海外法律服务需求等。就目前来看,中国每年有大批学生前往美国留学,接受美国法律教育,有相当比例会回国为祖国服务。中美法律教育的这种紧密联系不容忽视。因此,对我国法律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和批判,并将其置于更宏大的世界叙事背景下进行思考自身定位和未来发展,无论对从事教学科研具体工作的法律教育者,还是制定法律教育战略或政策的政府公务员,抑或是接受法律教育的法学生,乃至于任何可能对法律教育施加影响的更为广大的社会群体来说,都是有益的。
对于这本书,我是先读后译的。作为读者,这本书给我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的感悟。推荐书,就如上菜。这里我先分享自己的感悟,就如同上菜前的介绍,做一些推荐者的功夫。具体食味就留待食客自行品尝了。
其一,对待法律教育的全球化眼光和胸襟。全球化不仅带来了生产、消费、服务等诸多方面的全球流动,也让法律教育具备了全球化特征。各国的法律教育固然是植根于各自特殊的地方化土壤,各具特点,但我们不应忽略地方法律教育与全球法律教育之间的互动与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法律人才具有跨国法律教育背景,他们的理论研究方法和实务工作方式都不可避免地体现出多元法律文化的烙印。在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寻求接受多元化的法律教育,而无论其最终是服务于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在现实当中,各国的法律教育也在相互影响,甚至会带来法律文化的相互交融。我们对法律教育展开研究时,如果忽略这种现实情况和需求,可能很难对自身法律教育的定位和未来发展做出准确的判断,找到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甚至可能错过法律教育改革的历史机遇。
其二,注意到法律教育与诸多影响因素之间的联系。法律教育从来不是养育在玻璃瓶中的花朵,它植根于大地,伸向天空,是特定社会生态中的重要环节。因此,法律教育决不会是封闭的,它需要与社会、与世界融通;也不应是模式化发展,它不可能超脱于其所植根的那片土壤,变成空中楼阁而毫无益处。在这本书里,学者们通过对各国法律教育的对比研究,汲取其本地化的教育经验,为我们展现了不同法律教育体系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地方化的法律教育会受到诸如历史传统、政治、文化、宗教、发展愿景,甚至是外来力量介入的影响。从法律教育的主体来看,这些影响也是多维的。比如教授们的教育背景和思维方式,会逐步塑造现实中的法律教育模式;而学生不断变化的成长需求,也会推动法律教育方向的转变。注意到这些影响,并对其与法律教育之间的联系展开科学研究,可以避免我们只把眼光放在法律教育本身去闭门造车,从而打开法律教育革新的思维和眼界。
其三,批判与自省。一个法律教育体系是否能够存在并持续具有活力,除了天时地利人和外,对自身体系进行深刻地批判和自省也是十分重要的。批判和自省作为一种方法,有助于我们更了解自身法律教育体系存在什么问题以及如何得以改进。如何进行批判和自省,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三种视角:一是不同法律教育体系之间的横向比较;二是同一法律教育体系在历史上的纵向对比;三是时刻保持对自身法律教育体系的危机感。尽管批判和自省的方法、依据或结论不见得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赞同,但这种态度和做法本身,就体现了一个法律教育体系内在自洽性的动态需求。我相信,如果所有参与到这个法律教育体系中的主体都保持着批判和自省的态度,他们会更理性地认识到自身的定位、参与度或使命感。
其四,海纳百川的包容心态。古语有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法律教育同样如此。从基础上看,法学是一门关于思辨的社会科学,它需要容纳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理论、不同的经验和不同的方法。因此,在法律教育发达的国家,多样性往往是衡量法律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国家法律教育应该是包容而多元的,多元化的师资力量、学生来源、教育方法或法律文化,都会成为培养法律教育创造性和活力的土壤。国家法律教育还应该是包容而开放的,既需要更多具有不同背景的教师、学生、律师以及社会工作者参与进来,也应该鼓励这些人走出去,去到更广大的世界去印证法律教育的效果,形成更丰富的教育成果和经验。法律教育如能像大海般吸收新事物、新内容和新元素,必定会有助于扩大其容量、增加其厚度、强化其韧性。
作为译者,在翻译时的一些考虑和处理也想与本书读者分享,以帮助澄清疑义、便于阅读。首先,在翻译这本书时,我是致力忠实于原著的。翻译本书的初心是希望读者能够了解到原著的内容和信息,而非演绎。所以,尽量还原原著是本次翻译的主要目标之一。但在翻译过程中,我也会对极少数可能存在表达上不恰当、不完全符合现实以及容易导致误解的内容进行了处理,包括删减和转化。比如第一章第一节中,作者认为中国式的授课往往是单向的且学生人数超过数百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现在很多学校已经可以做到小班教学,尤其是选修课。比如我所在的单位外交学院,自建校以来,除了极少数基础性的必修课,几乎都是小班教学。但总体来说,本书绝大多数的内容都得到了保留并以原有的面貌呈现,对此读者不必过于担忧。其次,代入一种转换性视角。这本书的原作者们立足于美国式法律教育在全球教育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去审视和反思法律教育全球化,不可避免地站在了美国的视角。这涵盖了如何建立全球法学院、福特基金会对于法律教育全球化的推动作用,以及美国律师或教师在世界各地从事法律教育的经历等。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去看美国怎么做,而是美国怎么做对于我们来说存在何种有益的借鉴。在翻译过程中,我代入了这种转换性视角,去思考中国该如何去创建全球法学院,中国的基金会能否像福特基金会一样去推动法律教育甚至是法治建设,以及中国的律师或教师能否深入到世界各地展开法律教育或法律实践。读者只有代入这种视角,或许才有可能了解译者的真意所在。最后,对区域法律教育体系的关注。如果说法律教育全球化是一张大型网络,各个国家是这个大网上的点,那么区域法律教育体系就是一张张小型网络。我们以前对这些小型网络没有给与足够重视,以至于我们的眼光往往直接瞄准了地球的另一面。而实际上,区域法律教育体系既可以是全球体系与国家体系的“连结点”,也可以成为自身法律教育体系走出国门的第一个“试炼场”。像本书中提到的SELA这种一种会议形式抑或理解为一种法律教育传播方式,它不仅具有相当的活力,而且对于促进美洲法律教育的交流颇具益处。
这些想法,有的是源自于阅读这本书直接获得,有的是消化后间接触发。无论哪些,均是立足于对我国法律教育体系的思考。我本身作为中国法律教育的一份子,一直期待着对我国法律教育体系建设和改革尽一些绵薄之力。我认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法律教育体系应至少具备以下三个因素:第一,“自洽”。即法律教育体系的建设目标、逻辑与路径、发展阶段、构成条件和影响要素等能够形成内部的合理性和统一性,经得起科学推敲和考验,并有利于形成法律教育的共同语言,让法律教育的参与者能够凝聚起共识,为共同的法治目标奋斗。这种内部自洽性同样需要与外部社会的现实发展建立联系,呼应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要,找准国家法治和国际法治发展的历史定位,形成同频共振、动态自洽。第二,“务实”。“经世致用”是法律教育的鲜明特征。法律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法律人才,无论这些人才是服务于政府部门、司法机构,还是学校、律所或企业,都需要扎根社会,解决现实问题。这就要求法律教育体系的建设和改革应坚持以现实为指针、以问题为导向,淡化学科固有的界限,拆除校园与社会之间的藩篱,加强教学单位与实务部门的交流与联系,鼓励教师、学生、律师和其他法律工作者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让法律教育的效果在现实中得到检验,并从实践中源源不断地汲取养分。第三,“更新”。一个初设完美的体系,如果一直故步自封、一成不变,慢慢也会落后于时代,与社会脱节;而一个起初不甚完美的体系,如果能因地制宜、依时而动地不断自我革新,不断进步,也会逐步演化得成熟和完善。我们应该把自身的法律教育体系建设成为一个谦逊、包容、开放的体系,使其善于学习,勇于进取,不断实现自我进化和升级,从而保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万丈高楼平地起固然难,更难的是站在高楼之上仍有吐故纳新、自我改革的勇气。对于一个优秀的法律教育体系而言,“自洽”可为体系之根基,“务实”即是体系的建设标准和发展方向,“更新”则属体系自带的特质了。
最后,我需要感谢原作者和牛津出版社同意我翻译此书,也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译作。翻译这本书,让我有机会作为读者分享一些阅读感悟,以及作为译者,有幸为更广大的中国读者去阅读此书提供了语言上的便利。但无论作为读者还是译者,我所作的功夫仍是粗浅的,只可视为原书知识的“搬运工”。原作者们为此书付出的心血和贡献的智慧,有待读者在未来阅读时自行体会。我在此絮叨几句,权做铺垫而已。最后的最后,要特别感谢原作者加斯教授和沙弗教授,他们对我翻译此书给出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在知道本书将为中国读者呈现后,不辞辛劳地为本书做序(已各附英文原序于译序之后),把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想法放在序言里与中国读者分享。尤其是沙弗教授,我知道他的序言是在多个会议间隙中作出的,殊为不易。
严文君
2025年4月于北京
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