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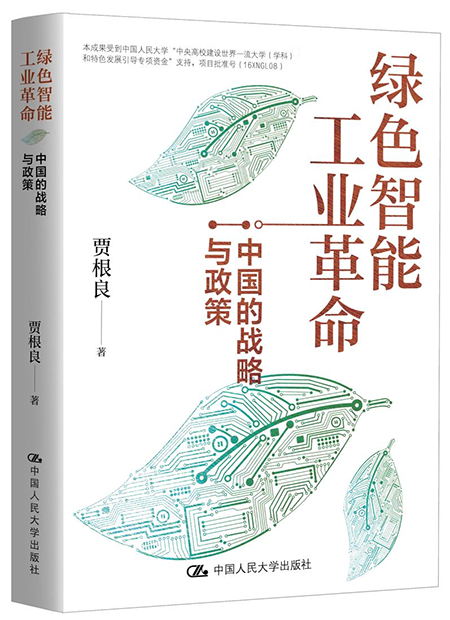
《绿色智能工业革命:中国的战略与政策》(订购)
贾根良 著
本文是贾根良教授所著《绿色智能工业革命:中国的战略与政策》一书的前言,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25年10月出版。
本书导论已交代写作宗旨和各章的主要创新点,但由于篇幅较长,读者不易快速了解其基本内容。应编辑之邀,现将其中几个主要观点简要概括如下。
一
笔者在2013年2月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中指出:“随着人工智能等科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系统都将实现智能化。”这种观点有助于人们理解2017年7月8日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本书区分了传统工业化和智能工业化。人们习以为常的工业化概念实际上只是工业化的特定类型,即前两次工业革命中资本替代体力劳动的工业化。在这种传统工业化的时代,资本的能量生产率的高低决定了一国是富裕还是贫穷。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前两次工业革命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它的核心是以人工智能系统替代人类的脑力劳动。这种以智能生产为核心的智能工业化方兴未艾,代表着工业化的新类型及高级阶段。工业化将向纵深发展。资本的信息智能生产率和智能工业化是目前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自英国开始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三次工业革命。每次工业革命的持续时间都长达100年左右,并都由两次技术革命浪潮所构成。奇数次技术革命浪潮创造新的主导产业和新范式,但其革命性作用局限于新的主导产业;偶数次技术革命浪潮将奇数次技术革命浪潮扩大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和整个社会,传统产业的生产率因之发生了量子跃迁。在偶数次技术革命浪潮期间,随着奇数次技术革命浪潮走向深入,其革命的潜力渐趋枯竭,但与此同时,爆发下一个奇数次技术革命浪潮(下一次工业革命的上半段)的时机正在孕育并逐渐成熟。目前我们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下半段,这是信息技术革命继续发展与第六次技术革命(可再生能源革命)浪潮的阶段,是绿色新政在美欧国家兴起的历史背景。
今后半个世纪也是信息技术、认知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四大技术初步聚合的时代。如果说19世纪是能源革命的时代、20世纪是信息革命的时代,那么,21世纪70年代将迎来以生物技术、新材料和纳米技术革命为主的“物质革命”的时代。历史经验说明,工业革命的爆发标志着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已经进入摧枯拉朽和突飞猛进的历史阶段,但其变革的力量在此前数十年就在不断发展壮大。这就好比,虽然1971年英特尔微处理器诞生才标志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爆发,但作为其萌芽的信息技术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潜滋暗长。我国不仅要尽早布局生物技术、新材料和纳米技术革命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率先将研究成果商业化,只有这样才能占据“物质工业革命”的先机。为此,我国需要大刀阔斧地改革国家创新体系,近年来构建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的呼声愈来愈高。
二
从世界经济史来看,新的科技革命、新工业革命虽然最先发生在当时的发达国家,但在相对落后却具有强大组织能力的国家有可能发展最快、最彻底且后来居上,这说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非线性和不平衡发展的特征,也导致了国家间国际竞争地位的此消彼长。因此,无论是对领先国家来说,还是对赶超型的后发国家来说,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都是:为什么新工业革命在相对落后而非原先领先的国家有可能会实现最快和最彻底的发展?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和制定具有关键性作用,本书试图根据演化经济学和演化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历史洞察力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
本书提出了普雷维什辛格新假说并分析了其成因。该假说是指,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和服务产品的贸易条件相对于发达国家呈现出长期恶化趋势,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参与新国际分工的方式,即从价值链低端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掌控的全球价值链,这导致了发展中国家无法摆脱发达国家的支配性影响。这是我国有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陷入高端产业低端化的困境的根本原因。因此,我国应该走一条从价值链高端和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入手的技术追赶道路。正如笔者2014年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本书第八章)所指出的,我国必须坚决抛弃依靠外资技术转移和沿着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逐步实现技术升级的幻想,痛下决心自主研发绝大部分甚至所有领域的核心技术。
本书通过整合迄今为止经济学说史中的相关论述,提出了四个依次递进的关于国内经济一体化的命题,构建了一个对我国内需问题或国内大循环进行综合性分析的理论框架,论证了加快国内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扩大内需中的引擎作用,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统一国内市场、将实际工资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实现资本品工业价值链高端的进口替代和国民经济平衡发展。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借鉴美国政府的网络型产业政策:弥补创新链中缺失的环节,形成以公私合营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和构建网络化价值链。网络型产业政策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产业政策的新型产业政策,在这种政策下,政府不能仅发挥修正市场失灵的作用,还要发挥塑造和创造市场的作用,在技术革命中担当商业经纪人和技术创新领导者的双重角色。
本书第十章收录了笔者在2013年提出观点、2018年发表的长篇论文《不对称全球化:历史、理论与当代中国》的初稿。该章提出,世界经济史告诉我们,发展中大国很难在与发达国家的深度全球化中实现经济赶超,容易陷入某种依附地位;如果适当保护国内高端技术和产品的市场,与发达国家之间处于浅度全球化的状态,发展中大国就可以创造一种对国家崛起至关重要的战略性市场空间,以确保在国内市场上创造战略性新兴工业的价值链高端,实现其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并借道同等发展程度或比自己落后的国家的价值链中低端市场,在国际上建立针对原有发达国家的技术经济领先优势。中国可以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建立全球价值链高端并把经济全球化的重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外围包围中心”的经济崛起新道路。为了确保这种新战略取得成功,中国需要针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实施保护中国高端产业、价值链高端和货币金融体系的战略。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美经济脱钩或者美国试图对中国经济再挂钩,这都应该成为我国的战略选择。
三
共建“一带一路”和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倡议无疑是伟大的构想,自我国提出这两个倡议以来,有人认为这是我国利用外汇储备加快企业“走出去”并化解巨额外汇储备的最佳途径。曾有记者在2014年以《4万亿外储“下天山”》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然而,对于人们的这一看法,笔者认为,拿着美元、日元和欧元等到发展中国家去投资、贷款,是在扩大外国货币的势力范围并压缩人民币在国际社会的生存空间。因此,笔者当时就撰写了《“一带一路”及亚投行的“阿喀琉斯之踵”》一文,并在2015年召开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23届年会上就这一问题做了大会主旨发言。笔者指出,利用外汇储备加快企业“走出去”不仅无法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目标,反而很有可能演变为替外国资本“打天下”。本书第十一章就收录了这篇论文。2017年6月,笔者撰写的内参《“一带一路”的转型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新方略》被相关部门采纳。有文章写道,2017年下半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提出鼓励使用人民币投资和结算的战略思想。
在笔者看来,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实质上是为本国高质量生产活动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市场保护的理论,我国可以效法目前的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通过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等措施为本国核心技术创新提供有保障的市场的成功经验。但由于笔者的这一看法不被学者们和一些决策者接受,所以笔者就将眼光转向了政府采购市场(更准确的说法是“公共采购市场”),寄希望于它可以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提供有保障的市场。笔者早在2010年的一篇论文中就建议停止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在2011年撰写了《我国推迟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战略构想》(该文被收入春秋研究院主编的《战略》(第一辑)中出版),并在过去十几年写过内参和发表了多篇文章呼吁重视这一问题。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