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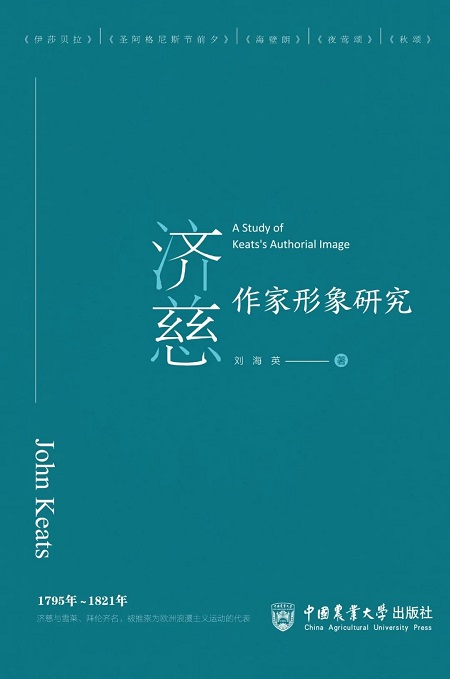
《济慈作家形象研究》(订购)
刘海英 著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济慈是英国六大浪漫主义诗人之一,国内外济慈研究领域的成果相当丰富,惜未见一部专著探讨济慈作家形象问题。本书通过包括绪论在内的5章24.5万字的内容,聚焦济慈在文学史上的形象之变迁历程,梳理济慈作家形象生成、初步发展、快速发展和确立4个阶段的特征,阐述报刊、友人、继承者和研究者、故居与资料中心4个文化要素的作用,揭示文化力量与济慈作家形象之互动关系。为济慈辩护与攻击济慈的报刊文章构成对话,生成济慈作家形象。济慈的友人用文学艺术作品将济慈形象传播至世界各地。丁尼生、罗塞蒂、米尔尼斯和阿诺德或继承济慈诗风,或研究济慈作品,使不同体裁的济慈作品得到认可。在20世纪上半叶,伦敦的济慈故居、罗马的济慈G雪莱故居和美国哈佛大学济慈资料中心相继建立,确立了济慈作家形象的经典地位。
作者简介
刘海英,辽宁省铁岭县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外语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曾在剑桥大学英语系、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比较文学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访问学习;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项、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中国农业大学项目1项,出版译著1部(合译,第一译者),发表英语语言文学研究论文和译文三十余篇,参与编写教材和教辅用书多部。
编辑推荐语
想不想了解一名诗人去世后的200年里,是如何通过他自己的诗歌和书信的魅力,与友人、编辑、包括博物馆及其墓地等各种内外因素由“可怜的济慈”转而成为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试问这世上,还有哪位作家的经历比济慈更富有戏剧性?回答是:没有!
刘海英副教授用10年的研究得到的独特结果创作而得的处女作《济慈作家形象研究》,首次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有着独特诗歌风格——慢速度、优雅、描述十分具体、视听感十足、把所描绘的经历写到极致的诗人济慈的作家形象。诗人济慈在给妹妹芳妮的信中写道,我希望窗子开向日内瓦湖,我坐下来,整日读书,就像某位伟人读书的样子一样。我们虽然不能把自己的窗子开向日内瓦湖,但我们可以感受到在温特沃斯寓所,济慈沉静而安详地身处他所热爱的书籍之中,读书时的模样——两把椅子相互垂直地摆放在地板中央,年轻的诗人济慈坐在一把椅子上,衣着整洁,身穿黑色西服套装,白色衬衫领口上打着领结,右腿放在左腿上,膝盖上放着一本书,右手扶着书,左手放在头上,左臂肘支撑在另一把椅子的椅背……
那么,就让我们在想象中共读诗人济慈在1816年5月发表的第一首诗歌《哦,孤独,如果我想和你必须同住》,当然还有《夜莺颂》……阅读诗人济慈1817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想象着自己成为了“济慈圈子”中的一份子……
想象的终点就是回到现实生活中,阅读刘海英老师另辟我国学者济慈研究蹊径的最新济慈研究著作——《济慈作家形象研究》。
部分读者评论
(1)出版人&翻译家 孔宁老师
今拿到海英老师的《济慈作家形象研究》,便先迫不及待看了她写的伦敦济慈故居的一节,不愧为研究学者,走访不说,前前后后的研究极为细致,令人惊叹!其实我也是济慈粉丝,那年走访济慈故居前做了大量功课,也努力找寻中文相关书籍,但除了诗集和一本评传到手外,相关研究集空缺,对我这个爱好者来说总觉得差点啥。伦敦北区的汉普斯泰德是文化人集聚地,许多耳熟能详的作家、艺术家、诗人、哲人都曾在此居住或暂住过,其中济慈就在此暂住过3年,今从海英老师作品中得知,他在此地曾暂住过4处,而今留下来的故居博物馆也是粉丝们心中最心心念之地,因为在此他遇见了芳妮,无论坊间及后来学着如何说其二人关系,我理想中他们就是彼此之爱人,因为济慈在此期间创作欲望可说达到了峰值,完成了六部颂诗中的五部。
今日唯遗憾的是,看到海英老师作品晚了,其对伦敦济慈故居及其纪念图书馆从建筑、历史到藏品的研究深入的不得了,为研究者和粉丝打来了一扇门!等机票便宜时,再次沿着那条静谧的济慈林荫路,东上拜访!
(2)必记本公众号北京大学教授原平方老师
媒介让人焦虑、文学使人心安。在喧嚣的年代做一个诗人的研究,是在浮躁的世界造一张平静的书桌。“济慈作家形象研究”,其实是济慈作为诗人的文学接受史。正好多年前涉猎过同作为诗人的李贺的文学接受史:比较来看,李贺与济慈正好相差1000年,均属天才的短命诗人;身后寂寞的李贺之遇李商隐与济慈之受拜伦推崇也相仿佛,有文名有地位朋友的眼光与颂扬对于无名作家的成名功不可没;或许,年轻所伴生的奇思异想也是他们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相似之处。二者的共通点更在于: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ten in water。不过,济慈有红袖可以慰藉,李贺却无相思可寄、只有一个姐姐庇护。但文学的力量却让他们不至于随水流逝、反倒历久弥新。
(3)中国农大校报执行主编何志勇老师
1821年,26岁的诗人济慈临死前对友人交代了自己的墓志铭“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 in water”,后来被译为“此处长眠者,声名水上书”(“这里躺着一个名字写在水上的人”)。我一直在想“水上书”是诗人怎样的一种心境?浮萍飘荡?还是如鱼饮水?英年早逝,又有远大理想的诗人以怎样的心境面对死亡?也许就想着:陪伴自己这短短一生的名字,就像写在水上的字,一阵风就会把它吹得无影无踪。死亡会将生前的一切功名利禄吹散,往日的一切都将随风而逝。但有文章说,这句话的翻译应该是“这里躺着一个名字用水写成的人”,而不是“名字写在水上的人”。文章分析出现这样的乌龙,可能雪莱在悼诗《哀济慈》引用了这句话,但写成了“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 on water,writ in water”变成了“writ on water”,“用水写成”变成了“写在水上”。文章还说“用水写成”是英国文学中的一个既成典故。这句话,是“速朽”的意思,水写的,很快就干了,什么都不会留下,文章说,这才是济慈拟墓志铭的本意。这不是一个希望,也不是一个预判,而是济慈对他此生的总结——我有才华,有抱负,但可恨天不假年,死后大概谁也不会记得我。
我到觉得,两个译法各有千秋,表达的意境也差不多。“水上书”似乎更有诗人生前的影子在随波荡漾,涟漪散去,也是一无所有。
我的英语也就ABC的水平。不过,诗人万万没想到,无论是“用水写成”的,还是“写在水上”的,他的名字却“如东海长流水”,没有“速朽”,而是“不朽”了。济慈墓附近的墙上后来装了一块大理石碑,上面刻着铭文:“济慈呀!如果你那宝贵的名字是用水写成的(writ in water),那每一滴都是悼者颊上滚落的泪。” 1877年,王尔德在《济慈墓》中也写道:“你的名字用水写在了大地上, 但我们的泪水会使你的纪念碑万古长青, 像罗勒树一样茂盛。”王尔德在济慈死后30多年才出生,这位自傲的作家却在《济慈墓》中表达者对济慈的惋惜、不舍,哀伤、悲痛,崇敬、怀念,各种情感。当王尔德看到济慈的情书被公开拍卖时写下了《有感》:“那些把诗人心灵的水晶面打碎的人,不爱艺术。”最近看新闻,很多与“死亡”有关,病痛、意外、谋杀、战争,人在时间的长河里总是很渺小。
小时候,总是思考人死后面对永无休止的“睡眠”,真是恐怖。后来长大,不再思索这个无解的问题。现在不知道是老了吗?还是经历了亲人的别离?又在想,人死后,变成了什么?有没有灵魂?希望有吧,那逝去的亲人,又去了哪里?像济慈,他死了吗?或着还活着吗?——只要人们还记着他。
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