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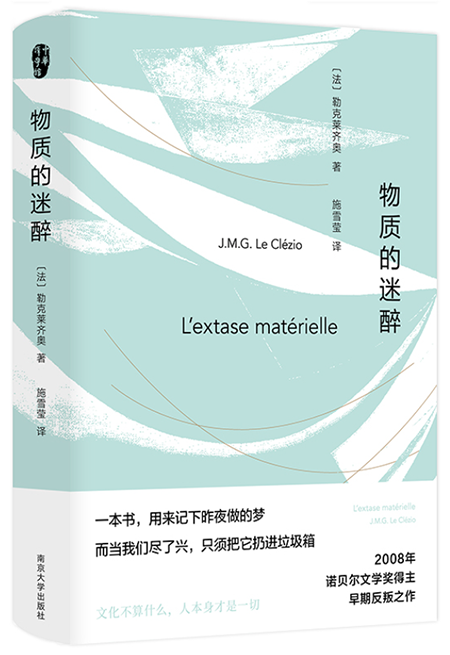
《物质的迷醉》(订购)
勒克莱齐奥 著
施雪莹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勒克莱齐奥被认为是当代最伟大的法语作家之一。他继承了法兰西的人文主义传统,善于以抒情诗意的文字表达对人生与世界的沉思,早期创作表达对现代文明社会的反叛,注重新文学形式的探索,20世纪70年代后特别关注异质文明与他者,关注人的存在。
1963年,勒克莱齐奥出版第一部小说《诉讼笔录》并获得雷诺多文学奖。1980年,小说《沙漠》获得由法兰西学术院颁发的保罗·莫朗文学奖。2008年,勒克莱齐奥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在颁奖词中用“新的断裂、诗意的冒险和感官的狂喜”来形容勒克莱齐奥的文学历险及其作品的诗学特征。自1983年《沙漠》中文版首次为国人阅读开始,勒克莱齐奥的作品始终以其严肃的文学追求和坚守的人文立场在中国文坛上受到好评。
1967年,距27岁的勒克莱齐奥发表首部小说《诉讼笔录》不过4年,这个叛逆的年轻作家想要用一本书探寻世界的样貌和存在的本质这些终极问题。他不加掩饰地怀疑一切,无论既有的思想、体系、语言,还是他自身。《物质的迷醉》就此诞生,它是勒克莱齐奥早期重要的散文作品,在作家的作品中独树一帜。
内容上看,本书重新思考自我、存在、文化与文明等概念,深入探讨了写作的本质与目的,与勒克莱齐奥的其他虚构类作品构成互文,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其创作思想。
从形式上看,本书以诗意的语言阐述哲理思考,又在思考中塑造新语言。它通过丰富、具体的词语与平白的句式重构日常生活经验,为读者带来独一无二又焕然一新的审美体验。
这是一本拒绝一切体系的散文集,关乎一场永恒世界与人的短暂相遇,它始于“我”未生之时,终于“我”死后之时。勒克莱齐奥在这本书中言说了语言边界外无可言说的存在,搅动读者固有的观念和习以为常的事物,于微末之物中探求宏大世界的谜。
人造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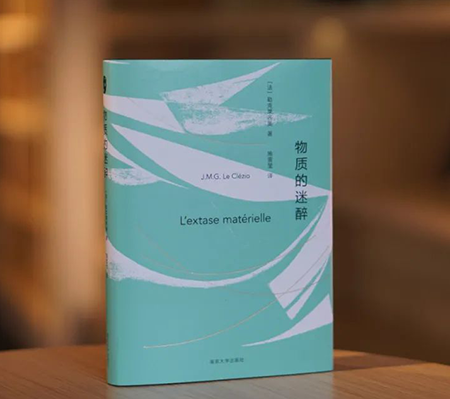
个体真正的悲剧在于,他既要被成就,又命中注定。他不拥有什么。他属于他人,通过表面的交流能力相连,被社会改变,个体是种种力量的交汇点。他是一场内爆的核心,各种外来能量在这个逼仄空间里激烈而混沌地彼此交聚、融合。
作为个体,我毫无自由可言,甚至没有自由自认真诚。我的理想,我对世界的看法,我的信仰,我的所思、所说、所写,统统不属于我。我没有选择它们。我不过是自由幻象的玩物。曾几何时,对我而言,再没什么比思想更自由。白、黑、黑、白,我统领着,我幻想我统领着。骄傲如我甚至相信,若我的想法与现实相反,道理应该在我。对想象、对语言如此精细的建构——有时甚至逼近梦境——确实曾经好像是我无可争议的财富。我一度相信自己可以对词语为所欲为,对我的词语为所欲为。
可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词语不属于我。语言不是我的财产。至于抽象的思维,对想象虚假却愉悦的构建,则不断将我背叛,对此我却从未怀疑。
我曾一度相信,我的判断、情感、道德,自然而然出自我心。我当然明白社会经验塑造了我,但我觉得总该有类似自由意志的可能选择。在诸多品质链中择一的选择。我错了。没有选择。
我身上的一切,都来自他人。一切。我的高尚思想,我的性格,我的品位,我的道德,我的骄傲。没有一个属于我。一切都是拿来的。我窃取了它们,而别人逼迫我将它们植入内心。意识、拒绝、敌意:他人,总是他人。清醒、勇气、绝对:他人,他人,他人。
迟早,人会察觉自己活在社会之中。他明白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于是他需要一种意识形态。在与现实的接触中,他身上逐渐生出一种广义的人道主义,促使他爱他的邻人、寻找友爱的温暖。如果他认真思考这种人道主义,他会发现单有情感并不足够,还须建构出一种道德体系。他推崇共存所必需的情感与首要法则(礼貌,尊重他人财产,仁慈,慷慨,等等),以此回应世界的重要议题。当这种推崇脱离了具体实际,这个人便造出了谎言、假物。
这是如何发生的?感知如何产生了滑动?人道主义原本是半自发的情感,如何沦为伪善、心口不一?是源于将之系统化的尝试吗?
说到底,这便是社会介入提出的问题。更有甚者,这便是真诚的问题。具体从哪一刻起,一个人不再真诚,反而成为幻觉的玩物?这种硬化何时发生,被感知的事物何时开始僵化,一切何时走向抽象,成了游戏?我看见身前重又敞开他人支配的深渊,不可消减的旋涡,让我不再是我,而是一个倒影、一声回音,一粒可鄙、多余的齑粉。
因为哪怕我的存在从不完整,哪怕我不过是我所在世界精神、习俗、义务与风景的产物,曾经,这个我一度是存在的,就好像出于某种共识,出于某种相对的和平,而另一刻起,这个我消失了,让位于炫耀、空洞的文字游戏,没有血肉,也没有思想。
曾有一刻我对我本应简单体验的生活强加要求,为了造出某个自洽系统的虚荣,我放弃了自己的存在,投身于确信的无知当中。
出于某种“信念”的力量,我任由自己陷入不可逆的失衡。现在,畏惧于再次跌入虚无的焦躁,我宁愿选择抽象系统炫目而虚荣的美。许多人在回归自身之后,都发觉自己的生活不过是骗局,而他们人造的意识形态也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人无法如此轻易就逃脱孤独。诚然,怀疑不是建设性的举动,幻觉则与信仰一样,拥有颠覆山峦的力量。可颠覆山峦又有何用?毕竟我们自身也不过齑粉,简单、清醒的一瞥便足以让您土崩瓦解。
最为深重的罪行,人若犯了,原因不是情感,而是才智。必须学会拒绝理解的欢愉,必须学会放弃好为人师的傲慢。信仰出现并不是因为人们需要它才能获得幸福。人类的爱并不简单,更与善心无关。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注定无法伟大而真诚?并非如此,但既然谎言和人造物确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基石,就必须质疑所有不源自我们情感的事物。我们必须不断回归自身,深化自我,认识自我。只有在接近自身秘密的过程中,我们才能触及普适的谜。我们的统一性,由无数碎片构成的不幸的统一性,必须将它寻找。所有判断、道德、宇宙真理的钥匙,如果存在,必然存于这统一性之中。
那么现在,还剩下什么?不剩一物。我已经剥去身上所有遮蔽我脆弱真我的外物,就像褪去华而不实的外衣。我是空洞的又如何,注定一死又如何。信仰,或许需要用另一种方式触及。形容枯槁、没有未来又如何,我的自私无法变成人道主义又如何。我只想要我能把握的东西。让我抵御他者吃人的深渊,抵御我目光的深渊的东西。哪怕只有虚无,只有绝望和失调,它们也充实了我,因为这就是我,是我唯一的真实。
或许轮不到我去评判最后剩下的是什么。但是,我必须这么说:我什么也不是。
我写下的这些词句不属于我。我没有权力相信它们是我的。我不过是历史的记录者,能够反映事情本身便已心满意足。归根结底,我想做成的便是此事:一本忠实的书。不放弃任何人性的东西,不轻视任何物质。因为在遵从外部要求的过程中,我也在塑造自我。奇特的双重行动。
我书写。我用他人的思想书写着。
写作
写作,肯定有其用处。然而是什么用处呢?这些精雕细琢的微型符号独自前进,几乎独自前进,覆盖白色的纸面,刻上平坦的表面,画下思想发展的轨迹。它们删减。它们调整。它们歪曲。我喜欢它们,喜欢这支圈、折、点、线组成的军队。我的某一部分活在它们之中。哪怕它们并不完美,哪怕它们并不真正在交流,我依然感到它们带给了我来自现实的力量。有了它们,一切都变成了故事,一切都走向它的终点。我不知道它们何时会停下。它们的故事是真,或假。我并不在乎。我倾听它们并不为这个原因。它们让我心生愉悦,所以我欣然任由自己被它们行进的节奏所欺骗,乐于放弃有朝一日理解它们的希望。
写作,如果确有其用,必然如此:见证。留下被铭刻的记忆,柔缓地、不露声色地产下即将孕育的卵串。不是阐释,因为或许没什么可被阐释;而是同时展现。作家是寓言的制造者。他的世界并不诞生于现实这一幻象,而是产生于虚构这一现实。他就这样前行,赫然盲目,断续缀起种种欺骗、谎言和微小的善意。他的造物不是为了永恒而创造。它也应该有尘世之物的苦乐。也应该有缺憾的力量。且应该听来悦耳,温柔而感人,仿佛一场想象的探险。如果他打下根基,那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基础。一如代数算式,他将世界简化为与某个自洽系统相连的图形表达。而他提出的问题总会被解决。写作是时间唯一的完成形式。有了一个起点,便会有一个终点。有了某个符号,就会有某种意义。语言组成的幼稚、细腻、温柔的戏剧。片段的世界,完成的图画。不可抗拒的意志,微小符号的神秘大军永恒前进,在纸面上积累倍增。此处何物?是什么被标记?是我吗?我是否终于让世界回归秩序?我是否得以在这一方小小的白色空间让它成立?我是否将它塑造?不,不,这一点上,别弄错了:我不过是在讲述人的传奇。
书写的形式、写作的体裁并不真的那么重要。对我来说唯一的关键:写作的行为。文体的结构是脆弱的。轻而易举便会破裂。读者和评论者都被形式欺骗了:他们不愿评价个体,却要评价作品。作品!它们真的存在吗?
当然,文学体裁是存在的,可它们无关紧要。体裁不过是种托词。人们并不会因为想写一部小说就创造出艺术。也不会因为他的作品被称作“诗集”就成了诗人。为自己和他人的写作,唯一的目标是忠于自我,正是通过这种写作,人才能触及艺术本身。
今时今日,人们愈发偏好艺术唯一的表达方式,认为它应该是探究人类意识的某种途径。虚构的故事斗胆变作科学,科学又回归神话。在所有形式细分之前,我们想要表达的首先是活着的人的历险。
但“体裁”的问题确实比看上去更加重要,因为有太多人,面对体裁会像对待时装那样,附庸风雅。他们宣称自己只喜欢小说(而且在小说中,只喜欢一种“体裁”,诸如侦探小说云云),或者只对诗歌有感觉。而同样一首诗,如果封面上写的是“短篇小说”或“叙事类作品”,就不会得到业内人士同样的热情追捧。又或者,一个批评家可以斩钉截铁地断言一本书不可能是“一本好小说”。一张轻易附上的封面,作用就是将只能单独评判的作品归入笼统整体。这种教条主义与缺乏主见的行为是空无的掩体。关于人类语言的迟钝谎言,不在于它试图建立起脆弱的联系,或是它对本质的孤独视而不见。而在于它不愿意向前一步,迅速深入交流的核心。人什么时候容易上当?并非他们尝试彼此呼唤的时刻;而是他们高声叫嚷着拒绝如此的时刻。他们满足于表面的结构,其实却应该挖掘最悲剧、最真实的部分,找到撕心裂肺的语言,去打动人心,或许,将黑夜转化为暗影。
为了接近我的真实,我贫乏的工具,只有直觉与语言。但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工具于我已经足够。它们确定性上的贫乏却是偶然性上的财富。我不应以自己的口吻说话。我该让身上的他者诉说,其他无是,其他物品。虽然我的工具并不理性,可它们激发的情感却让我得以在自己意识的未知领地上,苦乐参半,蜿蜒前行。人不可能同时获得知识又保持强健。而我,我选择了脆弱,让目光与话语漂泊无依,和缓地埋葬,肥沃地消亡。我担起自相矛盾、无可举证的风险。但我感觉到正是在此处,一切猛烈地活着、躁动着、扩张着。我心怀恐惧。无论如何,事实是,事到如今我已别无选择。回头已经太迟。当有朝一日,事物以其本来的样貌,展现在您面前,当它们终于献上自己冰冷又疯狂蔓延的景象,没人再可以忘却。渺小、伟大、肮脏、无垠、高贵、癌变,世界,骇人而嘈杂,同时又克制且精致,世界,以人为尺度又超越了人的尺度,被简化为符号,打破了符号,容易模仿,也容易发狂,世界,大地、生命、伸出小枝的树木、鸟儿、叶子、泥板、沼泽,还有蛤蟆、白色花萼、蚊蝇,世界,猛兽的大军,浓稠、发黑、呛鼻、发亮的血,它发干发脆,滋养着猎捕的族群,世界,光的运动与原子的滑行,太阳的轰炸与空间的空洞,黑暗,一切,绝对的一切在此,一切将我冲击,一切将我塑造、将我羞辱、将我面朝下扔向大地,世界,冰冷深渊的空间、贪婪漏斗的空间、时间的细节、生化循环、疾病、新生与死亡,世界,创造,创造不息的曲面,其中没有一物可以带来和平,没有一物可以止于自身,其中没有微笑和解,没有举枪言和,十分神圣又十分邪恶的球体,其中永不会给出这个可鄙问题的答案:“然后呢?远处有什么?随后有什么?”
本文节选自南京大学出版社《物质的迷醉》
来源:南京大学出版社
|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
首页 |
宏观指导 |
出版社天地 |
图书代办站 |
教材图书信息 |
教材图书评论 |
在线订购 |
教材征订

